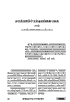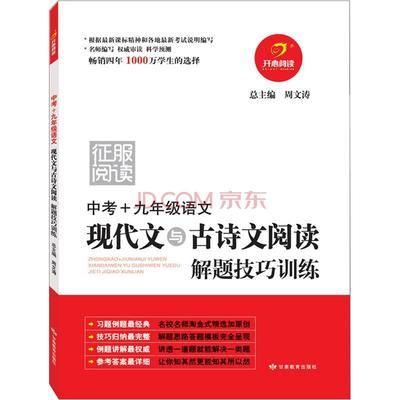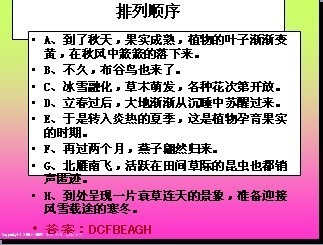1951年冬,我上了学,上的是半年级。
学校离家不足5分钟的步行路程,叫“三官庙小学”。校内有一大庙,庙内曾供三官,曰“天官、地官、水官”,故名。该庙修建于何时?由何人修建?均不详。三官早已不知去处,大庙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别看大庙陈旧的样子,对学校来讲,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办公室只在南面开有门窗,没有玻璃,全是纸糊的,因此光线很差,又没有电灯,感觉有点儿阴森和恐怖,仍然保留着一些庙的氛围。庙内柱子上挂着一座挂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最现代化的设备了,整天“嘀嗒嘀嗒”地响着,像在努力驱赶着庙内的阴森气儿,也增添了些许生机。
“中南海”简陋若此,其他教学设施就可想而知了。不,可想但未必知。就说教室,先不说好赖,单数量就不足。刚上学时,我们半年级的学生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室,而是和一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加起来多达85名学生。上课时,由同一名老师在黑板中间划条分界线,分别讲授半年级和一年级的课程。85个小学生密麻麻地挤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教室里,又有近半数人听着不是讲给自己的课,秩序混乱就是难免的了。

升到一年级后,我们算有了自己的教室,但低矮简陋。夏天还好过点儿,冬天实在难熬。没有炉子,纸糊的窗户透不进多少阳光,室内格外阴冷。往往上课不到十分钟,桌下跺脚声就响成一片,前面讲课的老师则从黑板的这头走到那头,还不时将手放到嘴边,接收点热气儿,要不就无法拿住写字的粉笔。学生们一个个坐得挺直,不像夏天时爬在桌子上慵懒的样子。为什么?原来多数孩子只贴身穿着一件棉袄,或最多再衬件单衣,身子挺不直,就会从后背灌入凉风。所谓书桌就是在几根木桩上钉上一块长长的木板,木板的长度比教室的宽度小,靠墙两端留出行人的空道;木板的宽度一尺左右,够放书本了。板凳则是书桌的相似形,成比例的缩小就是。这样的书桌不能盛书,只能放书,而且只能放当节课用的书和本,其余的装在书包里,书包则挂在书桌边上的一颗小钉子上。
与简陋的教室比较协调的是学生们的学习用具。我的书包是把一条羊肚手巾对折,将两个侧面缝上,再在开口的那面翻个边儿,穿上一条绳,就成了。装在书包里的除了书之外,还有块石板。这石板是用来写字的。由于农家大多贫穷,承担不起笔记本这样的易耗性学习用品,所以,写字练习、算术演算类的科目,老师并不要求一定要写在纸上,只在石板上练就可以了。石板的好处是可以反复用;缺点是易碎。一些喜欢追逐打闹的孩子,上学或放学路上,常有打碎石板的经历,只好硬着头皮告诉家长,硬着头皮等着家长呵斥,甚至挨上几巴掌也是有的。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由家长掏出钱来再买一块。一块黑板的价格是两毛五,这对多数农家都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许多学生是知道爱惜的。与石板配套使用的是石笔和石板擦。石笔较便宜,石笔擦也不贵,还可以自己做。到了3年级,笔记本就不可少了,学生要记笔记,也要把做完的作业交给老师批。为省钱计,多数学生自己买纸,自己订本。看准商机的小贩常把学生用品带到学校来卖。花4分钱就可以买一张大白纸,回家裁成32小张,自己找来针线,动手订成一个本,用起来格外知道珍惜。到了4年级,老师要求用钢笔写字了。这钢笔就更算是大件了。没成想,回家一说,二叔很痛快地斥巨资给我和文睦哥各买了一支“自生”牌钢笔,单价是七角五分钱(那时父亲与二叔还没分家呢,父亲常在外赶辆骡子车拉脚,家里事就由二叔打理)。
校园里有七、八棵柏树,排成一排。树虽不高,但很沧桑古老的样子,似可见证大庙的历史。两棵高大的槐树是校园内的另一道风景。一口铁钟就挂在其中一棵的树杈上。当时,这口铁钟及大庙里的挂钟担当着重要角色,指挥着全校师生员工的作息。它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师们,乃至校长(王馥亭)都没有手表,要想知道准确的时间,就得进入大庙里往柱子上的挂钟朝拜一眼。由于员工不足,没有专职人员负责上、下课的敲钟,而由每个老师轮流值日;轮到值日那天的老师,要格外注意挂钟上的时间。每天早晨上第一节课前10分钟,要敲一遍预备钟,意在提醒全体师生做好上课准备;待敲完第一节课的上课钟之后,值日老师便赶紧去上自己的课。在课堂上看不见挂钟,只能凭感觉;课讲得差不多了,估计该下课了,便出去敲下课钟,让全校师生方松一下。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有的老师讲课兴致高了点儿,或者学生们的感觉跟得慢了点儿,就会使45分钟的课延长到55分钟或更长,害得其他班也跟着压课。当然也有提前下课的时候。好在这一天都归他一人控制,能在其它课上灵活调整一下。但比较精明的老师常常这么做:在预计下课之前打发个学生看一下挂钟,这样就容易靠谱了。我就多次被打发去看过钟,但实在难为情,不认得,只会说“长针指着几、短针指着几”,但老师精明呀,说声“好”,算我不辱使命了。
虽然家里没有钟表,但几乎没发生过上学迟到现象。因为家离学校很近,上课前的预备钟声听得清清楚楚;听见钟声,即使还在吃饭,赶紧耙拉两口,背起书包上学也赶趟儿。不过,通常是不会这么紧张的。农家自有农家掌握时间的诀窍,古人不早就发现“见堂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了吗?早晨,凭太阳照射在窗户纸上的屋檐的影子,就知道时间的早晚,比如影子到第一个格子就该吃饭,到第二个格子就该动身了,等等。碰上阴天,就尽量赶早不赶晚了。总之,以不迟到为前提。在家长的监护下,办事守时的良好习惯从小得到了培养。
在学生面前,老师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当时普遍流行着体罚,几乎所有的男老师都充分利用了体罚这一法宝对付“乱说乱动”的学生。轻者或初犯,会领教一段粉笔头的袭击;重者或累犯,有时会享受黑板擦或教鞭的重创。进行袭击时,老师并不正眼盯着目标,而是若无其事地照常讲课,只用余光扫一下,而后来个“说时迟,那时快”式地突然袭击,学生往往会遭到猝不及防的打击。由于训练有素,个别老师的命中率出奇地高。这时,坐在被袭者前面的学生会条件反射地朝老师挥舞的方向看过去,落实一下倒霉蛋是谁。坐在后面的学生有的惊愕一下,有的小声窃笑两声,便很快平静下来。但平静是相对的,不平静才是绝对的,因为那是一群注意力集中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的孩子。老式的教育遵循“不打不成人,打成作官人”的信条,老师对学生实施体罚,被看作是对学生的负责任,是为了学生好。
在体罚学生的武器中,最常规的是粉笔头,杀伤力不大,老师往往投过之后跟没事一样,继续讲课,警告一下而已;黑板擦要算重武器了,袭击的同时,还常伴有老师声色俱厉的训斥。由于学生太多,犯科的频率就高,而且可发生在任何时刻。赶巧老师手里没有粉笔头或黑板擦,怎么办?比学生聪明得多的老师会因地制宜,比如顺手拿起教鞭,迅速奔向肇事者,朝后背、脖子、胳膊甚至头上抡去,姚凤贵的脖颈子就被敲肿过;赶上手里没有武器,对学生煽几个嘴巴,打几个耳光也是有的。最恶劣的一次是,某天下午没到放学时间,几个学生偷偷往家跑,结果除王树田(后改名王存仁)一人侥幸得逞之外其余全被老师擒获,首先挨了几脚乱踹,然后又遭受一种酷刑:往眼睛里滴石灰水!何其残忍!记得王桂森是受刑者之一。
女老师管教学生的常规武器也是粉笔头,但投掷的力度不够,准确度更难获恭维,有时还会误伤无辜,弄得自己挺尴尬。但她们,比如那位身子挺胖、眼睛挺大的张老师,半年级和一年级时任我们的班主任,惯用的手法是拧耳朵或掐脸蛋,“犯人”脸上轻则发红,重则变青变紫变肿,疼痛倒还好忍,这被羞辱的印记几天之内都留在脸上,实在有失体面。为此,多数学生会汲取教训,克己自律一段时间,老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善体罚的女老师就数贾艺文了,她是我们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淑女型老师,喜欢跳舞,也教学生跳,但她对学生的温良恭俭让换来的却是常被学生的顽劣气哭。
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是本村的许梦池,人长得很白净,说话声与女性相似,厉声喝斥或动手打学生的情况很少在他身上发生。他头上留着分头,在当时是很超前、很时髦的,但他不敢以此大胆示人,一年到头带着一顶帽子,将头型遮得严严实实。越是如此,学生们就越觉得好奇,就格外关注他的头部。极偶然的机会,许老师会将帽子摘下一瞬间(兴许是头皮痒了挠一挠),然后又很快戴上。就这一瞬间的亮相,会让学生们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并成为许多学生,尤其是女生的谈资。在许梦池当班主任期间,王桂重、王桂秋兄弟俩曾先后代过课共两个月的时间。王桂重平时几乎没有笑脸,常常目光呆滞冷峻,对学生特别喜好体罚,他动辄挥舞拳头,狠狠地向学生头部砸去,有时也拿带有铁皮箍和弹簧夹的硬折子代替双拳,加上他那浓浓眉毛倒竖、大大眼睛怒瞪,煞是吓人。多数学生感觉他有些过分。他的弟弟王桂秋则比他温和得多了。后来,王桂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障碍,喝墨水,跳墙,在家里家外乱打人,……
比较起来,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李铁宾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最轻松,甚至可以说李老师是最不讲师道尊严的老师。当然,有时他也会朝学生动武,脚上那双带着厚厚鞋底的黑皮鞋是他的常规武器。就算不动武,他的怒眼一瞪,也怪吓人的。但过不了一会儿,他又会把气氛调整得很轻松,让学生很容易跟他接近。
他教我们自然和体育两门课。
自然课上,他用两节很大的干电池和一段细细的铜丝导线做试验,在导线上涂抹的蜡油会因通电而熔化;把导线做成螺旋管状,通电后会产生磁场而将小铁钉之类的吸住;把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一会儿蛋壳会变软;……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李老师常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等你们将来上中学就会明白了。”这句话很实在,也很得体,因为当时的小学生没有更深的基础,只能点到为止了。但这句话也是很有激励性的,尤其对求知欲强的孩子。当时的状况是,大多数农村的小学生进不了中学的,升学率不过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农家子女念完6年小学后,就成了13、4岁的“童农”。
体育课就很灵活了,刮风下雨天自不必说,上室内课,课堂内容基本上就是讲故事,杨家将啦,童林大闹五台山啦,听得男生们聚精会神,多数女生则趴桌子上睡觉。多数时间还是上室外课。齐步走之类内容学生肯定不喜欢,鞍马跳箱类可能是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多数学生也不感兴趣。李老师自己年龄本不大,大概天性也是喜欢玩耍之人,更明白学生的心理,自会投其所好,经常把一节体育课上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他常把学生带到鲁家坨庄北的一个大沙坨子上,分成两拨,拉开距离,他自己带领一拨,以沙坨为“战场”,模拟上甘岭战役,玩打仗的游戏。仗打得异常激烈,土圪塔就是“手榴弹”。不消说,李老师“敌方”的袭击目标全是老师的脑袋。土圪塔虽然不会爆炸,但击中目标时也会冒出一股沙烟的,李铁宾老师的身上、脸上没少挨“炸”,每逢这时,同学们,包括他一拨的,免不了哄笑一阵;他本人也只有苦笑而已,并不会对攻击者(也无法确定攻击者)发怒。他是真正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这也是学生们愿意与他一起玩的原因。有时,李老师也带学生到庄南的树林子里去玩,讲故事、掏斑鸠窝、摔跤比赛是常有的节目。当时,堪与老师对垒的摔跤手是王桂全,他年龄较大,主要的是他长得身高膀园,令李老师很难对付。
那年代,有自行车的很少,而李老师竟骑辆德国进口的带有摩电前灯的自行车上下班,好不让人瞠目。
五、六年级时共有两个班,我们班的班主任叫傅树坛,教语文。傅老师的课讲得很精彩,字写得尤其带劲。油印的考卷及复习题之类,常由傅老师刻蜡板。院墙外面的白底红字宣传标语也出自傅老师之手。标语的时代性很鲜明:“少年象罗成,老年赛黄忠;青年学赵云,壮年比武松;干部智慧胜诸葛,妇女压过穆桂英。”“手是巨大的财富,脑是无穷的力量。大家动手又动脑,一切困难都吓跑!”
1957年的暑假过后,再一开学,我就要升入六年级了。但不知为什么,那年的暑假格外长,竟达70多天。作为小学生,通常不会嫌假期长;农家小学生,就更希望假期越长越好了。假期长,除必须帮家里干些活之外,总有玩的时间。自由地玩耍,是所有孩子的天然需要。那时农家孩子可玩的项目都比较简单,所用道具多随处可得,但也能让单纯的孩子们玩得投入、玩得开心。比如,两个人各捡块破瓦,砸成烧饼大小,就可玩“驾瓦”的游戏,既练瞄准,又增强弹跳力。再如,将硬纸壳剪成火柴盒大小,就制成了“片儿”。甲乙二人就可玩“扇片儿"的游戏了。规则是:甲拿手中的片儿去扇乙放在地上的片儿,如能扇翻过来,就赢了,乙的片儿归甲;乙再放地上一张,如甲又扇翻过来,又归甲,直至扇不翻过,轮到乙来扇。高雅一点的“片儿”须花钱买,5分钱可买一大张印刷精美的画片,可分剪成60小张,每张都印着五颜六色的人物,多为三国、水浒、杨家将、封神榜里的名人。还有“欻(chua)大把儿”、“扔錁儿”、“罚滚儿”、打玻璃球,以及不用任何道具就能玩的“藏猫猫”、“骑马打仗”等游戏,虽不高雅,但也都陪伴着农家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捎带着也锻炼了身体。
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玩得开心的那个秋天,老师们都集中到县里参加很重要的会,顾不上给学生上课了。此间,有一批心直口快的文化人交了恶运,被戴上了类似孙悟空头上紧箍的“右派”帽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