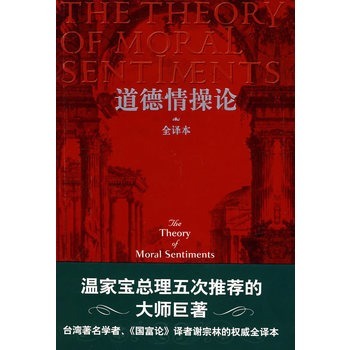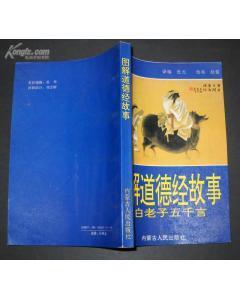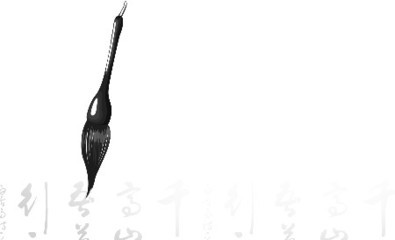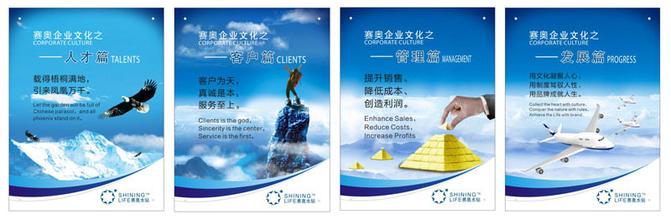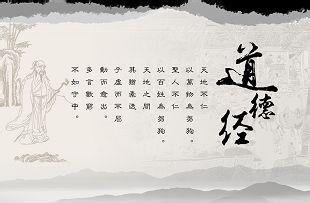一般认为,《道德经》是讲宇宙天地大道的,似乎,与心智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么认为,只是看到了《道德经》表层的意思。没错,老子在讲道、讲不争、讲高下相倾、讲无为、讲清静为天下正,等等,但我们要思考,老子为什么讲这些,老子讲这些与我们人类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智者,老子当然不会不着边际的只讲些他对天地的看法,除非他想显示自己的高深,或者,隐居前五千言书写,纯是为了糊弄让他留下墨宝的关令尹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一个要隐居的人没必要通过高深来证明什么,一个喧嚣的世界都被他放弃了,他还会在意高不高深的名声吗?而关令尹喜最后是跟着老子走了,成为了老子的嫡传弟子,可见并没有被糊弄而是得了真传。
所以,我们要知道,老子并不是在讲天、地;老子是在讲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认识天、地。
老子说,维系这个世界运转的背后关系叫道,这个道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叫做象;你要认识象和象背后关系(道),就必须向天地一样,谦卑、虚空(老子叫恍兮惚兮)、清静。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你清静下来,这个道、这个世界在你的面前就会以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你就和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和谐的二元,你通过正确的认识它也就和它和谐一体了。
你看《道德经》要明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序,不仅是逻辑排列,它也是心智认识世界的一个顺序。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内心和地、天、道发生联系,最后,才能回归到道法自然的无为境界----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认知过程是一个和道融合的本源状态,是道本来的面目,是生命与天地一体的自然、和谐。
《道德经》一直在讲一个认识世界的基点(我们现在把这个基点叫做原点),人以自我为原点,清静、谦卑、守拙,仰望天地,通过心智对地、天、道的认识,又回归到自我与道合一的无为境界,又回归到清静无为、和谐旷远,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灵认识的旅程,而这个心灵认识旅程的轨迹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看看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是如何破解这个奥秘的:
道可道,非恒道矣;老子说,能说出来的道理,就不是恒久、永恒的真理,因为,真正的大道是隐藏着的,是恍兮惚兮、旷远深邃的、自有万有的,它一直在以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孕化这个世界、修复着这个世界,我们要对它保持尊重,我们要谦卑、清静,但同时,我们也要进取;
名可名,非恒名矣;当我们在进取中对道有一些认识,我们把这些认识说出来或者写出来,这些被认识的道性或者道理就有了名字,就有了关于它的概念;当一个事物被认识,被概念化的命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有局限的了,就不是恒久的了,因为,它变成了我们人心灵的一个认知,它就从道性中被隔离出来了,这就是非恒名。这个认识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不管怎样,只要一作为人的认识,它就只是一个对道性的某一个方面的了解,它就处于有局限的状态,它的认识就是一个有边界的认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一个有边界的世界。
故常无欲,以观其眇;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认为,我们的心智对这个道、名构成的世界进行感知时,有两种状态,这两种不同的心智状态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当我们清空自己的欲望,放弃我们的判断,我们会发现世界的精妙、会发现道的奥秘、会觉知事物起源的深邃;而我们认识了事物后,我们就处在了有为状态,我们的欲望就会出来,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认识来命名、界定、改造事物,我们会看到事物的联系性、事物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以及,事物的旷远广大----我们会明白事物的局限性和边界,当然,我们也得承受欲望太强所带来的反作用效果。
我们看到,在开篇的枢纽中,老子在讲什么?讲道和名,实际上也在讲心智欲望,在讲我们心智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时状态,以及,这种联系性对我们心智的影响。
老子讲这些是有一个基点的,这个基点是什么?是的,是人,是人的心智,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道德经》开篇就是在是讲心智,讲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融入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老子说,这是个玄而又玄的与道融合的过程。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为什么玄而又玄?因为,你在自我心智面对世界的基点上,静而又静、恍兮惚兮、不争无为就把自己和道融合了起来,你就能体会与道合一的美妙;但我们是活在现实中的,我们不能一直不作为的就这么美妙下去,我们还要有欲,还要与人和世界发生联系,这个联系会主观、会局限,但这个进取是生命的必须,这个完美的道性本质和不完美的对道的不断认识就构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生活状态。
我们把老子这个以人为基点的心智智慧叫做原点智慧,它虽然玄而又玄,但它是我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本源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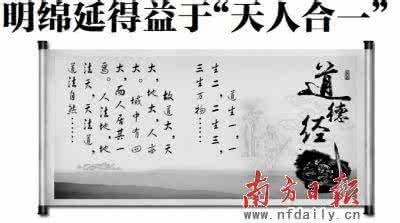
静与动、无为和有为、融合和边界、清静与纷扰、圆满和局限, 这是心智一直存在的二元状态,这也是老子给我们揭示的玄而又玄的奥秘。
所以,《道德经》的智慧看起来是讲天地大道的关系,实际上是讲天地大道与人的关系、与心智的关系,它是一本关于宇宙大道的书,也是一本通过认识世界让自己心灵得到宁静的书,事实上,它更是一本关于心智智慧的智慧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