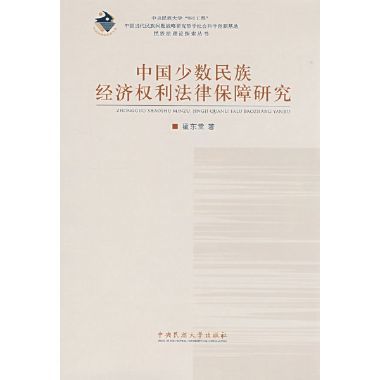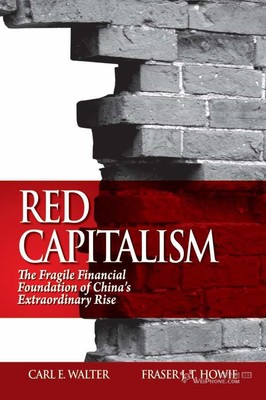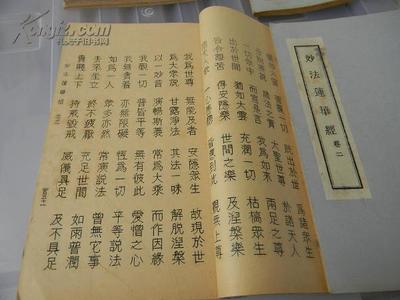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起步腾飞,我国法学教育也快步迈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法学教材在需求的爆炸式增长等刺激之下可谓层出不穷,琳琅满目,品类繁多。一般印象中,教材之于大学生基本上是考完即遭弃置,在时间的洪流中,因为他们的枯燥乏味、千人一面和似曾相似,多被匆匆风吹雨打去,很少也很难再被人想起。不过,这仅仅是一般的虽占绝大多数的毫无特色的教材的命运。一些少数有思想特色的极具鲜明个性的法学教科书,则仍然为人用而不忘、暗香不去,并被曾经受其启发润泽的法科学子珍藏爱护,不时拿出来回味一番,以为增进学理知识,兼及回顾过往走过的路。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多数教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知名亦或无名、薄的还是厚的,大多成了“驿外断桥边”的浮光微澜、横斜疏影,能记起的实在有限。不过,有如下几种教材却是印象深刻而难忘的,根源在法里法外都有。首推张文显教授主编的红皮本《法理学》。如今已很难想起这本教材在法理学知识内容上有什么“特色”了,这本教材所绍介的乃是法理学、法律哲学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关于“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所形成的学界共识与通说,是最基础的内容,潜移默化之中,红皮书中所记载的法理知识悄然入脑,化于无形,“为我所用”。虽然“法律人的思维”得以初步建立,但一些条条框框在毕业之后甚或是期末考试之后就“都还给老师了”。这样一种知识传授上的“白开水”,是很难对一贯挑剔的大脑皮层造成刺激的。而它之所以还能够给人打下深刻的烙印,乃在于时年(或许延续至今)法学院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国内大多数法科学子都在使用张文显的《法理学》。现在想来,不外乎如下几点原因:其一,这本书在同类教材中水准最高,主编权威、名气大,撰稿人阵容豪华、庞大,高手云集,几乎囊括法理江湖各大门派的代表性人物,[1]“集聚效应”、“明星效应”、“品牌效应”凸显。其二,是书“简明而富有逻辑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对法的本体,法的演进与发展,法的制定与实施,法的价值,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法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阐释;对通贯整个法学体系的基本范畴,诸如法、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全球化与法律发展、法治与社会建设以及法律程序、法律方法、法律职业等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引自《法理学》内容简介),体例简明清晰、知识系统全面、语言通俗易懂、阐说深入浅出,确实适合用作法律本科学生入门武功秘笈。其三,大一新生,对于刚刚触碰到的大学校园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懵懵懂懂,对各种规则尚不熟悉,只能乖乖听命于学校教务部门统一购买教材等诸安排,不像大学后期,大家伙慢慢都修炼成了“老油条”,教材打破“一统江湖”局面,五花八门,来源渠道也多种多样,如复印的(文印店以营利为目的的大批量复印销售教科书有侵犯知识产权之嫌)、从师哥师姐处借来的、学期末先下手为强提前到图书馆借出的、毕业季从毕业生的“跳蚤市场”上花五毛钱买的或是与其他商品搭售送的、从各大实体书店或是网上书店购买的,或是少数不羁者干脆就不用教材等。是故,法学教科书格局的前期一元与后期多元,愈发使得张文显的红皮本《法理学》成为共和国一个时代法科学子的共同记忆!

第二本难忘的教材,是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健主编的《商法》,也是红皮本,系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这本教材的使用面不如张文显的《法理学》那么广泛,但这本书被我及身边的同学都死死地记住了,原因或与商法知识无关,说出来还显得对作者本人及其学术成果有些大不敬,甚或还有侵犯人格权、有损他人人格尊严之嫌,但幸是大家并不带有任何主观恶意,仅是过过“嘴瘾”,以为生活谈资罢了,并不对千里之外的范健教授造成任何心理不适与客观危害。故而在此也不必佯装高端、作遮掩之态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敢做就要敢当,真实原因端在于作者“范健”之名与民间使用频率较高的粗鄙话语“犯贱”一词正儿八经同音契合。拿到这本教材时,实在难以免除将此二者联系起来,就连商法老师在上第一节课时,也拿编著者范健教授的名字开了个与我们这些“无知者无畏”的学生同样俗气但接地气的玩笑,并借机有感而发一番关于自然人、法人商标、商号等取名哲学沉思的宏论(这也属于《商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一),如要将拟好的名字事先用普通话读一读,同时也要用家乡土话读一读等等,还要格外注意听音、听义、听节奏,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第三本难忘的法学教科书,可能是分量最重的一本法学教科书,是国内法律人都熟知的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的个人著述《刑法学》。[2]应该说,这本书作为教学用基本教材在法律本科生中的使用面不是很大,并非教材本身质量不高,恰恰是因为质量“太高”导致“曲高和寡”及显得不合时宜。本科阶段,法科学生处于法律基础知识的适应期、启蒙期与积累期,没有根基,比较脆弱,若在这时施用猛药,与拔苗助长无异。更为具体而现实的问题是,比对本科阶段安排的刑法课程教学学时,采用张明楷的《刑法学》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恐一时难以消化,甚至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造成内外循环紊乱。不作为基本教材采用,并不意味着《刑法学》从此就被大家抛弃,相反的是,张氏刑法以它别具一格的体例结构、刑法思想及文字魅力成功开辟出第二战场,国内多数法学院的刑法教师成了《刑法学》一书的“推销员”,他们在刑法课堂上不自觉地会向学生反复引述张明楷教授的学术观点并推荐《刑法学》,[3]将之列为课后必读书目,《刑法学》由此在青年法科学子中间得以广泛传播、热烈讨论。张明楷教授凭借其一手“经营”起来的《刑法学》,“未有蹈常袭故、循规遵矩”(第三版前言),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在中国刑法学界自成一派,独步武林,俾睨天下,积极倡导并投身刑法理论的学派之争,引领刑法研究风骚十余载,至今未有止歇迹象。“大抵缘于村生泊长的经历、讨是寻非的心态、标新立异的习癖、独树一帜的幻想、好高骛远的性情、不自量力的狂妄”(第三版前言),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领域的精耕细作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丽风气,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视野变得开阔、给人思想强劲冲击。他的《刑法学》已然成为一座高峰,对于学习与研究中国刑法人士,注定是绕不过去的。由此,张明楷教授被法科学子、青年学人亲切称呼为“楷哥”(也有称他“张教主”、“张大师”的),在他的身边也有形无形中汇聚起一大批“K粉”,通过“楷哥”与“K粉”之间的尊重与竞争、容忍与对抗、理解与批判,形成一股推动我国刑法教学与研究、刑事立法科学化、刑事疑难案件排惑释结的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不宁唯是,张明楷的《刑法学》与国内一般法学教科书在风格上是迥异的。国内多数法学教材沿袭的是前苏联过去一贯采用的主编制,全书由主编或执行主编统筹,各章的撰写任务由学者分工单独完成,虽然最终集成一书,但如同水果沙拉,虽然搅合在一起,却是各自为政,整部教材很难有自己的刑法基本立场,很难形成统一的刑法学体系,也很难将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缺乏内在统一性,更缺乏学术个性…….本来作为十分神圣的著作体例的教科书,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然而在我国,教科书这一体例被糟蹋了,被庸俗化了”。[4]如此这般,学生在使用刑法教科书时发现一本书中观点相互抵牾、前后自相矛盾、总论分论撕裂互博等错乱样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毫不客气地说,这种形式呆板、简单重复、内容陈旧、缺乏时代生命力的教科书,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学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也不无掣肘之处,这是“硬件”上的短板!与法学、法治繁荣发达的外邦法学家对教科书谨严且敬畏的态度相比,[5]中国法律人似乎在这一方面显得过于随意,最终导致“在中国,教科书成了最陈腐的材料的代名词”。[6]不知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张明楷教授从1997年推出《刑法学》第一版始,就大胆打破沉闷的主编制采用专著模式撰写带有个人刑法基本立场的体系性刑法教科书,数十年如一日,“精心‘经营’着自己钟情的教科书,在那片园地里阐扬传世理念、彰显卓异才华”(第二版前言)。应该说,这是作者对刑法长期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个人学术研究成果“最精华的部分”的高度自信,也是对国内刑法学教材建设现状的不满与反叛。联系张明楷教授的其他论著,如《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等,莫不让人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德日刑法学家的精神气质,这兴许与作者本人早年在国内接受的具有独特性的基础法学教育和曾经深度参与日本、德国多年的学研背景有重大关系。[7]“既立足于中国当今社会现实,又将论题置于世界刑法学之林思考;既评介中国的理论学说,又从学派之争的视角进行分析;既解释现行法条,又阐释规范背后的理念;既阐述刑法理论上的要害与重点,又预测和解决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与已经遇到的难题;既发表自以为成熟的见解,又提出自己尚难回答的疑问”(第二版前言),包括但不止于此,正因为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基础论、犯罪论、法律后果论与罪刑各论等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或许一种刑法法律现象有多家学说,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一书中能够列出有价值的别家观点,进而谨严而谦逊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轻易否认也不盖棺定论哪家观念是对的好的,而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决断。也摒弃了很多传统旧的刑法观念,注入了很多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坚持刑法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的观点,使刑法不仅引导一般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限制司法人员的权力;采取实质的犯罪论,立于客观主义立场,采取结果无价值论,坚持行为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是认定犯罪的实质根据的观点,使犯罪构成的整体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惩罚处罚的程度;根据刑法学的知识特点与规律,按照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的要求重构我国犯罪论体系,以确立科学的犯罪认定模式等,他的刑法学研究全面、细致、前瞻,涉及刑法学中的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等,抉微发隐,深考精思,故而以刑法解释见长、将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结合起来的《刑法学》一书获得了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欢迎与推崇,这种“两边都叫好”的现象在中国法学界是极为难得的,也很少见!“我希望自己的教科书能够影响那些在内心里对他人观点的确信或怀疑、对自己认识的清晰或模糊具有感受能力的法科学生,解释他们能够想到的理论问题;也期待自己的教科书能够接受实务的检验,解决实务家们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第三版前言)著者如斯目标定位,显然是顺利达到了。市场的嗅觉最灵敏,市场也是检验产品质量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刑法学》从1997年问世以来,张明楷教授先后三次修订,每次修订都是一次自我超越,一以贯之地以刑法解释学为本体,发掘成文法的真实含义和内在欲望,在这十余年间,我国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不断出台,《刑法学》并没有因为“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变成一堆废纸,反而每次修订版本一经推出,因其作为中国刑法教科书所具有的少见的集学术性、思想性与前沿性于一身,“依然洛阳纸贵,学界竞相传诵,学士爱不释手”(第二版前言),长盛不衰。[8]这是作者基于“对刑法的解释是一个无限的、不断反复、不断更新的过程,不喜欢拘俗守常、不愿意拘文牵义的我,也只能不断更改观点、更新论证”(第四版前言)理念支配之下主动作为与从不停歇自己对于事实与规范思考的结果。就我本人,则是搜集收藏了张明楷教授《刑法学》迄今为止出版发行的全部四种版本(前三种版本作为“历史文献”使用,最新的第四版用于学习研究),从四种版本的《刑法学》中,结合张明楷教授每年推出的十余篇“小题大做”的重量级学术论文,[9]大体可以管窥到张明楷教授刑法思想嬗变、改弦更张、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同时,《刑法学》一书也可视为中国刑法理论发展与进步的一面镜子。一本刑法教科书,能够连续推出四版,且还在不断更新完善之中(从前面四个版本统计,张明楷教授每隔4到6年对《刑法学》全面修订一次),这在国外法律学界或许显得极为稀松平常,但在中国法学界对于一本刑法教义学说作品而言说是罕见绝不夸张。《刑法学》是张明楷教授的“精神乐园”(第三版前言),作者在这片园地里,“下笔作文,直抒个人情怀,何等愉悦!操觚染翰,伸张人间正义,好不畅快!”(第三版前言)而众多法科学子则在其中获取精神食粮,薪传而成长。
学术作品(包括教科书在内)不在于多,而要力求以质取胜,这样才能赢得尊重、赢得信任、赢得市场。有的时候,对于那些真正有知识增量与智性挑战的,一人一本,足矣!一本精品,就足以让人难忘!我国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李洪林先生在回顾自己过去的“理论工作”生涯时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10]诚哉斯言!法治中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法律人才发轫于法学教育的悉心培养,而高质量的法学教育呼唤一系列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的支撑。迈向民主法治国,我们需要一批真正名副其实的“精品”法学教科书,尤其需要学术功力深厚、充满学术思想、闪烁智慧光芒的专著式法学教科书。
——2015年1月5日午后 初稿于广州二层楼上
——2015年1月7日晚 修定于广州南郊淡月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