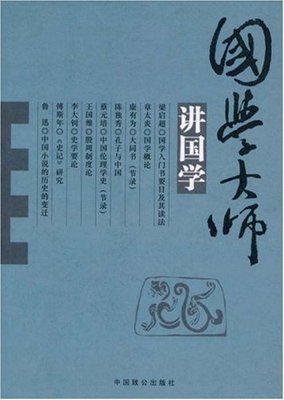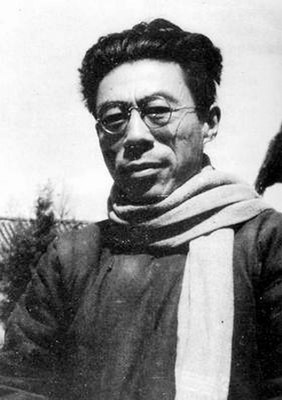民国初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股势力强劲的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对等级化的儒家学说展开激烈批判,由此掀起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延伸,新派学者在应对保守派挑战的同时,也开始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必须清理“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如何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就成为新旧人物共同关注的问题。
新旧之争引发一场运动
“国故”一词,古已有之,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至晚清则专指典章制度。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的,是章太炎,其《国故论衡》将语言、文学、诸子学等皆纳入“国故”范畴。“国故”一词遂流行起来,但“整理国故”真正成为一场大范围运动,是在“五四”前后。1919年初,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目的在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与此同时,刘师培等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口号,大唱对台戏。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系统回应《国故》主张,傅斯年在文末作“附识”以示支持(“整理国故”一词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国故》则刊发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双方你来我往,围绕“国故”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涵括国故与科学精神、国故在世界学术上的位置、国故的价值等诸多问题。新派批评旧派“追摹国故”、“抱残守缺”的倾向,旧派抨击新派“蔑视国故”、视国故已死的观点。不过,初期的争论焦点在于“国故”,而非“整理”,尚未涉及方法论层面,亦缺乏具体、明晰、详细的方针和计划。
将“整理国故”提升到一个新层次的,是胡适。他一再强调“国故”的中性含义,既非“国粹”,亦非“国渣”,主张用科学眼光看待传统文化。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系统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命题,从而正式竖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帜。1921年7月,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具体可行的方法,使“整理国故”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集体意见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正式发表,不仅反映了胡适本人认识的发展,而且说明“整理国故”已成气候,当可视作这场运动的宣言,同时意味着早期关于“国故”的争论,以守旧派失败告终。
此后,“整理国故”被大张旗鼓地提倡,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巨大波澜,形成持续十年以上的国学浪潮,不仅催生了众多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等)与学术刊物(如《国故月刊》、《学衡》等),而且创造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古史辨》等),直到新派阵营出现明显分化,唯物史观强势崛起,“整理国故”运动才渐次落下帷幕。而争论与交锋,贯穿着整个运动过程。只是,将其视作“昌明”国故的举措而鼓噪者迅速被边缘化,代之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
争论议题的拓展与深化
随着“整理国故”影响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如何理解“国故”、“国学”、“国故学”等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按照各自理解加以阐释,而这又反过来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陈独秀赞成研究作为“历史材料”的“国故”,但反对“国学”的提法,认为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吴文祺在强调研究“国故”必要性的基础上,反对将“国故学”简称为“国学”,认为会模糊“国故学”作为与自然科学性质相同的一门科学的界限。何炳松甚至列出来历不清、界限模糊、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囫囵吞枣等几大理由,力倡推翻“国学”才能真正“整理国故”。经过一番争论,当时学界大致将“国学”与“国故(学)”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粪土”与“香水”的混合体,为复古派大开方便之门,应被推翻;后者则属于科学范畴,可以纳入现代意义的学术分科体系中,做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此种界定,虽未必恰当,却不失为一种进步。
认为现代与传统根本不相容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普遍观念,而“整理国故”的兴起让很多人嗅到了复古的危险气息,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小说月报》曾就“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郑振铎、顾颉刚、王伯祥、余祥森等皆撰有文章,实际所探讨的已超出文学范畴,而是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大致都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尽管人们在将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联结起来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落实为具体方针、步骤时,因对科学性质和作用认识不同,彼此间的差异性随即凸显出来。胡适与梁启超关于“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的争论,背后即折射出探索路径的不同,前者目的在于以现代学术的分类方式去完成中国文化史,着眼点在建构新文化系统;而后者的出发点更多在于如何突出国学自身的特点,着眼点在当下,强调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人生哲学,必须“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更具代表性的,是两份分别来自南北两座学术重镇的整理方案的出炉,即:《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计划书》和《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前者的方法主要是以培养整理人才为主的“整理学术”和以征书、编书、辑书等为手段的“整理学术之材料”;后者则提出客观方面的“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和主观方面的“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时人对此多有讨论,但基本困囿于具体方法的完善,未能就科学法则是否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等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整理国故”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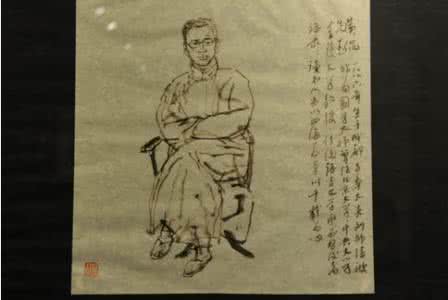
由于“整理国故”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使得这一运动本身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曹聚仁曾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很多人都对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展开过批评,事实上,批评的声音自始至终都不绝于耳。除守旧派的攻击外,主张完全西化者如吴稚晖就对“整理国故”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把“国故”看得一文不值,认为所谓整理毫无意义。此外,郭沫若、鲁迅、周予同、刘掞藜、成仿吾、陈源等都曾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尤其是接受唯物史观后的郭沫若,尝试将“整理国故”纳入到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中去,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开辟了一条新的史学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见或是从某一方面提出不同看法,或是对某些问题提出不同见解,或是对某些成果提出异议,很少有从整体上反对整理国故者。而面对种种非议,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的胡适,则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发声,给这场运动以持续的引导和促进,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思。
“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争论,人们对“国故”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位,抛弃了故步自封或全盘西化的极端做法,并以卓著的成绩使得科学观念深入人心。虽然人们基于不同学术理念做出相异的价值判断和研究路径,但殊途同归,皆以“再造文明”为终极目标,即:以现代解喻传统,将“国故”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从而改变以人为中心、不以学为中心的传统,实现中西学术的对接与整合,无疑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其影响至深至远。当然,这场超出学术范围,形成广泛社会参与的思想论争,也产生了诸如滥用“国学”、疑古过甚、走向琐碎等负面影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