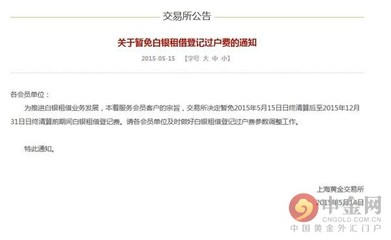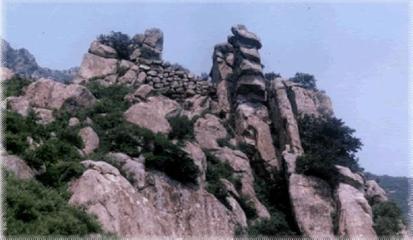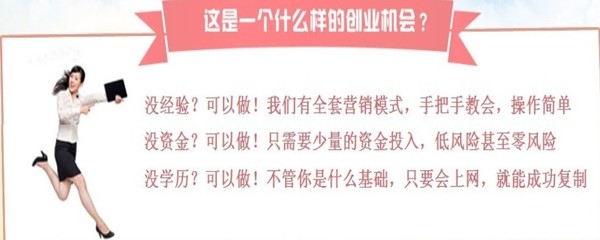作者:吴钩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听得我的心都碎了,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我这么多年读史的印象,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以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一个人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

——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说:“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告讦成风。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结果,告讦之风大兴,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议论,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
因此,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议加黜罚”。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诏令刑部开具取旨”。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说的是,拒绝告密、抵制告密,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哩。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