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曾推送刘小枫老师有关邹谠先生文章一篇,附于文末,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
邹谠先生(1918-1999)
黑格尔说过,熟悉(familiarity)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了解(knowing)它。当我阅读邹谠先生的著作“中国革命的阐释”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黑格尔的这一观察。多亏邹先生的洞察力,使我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曾经自认为是很熟悉的方面产生了新的有趣的认识。
举例来说,我以前从未觉得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一个特别的创新。这种策略对农民运动而言似乎是一条自然的路径。因为农民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从农村开始,然后通过夺取城市而掌握政权的。但是,邹谠先生做出了如下诠释:并非所有农民运动都把确保占领农村根据地作为比夺取大城市更为优先的考虑。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早期就夺取了南京,并宣布建立了新的政权。此后,他们把农村输给了由乡绅所组织的、并为国家军队所支持的当地民团。所以,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是政府的军队包围了由农民起义军所占领的城市,并最后击败了农民起义军,而不是正好相反。(Tsou,2000:214)
出乎意料吧?“中国革命的阐释”的读者会经常为邹谠先生在他们“熟悉”的事情中所发现的新的含义而感到惊奇。
邹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他在1994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午餐会上的讲演报告的草稿。为了领会这篇讲演稿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了解邹谠先生一贯致力于借鉴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诠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建国。他的第一本获奖著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不仅应当作为外交史领域的经典来读,而且应该被视为邹先生从复杂的国际背景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尝试。同样的,他后来着重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作品也可以这么理解。(见Tsou,1986)
邹谠先生知识探索的两个核心问题是:(1)我们如何诠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国?(2)在中国革命发生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在1988年退休之后,邹先生致力于发展一个综合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除了新近可以获得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材料,他还广泛收集并大量阅读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文献。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宏观历史变迁”的“微观机制”这一普遍性命题的最初构想。如果不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加全面详细的研究成果。然而,无论是就其所包含的启发性洞见,还是作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记录,能够出版邹谠先生的午餐会讲演稿都是非常可贵的。正如邹先生在文章的结束语所言,“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后果,已经辩论了两个多世纪了。中国革命也值得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给予类似的关注。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Tsou,2000::235)。
我很有幸能够在邹谠先生的晚年与其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下面是我对他文章中关键概念的理解的说明。希望能够促进对邹先生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思想的进一步探讨。
关于 “普遍性命题”
邹谠先生文中的普遍性命题如下:中国的个案表明,政治行动者所选择的创新、系统化和策略互动过程,是直接的和容易观察的微观机制;这些微观机制导致宏观历史变迁,特别是一个政治制度转变为另一个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Tang,2000:211)
这里“一个政治制度转变为另一个政治制度”指的是从帝制时代传统的威权制度转变为现代的“全能主义”党国制度(“totalistic” party state)。在传统的威权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到县一级为止。而在现代全能主义国家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无限的。根据邹先生的观点,这一历史转变的发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全面危机”导致了由地主阶级、儒家学者和官僚群体所构成的传统三元权力结构的崩溃,因此引发了围绕着国家的革命性重建的全能主义回应。邹先生特别关注这一革命的微观机制,即:“政治行动者所选择的创新、系统化和策略互动过程”。邹谠先生对这些微观机制的关注使他的观点有别于斯考切波(1979)的“结构主义视角”。斯考切波和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一样,认为“革命不是被人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来临的”[i]。这一差异也解释了邹谠先生对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作品的欣赏,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的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结构性条件与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我将在讨论邹谠先生的全能主义概念之后,对其所界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微观机制进行检验。
邹谠先生手迹
关于 “全能主义”概念的注解
邹谠教授在他文章末尾的注释中解释了全能主义这一概念: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两个不同方面。当政权的类型保持不变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可以发生重大变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一概念的基本错误,如同它被经常使用的那样,在于它错误地把政权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运用这个概念的人:(1)他们看不到除了革命之外,有其它激进变化的可能性;(2)他们不能充分解释那些由当权者发起或者至少是支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改变。1983年,当我得出上述结论后,我就开始用“全能主义”这一概念去专门刻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就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跟政权类型分离开了,而不是像原来所隐含的它们是自动连接在一起。(Tang,2000:236)
为了领会邹谠先生引入全能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因,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虽然经过过去的二十年改革,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已经自由化了,但是用全能主义这一概念来刻画中国政治制度仍然是有用的。根据邹先生的观点,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最典型的特征是没有任何法律,道德,或者宗教上的限制可以阻止国家干涉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任何领域。这并不意味着全能主义国家总是侵入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关键在于国家能够根据领导人的选择而随时随地地干预社会。与之相对照,自由主义国家的权力侵入社会和个人生活时要服从法律或道德的约束。
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政治制度称作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呢?邹谠先生在1986年接受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的致辞中说,中国的全能主义是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并被用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却是以消灭或阻止社会革命为目的(Tsou,1994)[ii]。因此,区分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有历史原因的。[iii]不仅如此,做出这一区分还有更重要的理论缘由。
我们必须记住对于邹谠先生来说,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两个彼此分离的方面。在一些“自由主义国家”,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能比其它的“极权主义国家”更广泛。一个支持此论点的案例是比较自由主义的瑞典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对经济领域的干预。瑞典政府比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政权更广泛地卷入经济领域。更重要的是,那些接受极权主义概念模型的人与掌握邹谠先生的全能主义概念模型的人相比,更易于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在为前共产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改革策略时,那些将这些国家视为极权主义的人倾向于支持“休克疗法”(如已经应用于俄国的那种范式)。这是因为他们把政权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为一体,看成是同一件事。因此,他们认为国家-社会关系方面的渐进改革是不可能的或不是理想的。俄国休克疗法的首席顾问以政治理由而不是经济原因而极力倡导快速的私有化就是很说明问题的。邹先生对政权类型和国家-社会关系上的概念区分打开了通过逐渐重塑国家-社会关系来改造政权类型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保留甚至强化国家的某些功能。这一洞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领会邹谠先生引入全能主义这一新术语的视角是注意到其“经验性”而非“规范性”的本质。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规范意义上有强烈的负面色彩。但是全能主义这一概念被邹先生用作经验上描述政治制度的工具。在规范意义上,全能主义的政治运动或政权可以是正面的(例如在二十世纪上半页作为中国应对外国威胁和社会危机的手段),也可以是负面的。因此,邹谠先生对于全能主义概念的经验性的应用和亚历桑德罗.皮泽诺(Alessandro Pizzorno)的“绝对主义政治”(absolute politics)的概念类似:
作为关于“变化中的政治边界”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皮泽诺将“绝对主义政治”定义如下:对于践行政治承诺和执行政治意志完全没有为其设定任何边界。社会中的所有事物都被置于政治之下,通过政治诠释,而且被政治看作可转变的,我将呈现这一图景的状态称之为“绝对主义政治”。…因此,绝对主义政治不是作为,或不仅仅是作为,代表组织一个政治制度(a politicalsystem)的某种模式,而是作为一种构想并可能管理能带来所期待的社会形式的工具的模式。(Pizzorno,1987:29-30)
邹谠先生的全能主义概念在规范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也类似皮泽诺(Pizzorno)的绝对主义政治。正如皮泽诺所说,在现代国家,政治为它自己和其他活动设定边界。为了界定什么在政治领域之中,什么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需要法律或废除法律,因此需要政治决定,政治活动和辩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政治的“反射性权力”(reflexive power),政治的绝对性概念就根植于其中。如果政治能够决定自己的边界,那么有时候它就可以过度扩展,或者说不设定任何边界。(Pizzorno,1987:28)
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能主义政治也存在和绝对主义政治一样的两难困境:在全面危机时刻它有创造新政体的变革功能,但是也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内在危险。[iv]
还有另外一个领会邹谠先生全能主义概念的视角是透过马基雅维利来观察。学者们长期以来对于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同时写了“君主论”(提倡“新君主”)和“李维史论”(倡导共和政体)感到困惑。不久前,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99)令人信服的论证了两书之间所谓的矛盾,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两本书是关于两个“时刻”:在第一个时刻,新君主凭借“绝对权力”创造了新的政体;在第二个时刻,新的政体通过共和的形式巩固下来。邹谠先生的全能主义概念表明中国革命尚未达到它的“第二个马基雅维利时刻”(second Machiavelli moment)。[v]
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关于 微观机制
邹谠教授界定了中国革命的三种基本的微观机制:政治行动者的创新、系统化和策略互动过程。
第一个创新是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之所以认为这是一种创新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俄国模式中(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农民被蔑视为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进行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巨大成就。就像邹先生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1977:3)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农民革命这一概念的诞生地。”然而,邹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创新本身也蕴含了1949年后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问题的种子。如他所说,对于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而言,这种依靠农民的革命的众多后果之一,就是这个政权的巨大科层体系主要是由在农村渡过他们的最好年华的干部或是由农民出身的干部所组成。这个政权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去把由这样的干部组成的科层体系转变为技术上有能力的和现代化的组织。(Tsou,2000:213)
对这一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双刃性的认识是邹谠先生敏锐的思辨力的又一明证。
邹谠先生讨论的第二个微观机制是“系统化”。对于他来说,为了应付长期革命过程中某个具体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在不同的时间或处理不同的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创新之间,必须具有某种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会使各种创新能形成一个总体效应,而不至于相互抵消。(Tsou,2000:222)
从分析的角度而不一定是从时间顺序的角度来看,系统化过程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从上到下的联系,横向的联系,和从下到上的联系。邹先生对系统化过程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从下到上的联系,他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起源来阐述这一机制:第三种形式的系统化过程是“从下到上的联系”(也就是从手段到目的、或是从在较低层次操作的原则到在较高层次操作的原则)。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在抗日战争以及在敌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之间的高度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中共采纳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即,所有的军队单位(和组织)…“无条件地服从相应的各级党委”(Pang Song and Han Gang,1987:4)。1949年之后,这一原则继续得到肯定和执行。1962年,它被提升为整个政治制度的一个普遍原则。…(在每个领域),党都起着领导作用。(Pang Song and Han Gang,1987:7)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能主义制度起源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对社会革命的追求。(Tsou,2000:223)
这一制度的谱系有着深刻的政策含义。许多人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是这个政权固有的特征。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就能够开始想象实行党的领导的新途径。
邹谠先生讨论的第三个微观机制是“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他认为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产生了创新和系统化的过程。为了全面解释策略互动的机制,邹先生借鉴了博弈论的深刻洞见。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专门分析不同人之间策略选择互动的分支学科。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赢者全得”的博弈模式。从袁世凯1915年复辟帝制到八十年代末,主要的政治冲突总是以一方的完全胜利为结局。邹先生承认“赢者全得”概念中的“全”不够精确,因为有些情况下不能完全从字面上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博弈中也可能是指不同的事情。但是邹先生试图通过“赢者全得”博弈所传达的实质洞见是不难把握的:中国的政治权力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在政治行动者的意识中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我这篇简短的导读无法涵盖邹谠教授原著的丰富内容。我仅仅探讨了他文中几个关键概念,还没有涉及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主题——即“宏观结构”对个人选择的制约。他说,有一组观察是这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1927-1946年间的非激进化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其在1949-1961年间的重新激进化的过程和结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些真实的事件。这些事件至少可以描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下人的选择的范围;在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哪些选择可以导致更大的成功;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对人的选择设置了哪些绝对的界限,一旦超越了这一界限,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仔细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个案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对结构约束与人的选择之间的界限这样的问题,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命题。
邹谠教授的文章值得仔细研读,文章不仅提出了重要的本质问题,而且也展示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相互促进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注释
[i]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一书之后已经改变了或至少是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其“结构主义视角”。她现在承认革命的领导者和政党在动员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Skocpol,1994::227)。
[ii]付世卓(Fewsmith)1995年在当代中国杂志发表的“对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书评”是对邹谠1994年出版的那本著述很好的评述。
[iii]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概念比较可以和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比较相联系,对于后者这对概念最近一个很有问题的看待方式,参见Furet(1999)。
[iv] Jon Elster,邹谠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好友,对于全能主义有如下评论:全能主义的理念也许可以用行为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理论来理解。即使当政府没有被下面,被人民所限制,它也可能尝试通过采用一种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的形式来限制其自身。但是,当所有权力都集中于政府手中时,它可能无法抵抗短期利益的诱惑。(1999年11月,和作者的个人交流)
[v]邹谠在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文中(Tsou,1986:115)参考了阿尔都塞。如果邹谠教授能够活着看到阿尔都塞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出版,他可能会注意到了自己的“全能主义”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第一时刻”的类似性。
参考文献
刘小枫丨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上)
刘小枫丨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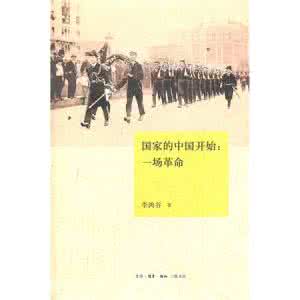
保马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