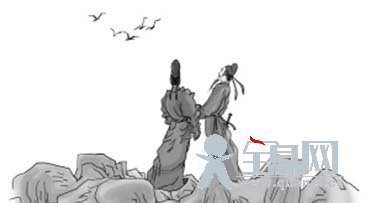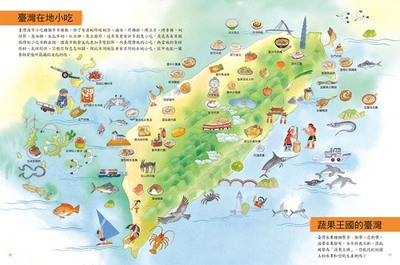由官转民
老北京的文化可以明显地分为官场文化与平民文化,在饮食上这种区别同样十分明显。满汉全席、孔府菜、谭家菜等宫廷菜、官府菜与满城都有的北京风味小吃:豆汁、爆肚、炒肝儿、灌肠、茶汤、豆腐脑、烤白薯、凉粉……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决不是属于一个系统,前者属于宫廷文化、官场文化,后者属于平民文化。慈禧太后固然也有尝点北京小吃的时候,但那是因为吃腻了肠子,想换换口味,或者出于猎奇的心理,平民百姓则做梦也甭想尝尝满汉全席、孔府菜和潭家菜。
遍布京城的饮食店铺也与老北京各阶层人士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大饭庄是王公贵族、高级官僚设宴的场所,饭馆是中下级官吏、商人请客便酌的场所,二荤铺是平民百姓吃便饭的地方,“大酒缸”是平民百姓买醉的地方。有钱人或许心血来潮会坐在街头弄碗豆汁喝,但极少有谁会进二荤铺吃花卷炒菜。至于街头的小吃摊则是穷人充饥解馋的场所。
进入民国后,饮食业的等级划分发生了变化,随着王公贵族的没落,大饭庄的生意越来越难做。1928年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南迁,大批官僚政客的离去,大饭庄纷纷关张停业,到了1940年前后只剩下少数几家。与此同时,风味饭馆先后兴起,比较著名的有正阳楼、丰泽园、东来顺,最有文化意味的是仿膳茶庄和谭家菜。
1925年,昔日的皇家御苑北海经过数年修缮得以竣工,改为公园对公众开放。曾在御膳房菜库当差的赵润斋,约了御厨王玉山、孙绍然、赵承寿等人,在北海的北岸合伙开了“仿膳茶庄”,所谓“仿膳”,自然是“仿御膳房”的意思。民国之前,谁要是想在紫禁城外再一家御膳房,那就是凌君之罪,连脑袋都保不住。到了民国时期,清帝退位,昔日的排场再也摆不起,御膳房里锅冷灶凉,御厨们只得走出宫门,走入民间,另找饭辙。
清朝皇帝虽然下台了,昔日宫廷的饮食文化仍然对广大民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开仿膳的想法绝对是个好点子。这个想法其实在赵润斋的心里转了很久,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是因为前些年辫帅张勋刚闹过一场清帝复辟的丑剧,万一大清朝又恢复了,自己的脑袋还要不要?直到溥仪被驱逐出宫,北海改为公园,赵润斋这才将多年的计划变为实际行动。
仿膳茶庄开业后,主要经营精制的宫廷小吃和一般的炒菜,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清宫名菜,如清炖肥鸭、樱桃肉、西瓜盅等。对宫廷美味仰慕已久的游客们,也不在乎多花些钱,仿膳的生意果然红火。虽说光顾仿膳的大多数是有钱人,穷人一时还不敢问津,毕竟也体现了“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观,比之昔日非帝王赏赐而不得食的封建特权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御膳房到仿膳茶庄,其中的文化意味不是很值得人们品味吗?
潭家菜的商品化也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光绪年间,广东南海人潭宗浚在翰林院任编修。此公是个出了名的老饕,对本职工作不上心,专门喜欢宴请同僚。他还亲自负责采买原料,京官的薪俸本来有限,他也不买房置地,把钱全用来买山珍海味和聘请名厨了。谭家菜既融汇了各菜系的精华,又独具风味,尤其擅长鱼翅菜,在京城留下了“戏界无腔不学潭,食界无口不夸潭”的口碑。
谭宗浚身在官场,却颇有几分清高,由于不善于应酬,得罪了顶头上司,先是被发往外地当官,后又托病辞官,死在归乡的路上。

潭宗浚的儿子潭璩青也是一个美食家,他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到北平沦陷时期,一直在京城当个小官,他家几乎天天高朋满座,盛宴常开,虽然变卖家产,也难以为继。谭璩青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改宴请宾朋为有偿服务。
潭家菜每桌的价格不低于一百块大洋,十分昂贵,但因采用真材实料,精工细制,慕名而来者仍然很多。想品尝潭家菜的人,必须转托与谭家有交情的人代为预订。谭家还有两独特的规矩,一是所宴的客人无论与谭家是否相识,均需在宴席上给主人谭缘青留一个座位,以示谭家并非以开饭馆为业,而是以主人的身份“请客”;二是无论订宴席的人权有多高,都要进谭家来吃,谭家概不出外设席。
谭家的这些规矩可谓用心良苦,中国的儒家历来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著名的孔府菜也不是衍圣公亲自下厨做的。历代士大夫中虽然也有亲自下厨烧菜的,但只是自娱自乐,饭馆里的厨子则被视为“五子行”之一,是下九流。谭氏父子能够将孔圣人的训诫置诸脑后,亲自采买,亲自烹饪,在家道中落的处境中对外承接宴席,变相经营赚钱,确实需要有“离经叛道”的勇气。对于谭家因放不下官架子而制定的那些“规矩”,北京人也没有采取苛求的态度。
谭家菜刚开始对外承接宴席时,只设晚宴,每晚两三桌。后来中午也设宴接客,仍然应接不暇,据《四十年来之北京》一书记载:“(谭家菜)声名越做越大,耳食之徒,震于其代价之高贵,觉得能以谭家菜请客是一种光宠,弄到后来,简直不但无‘虚夕’,订座的往往要排到一个月以后,还不嫌太迟。”
说到北京城里的中小饭馆,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有文字为证:
“一进饭馆,迎面火焰三尺,油星乱溅。肥如判官,恶似煞神的厨役,持着直径二尺,柄长三尺的大铁勺,酱醋油盐,鸡鱼鸭肉,与唾星烟灰蝇屎猪毛,一视同仁的下手。煎炒的时候,摇着油锅,三尺高的火焰往锅上扑来,耍个珍珠倒卷帘。勺儿盛着肉片,用腕一衬,长长的舌头从空中把肉片接住,尝尝滋味的浓淡。尝试之后,把肉片又唾到锅里,向着炒锅猛虎扑食般地打两个喷嚏。火候既足,勺儿和铁锅撞的山响,二里之外叫馋鬼听着垂涎一丈。这是入饭馆的第一关。走进几步几个年高站堂的,一个一句:‘老爷来啦!老爷来啦!’然后年轻的挑着尖嗓几声‘看坐呀!’接着一阵拍拍的掸鞋灰,邦邦的开汽水,嗖嗖的飞手巾把,嗡嗡的赶苍蝇(饭馆的苍蝇是冬夏常青的),咕噜咕噜扩充范围的漱口。这是第二关。主客坐齐,不点饭菜,先唱‘二黄’。胡琴不管高低,嗓子无论好坏,有人唱就有人叫好,有人叫好就有人再唱。只管嗓子受用,不管别人耳鼓受伤。这是第三关。二黄唱罢,点酒要菜,价码小的吃着有益也不点,价钱大的,吃了泻肚也非要点不可。酒要外买老字号的原封,茶要泡好镇在冰箱里。冬天要吃鲜瓜绿豆,夏天讲要隔岁的炸年糕。酒菜上来,先猜拳行令,迎面一掌,声如狮吼,入口三杯,气贯长虹。请客的酒菜屡进,惟恐不足,作客的酒到杯干,烂醉如泥。这是第四关。押阵的烧鸭与焖鸡上来,饭碗举起不知往哪儿送,羹匙倒拿,斜着往眉毛上插。然后一阵恶心,几阵呕吐。吃的时候并没有尝出什么滋味,吐的时候却节节品着回甘。仁丹灌下,扶上洋车,风儿一吹,渐渐清醒,又复哼哼着:‘先帝爷,黄骠马,’以备晚上再会。此是第五关。有此五关而居然斩关落锁,驰骋如入无人之地,此之谓‘食无有勇’!”
“美满的交际立于健全的胃口之上。”这当然是不易之格言!
“我们还是回德胜门,还是……现在已经快三点钟。”孙八问。
“我看没回去的必要。”老张十二分恳切的说:“早饭吃了你,晚饭也饶不了你,一客不烦二主……”
以上文字引自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的第十回,写的是富户孙八在北京城里的九和居饭馆请客的情景。老舍以夸张、戏谑、讽刺的手法,描绘了一幅老北京饮食文化的风俗画。
北京人的饮食文化讲排场体面,不讲经济实惠,讲口腹之欲,不讲清洁卫生(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俗话为证),讲暴食暴饮不讲健康营养。最后一条是:只讲究饮食,不讲究排泄。有个日本人来到北京后写下观感:“北京城内之不洁,虽尝有耳闻,然堂堂一大帝国之帝都,如此不洁则未必想象……街路行人繁忙场所,市民据路之左右大便者,不遑胜数,其多者五人乃至十人,列臀为之,其为者不以人见为耻,通行男女见之者不为怪。……大便尚然,小便者则到处为潴,为行潦。路上人粪之外,骆驼、马骡驴犬豚等之粪有之,粪秽叠叠,大道狼籍。”(引自宇野哲人:《第一游清记》)
今天的北京人看了这段文字脸上大概会发烧。旧时北京的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最早的公共厕所出现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是由外国侵略者下令修建的,北京人称之为“官茅房”,这也许是八国联军做的惟一的一件好事。事情虽然不大,其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却是耐人寻味的。
许多北京人是精明的消费者,他们对各种消费品的质量、品种、价格、制作工艺十分熟悉,他们会花钱,但是他们却不会挣钱。话剧《北京人》里江泰谈到他的内兄曾文清“最讲究喝茶。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茶对我们只是解渴的,可一到他口里,就会有无数的什么雅啦,俗啦的这些个道理。然而,这有什么用?他不会种茶,他不会开茶叶公司,不会做出口生意,就会一样:‘喝茶!喝茶喝得再怎么精,怎么好,还不是喝茶,有什么用?”
江泰自己是个美食家,“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种顶好的地方去吃。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小地方哪,像灶温的烂肉面,穆家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三妙堂的合碗酪,恩元德的包子,沙锅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没有一个掌灶的、跑堂的、站柜台的我不知道,然而有什么用?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开馆子,我不会在人家外国开一个顶大的李鸿章杂碎,赚外国人的钱,我就会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令人诧异的是:有的北京人竟然雇人养金鱼、养花、养蟋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