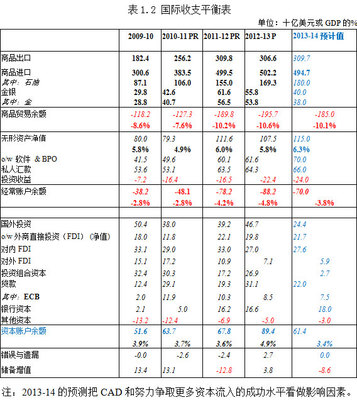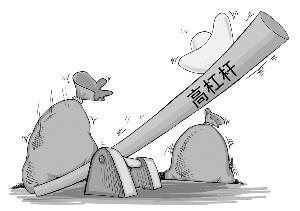一只蝴蝶是一朵花的灵魂
文/九妹
每一只蝴蝶从前都是一朵花的灵魂,在花丛中飞舞是在寻找前生的自己。
——张爱玲《临水照花》
一
许是骨子里的天性,不能书画的我却喜欢笔墨纸砚,一支支笔,一块块墨,一张张纸,一方方砚,成就了1个个艺术家,成就了1种种艺术流派,日日润泽其中,竟觉得心灵已洇得清软幽活,反而是身骸俱松,得到从未有过的畅意。
因了喜欢,不忘老师梦记的一则短文:
明代的马湘兰偶然得到一方绿玉宋砚,背面刻了1个叫阿翠的女子,湘兰竟然觉得她的眉目与自己相似,更可怪的是右边的脸颊上也有1个痣,湘兰疑问:“妾前身耶?”她还认为,这个阿翠可能是苏翠,同样是烟尘女子。如果是她的话,湘兰说,她宁可剃掉一头秀发遁入空门,“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
后来,我得知这就是《骨董琐记》记载的“阿翠砚”。这样的砚,是骨董,有故事,拿在手里值得反复品玩。“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读文,看石,我自言自语:何时也碰到一方砚呢?
几个月后,果真有一方砚台绕过千山绕过万水端摆在我的书桌上。
那是一方满金晕的歙砚。砚石质地缜密、结凝,金晕巧妙地雕琢了一株牡丹,老株着花三朵,琢工浑朴舒展,花儿绽放的方向还翩跹着一只玉蝴蝶。此砚为江苏的七哥所赠送,他来湘西看自己资助的2个学生。我打开木盒子,小心地取出砚台,开心地笑:“送砚给我啊,看来我终有一天会画画的!”站在旁边的七哥,一脸疑惑:“你不是早就在画画吗?”我与七哥认识已经好几年了,情同手足,但他并不知道我尚未画过水墨,当然也从来没有用过砚台了。这歙砚,是我的第一方砚台。
七哥两年前路过歙县,朋友与歙县唯一一家做彩砚(金晕)的店铺老板是兄弟,遂执意要送一方歙砚给七哥,七哥知道歙砚很贵,盛情难却,就又买了一方。我是在网上见过七哥的两方砚图,羡慕得睛目放光,只是一直不知道他买下的那方砚是准备送给我的。
七哥千里迢迢背着这么一块砚石,硬邦邦的,沉甸甸的,除了喜欢之心,更多的是感动之情。我曾见过一位老画家的数十方砚台,端砚、歙砚,还有湘西本地的水冲石砚,新新旧旧,各式各样,其中不乏名家制作。面对那些砚台,我却没有丝毫的喜爱之念。也有做砚的朋友说要专门制一方砚台给我,我也没有丁点的拥有之想。而这方歙砚,我喜欢的心情如今生照见的前世。有人说万物皆有缘,许是真的吧。

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WWW.aIhUaU.com)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七哥还有几方端砚,均不为收藏,是曾经邂逅相遇的喜欢,现时挥毫书写的欢喜。携砚访友,更显文人相会的1种清雅。七哥说砚上牡丹和蝴蝶是有寓意的。我懂,但不愿去想善祷善颂,我喜欢它们被雕琢得比自然还自然,花开灵性,蝶飞野趣。
吴从先《小窗自纪》里有句话说得真好:“风流无用,榆钱不会买宫腰;笔砚有灵,书带亦能邀翰墨。”中国文人讲究怡情养性,风雅之余,要的其实是1种风骨。喜欢阿翠砚的马湘兰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能诗善画,特别是画兰堪称一绝,不知道她书画之际是谁的手指捏着墨在砚上磨,是自己,是丫环,抑或是她相恋一生却未结夫妻的才子王雅登?这一番臆想,如是湘兰疑问“妾前身耶?”
我亦想着自己就是那个磨墨人,若说“红袖添香”是千古文人佳客梦,那么“绿衣捧砚”则自是引人暇思绮想,一圈一圈轻轻地磨,自是磨得满砚水墨,一片墨荷,一树白梅,几株水仙,几根兰草,得水而活,寄意生风,又是别样的婉约散淡,一以径流的端庄森严,蓦然转身,却是灯火阑珊的幽远深隐。那份心,那份情,又会有意无意的令人去想阡陌过往,想起美好的时光许是会心一笑,想起无心的过错可能蹙眉神伤,喜、怒、哀、乐,或独自存在,或是杂糅在一起,思绪随之蔓延,心也随之飘摇,还有那生动的表情。
凝眸砚上牡丹和蝴蝶,我幽幽地感叹:一只蝴蝶是一朵花的灵魂。
二
等待七哥到来之际,我1个人呆在家里画石头画。
自从在陌生城市中租住房子后,我已经很长一段时日没有画石头了。以前画画的石头,都是在家乡酉水河边捡的,每次回乡都会拾捡几个偏平光滑的石头,装在大塑袋中很沉重,由爱人哼哧哼哧地搬回家里,我想画红楼女子之际就拿起1个石头,坐在院子的石榴树下边晒太阳边涂抹绘画。
前前后后,在石头上画了四五年了吧。当然,我这也不能叫绘画,就是因了从小就有的美术梦而以自己的方式涂抹着梦的色彩,画红楼女子也是让梦中的自己走进朱阁黄梁,邂逅美丽,相遇才情。
今年三月的1个周末,阳光正好,心情正好,就想画石头了。画什么呢?耳际飘响着一位友人的话:画几个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啊。我是迷沈从文作品迷了很多年了,想着这位也有1个九妹的文学大师,以及“二哥”与“三三”的幸与不幸,突然地就想起了他们的四妹——张充和。
张充和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当代小楷第一人”,我对张充和的认知,是缘于其三姐夫沈从文先生。1988年沈从文辞世,张充和写的挽联刻在墓碑上:“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四句联语凑起来正好是“从文让人”四字颂辞。我每次去凤凰听涛山沈从文先生墓地,凝眸五彩石上镌刻的十六字,心里以为这个四妹是最懂二哥的。后来,张充和还给《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别集》题了封面,“在那些秀逸的笔划间,谁知道凝聚了充和多少中夜的苦思和挥毫的心力”。我在读沈从文作品时,便也读了张充和的《古色今香》、《曲人鸿爪》,两本书记录了才女的琴曲书画,和1大批文人、曲人的往事。其中,我尤爱张大千创作的一幅画。1938年,张充和经武汉等地辗转来到成都。一日张充和与舞蹈家戴爱莲同去拜访张大千,在张大千家中,戴爱莲跳了1个舞,张充和唱了一段昆曲。张大千当场挥毫,画了张充和的背影,画中的张充和执扇,梳理的是1个古装的发式。这便是著名的《充和曲影》。画中曲影,如张充和的为人与修养,清淡之中,还有1种高雅气质,而这种气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