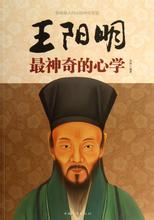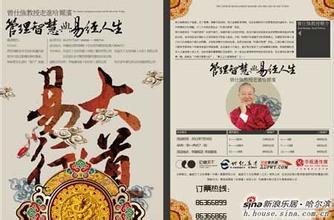《发现心灵的智慧:王阳明人生哲学感悟》
《发现心灵的智慧——王阳明人生哲学感悟》 第31节 作者: 明朗之阳光
给心灵减压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 ——《传习录》
陆澄问:“圣人能够应变无穷,难道也是预先研究过的吗?” 王阳明回答说:“圣人怎能研究得那么多呢?圣人的心就象明镜,心中明明朗朗,就能随着自己的感受而灵活自如地应对事物,无物不照。没有已过去的事物尚停留在心中,也没有还没到来的事物预先具备在心中的情况。” 王阳明认为,人只有认识了自己,心灵超然自在,才能在处理各种事务时悠游自如,从容不迫,应变无穷。 王阳明指出,圣人正因为他们的心象明镜一样,随感而应,过而不留,所以才能对各种繁多的事务应变无穷。
在今天这个信息量空前爆炸,日趋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言,我们更需要以这种“心如明镜”的心态来应对,才会生活得更轻松快乐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似乎已超出个人承受能力的繁重生活和工作,我们应该暂时放慢忙碌前进的脚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自己,改变自己,让心灵得到升华,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空前强大的生活压力。 现在社会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我们拼命地努力,步伐越来越快,再也不愿等待。尽管我们被过快的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但就是不愿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我们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殊不知,古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我们想快,但如果总是保持一种急躁的心理,我们就失去了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就会感觉不到快乐,就会以更糟的心情来对待生活。而这种消极、负面的情绪,只能带来低下的工作效率,令我们迎来更多的失败和不幸。试想一下,当我们饱受失眠的困扰,当我们精神涣散、心情浮躁时,我们能有多少把握做好当前的事情呢?所以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们在追求真正的快乐和成功的时候,却正在和快乐和成功擦肩而过。 精神上的压力,对于身心健康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压力长久地盘踞在心头,轻者使人情绪浮躁,遇事控制不住自己;重者则会使人患上抑郁症,进而危及生命安全。 在当前的社会里,我们要做的事太多,我们每天疲于奔命,心灵都已经被这些或那些要解决的事缠绕得紧紧的,再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本来状态,所以我们越来越被物质化了,那种和谐、实在的生活感受离自己越来越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永无何止地给自己加压了,因为人的心灵虽然有很大的承受能力,但其所能承受的压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人的精神就容易崩溃,引发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后果。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心灵的档次提升一个层次,以一种下意识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因为我们的心灵本来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睿智,在没有外物干扰、宁静平和的情况下,它能以更高的效率、更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种洞察力和睿智呢?这就要求我们每天抽一点时间出来反躬自省,与自己的内心多沟通、交流,那样我们就会多一分宁静和洒脱的心态,洞察力、智慧和能力也就会随之而浮现出来…… 任何事物都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我们的心灵也不例外。面对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我们可用的时间又不会因此而增多,假如我们还要以不断加快步伐来应对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超出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放下过于沉重的包袱,轻装上阵,以一种自然而从容的心态来应对全新的挑战。
生命说到底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追求心灵快乐与幸福的过程,如果人生中只剩下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活得没有一点质感和幸福感,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从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社会学家卡尔??里夫金考察中国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个词,成功和拼搏……我很奇怪,他们连快乐都感受不到,却想追求幸福。” 其实要想得到快乐和幸福,也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把自我放下来了,不再去攀比和计较什么,心灵进入一种宁静从容的境界,这样才能使我们获得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而只有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做事,才可以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打下基础。
《发现心灵的智慧——王阳明人生哲学感悟》 第32节
作者: 明朗之阳光

阳明先生的心学,强调“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
对于王阳明的“心即是理”的观点,这是最为后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不解的,也是攻击得最厉害的。拿上面“岩中花树”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唯物哲学家”们正愁对“主观唯心主义”没有适当的例子来讲解,一看到《传习录》这段话,一下就象逮到了一个宝:好!踏破铁鞋无觅处!这真是一个阐述主观唯心观的最佳反面教材!至此,王阳明“主观唯心思想”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算是摘不摘不掉了。 王阳明先生的友人提的问题实在十分尖锐,他知道王阳明是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便指着花树问:“你老兄喋喋不休地鼓吹天下没有心外之物的学说,我来问你,象这些花树,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吧,它们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问得妙极了,就象替我们问的一样。现代的唯物哲学家们最不理解的也是这一点。 说实在的,王阳明友人说的似乎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宇宙间各种事物的存在的确与我们的心在不在没有什么关系的啊,用一句比较著名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一个人死了,地球都照样转,万物都照样存在。 王阳明作为一个拥有高智商、高智慧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看过了太多的生死之事,绝对是不会连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也弄不懂吧。我觉得,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诘难先生的“心学”是胡说八道,是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十分可笑而荒唐的。 我们知道,马先生的辩证唯物论是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发展而来的,只是由于马先生一生投身于革命斗争,致力于思辨哲学,没有黑格尔那种天才的“唯心”体验,所以马先生自然而然地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中的“绝对精神”等“唯心”内容给剔除了。 按王阳明先生的说法,黑格尔算是一个有天赋、有圣人之资的天才,也许他没有进行过专门系统的修身养性的实践,但他在偶然中也体验到了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齐观的唯心境界,所以他能提出“绝对精神”的唯心学说来。而王阳明先生更进了一步,他是悟道了的人,对良知的本体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术语从他口中说出,自然也就不足为异了。 王阳明对于“岩中花树”的回答,颇有意思,后世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其实我也不理解。但我在这里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 在儒、释、道中,老师对学生的教育,都是非常讲究一个契机的。即只有你的心灵境界到了能够理解的那一个层次,对你讲这一个问题,与你的心灵对应了,触动了某一个灵机,灵机一动,你才能够理解,否则就是讲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 我估计王阳明回答友人“岩中花树”的提问,大概也是属于此一类型。那位友人的名字没有提及,可能不是他的弟子,在修身养性上也没有什么深入实践,对王阳明那一套“心即是理”的学说也是不太感冒的。他问王阳明这个问题只是抱着一种调侃的意味来问,王阳明是绝顶聪明的人啊,对于这种类型的提问,他当然不会正儿八经地去回答,因为说到点子上你也不会理解,徒然造成朋友间的口舌纷争而已,所以他也采用了一种调侃式的巧妙回答,就象我们熟悉的外交辞令一样,看似回答了问题,其实又什么都没回答。
在我看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其实在另一个地方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请问。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曰:“人又什么教做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的。如看一个人的生死一样,我们也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的,只看到一个人死后,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还照旧存在,没什么不变呀。殊不知对于逝去的那个人来说,他的天地万物在何处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