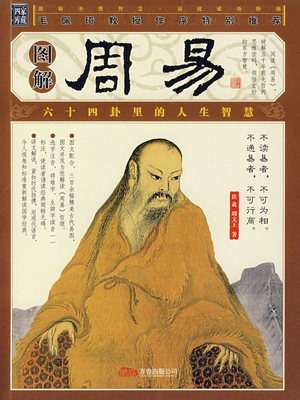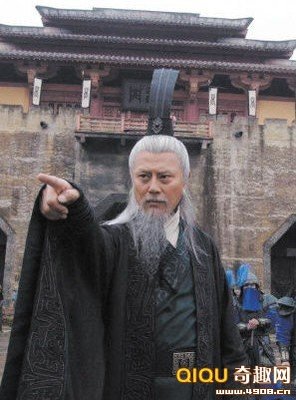因为姜太公的时代到了战国时期已经算是比较久远的事情了,战国时期以及以后的各种著述里讲了不少有关于他的故事,但是也多是真伪掺杂,很多都是传说,未必是真事儿。
我们先看看《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讲吕望的故事时,经常用“或曰”或“概”,就是说司马迁知道的太公望的故事也是根据不同的传闻,没有什么定准儿,实在是比较虚浮渺茫的,司马迁自己也搞不准哪个真哪个假,只能把这些说法都写写。
清代马骕《绎史》里说:“太公出处,自史迁已不能定矣,宜诸说之纷纷也”
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就是这么个实际情况。
吕望出身在姜姓之祖四岳之后(一说伯夷之后)的吕国,为吕氏,能够以国为氏,说明他祖上本来是吕国的王室贵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他这里就没落了,成了平头百姓。
根据上博简九《举治王天下》里的记载看,大概吕望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才学,当时周人的老大古公亶父正遭狄人的逼迫,所以他说“周室有难”,来到吕遂这个地方来访问吕望,谈论了一番,他觉得吕望是个大贤人,如果能用上他,将来可能会为周族的振兴起大作用。
古公还教育自己的孙子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说:“将来你要是能得到吕望,我们周族就能得到天下;如果不能得到他,那么咱们周族就难混了。”
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教育,如果吕望穷得精光、日不聊生,给人打工,怎么还能这么博学多才呢?很可能是他出生在吕国的时候,虽然家人在公室里没有什么职务了,可贵族身份还有,所以还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至于很有名望的周古公怎么认识吕望的,古书里没有什么记载,古公的老婆也姓姜,可能和吕望有亲戚吧,通过亲戚认识的倒是合理,不过这个没啥证据,就不好瞎猜了。
《举治王天下》里的说法是“既言,而上(尚)父皆至”,就是说在古公告诫文王之后没多久,吕望就自动来周了。
吕望去周的另一种说法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一个记载,说周文王被困羑里的时候,文王的手下散宜生、闳夭、南宫适想不出法子把老大弄出来,就想到了吕望。
他们以前有交情,是比较熟识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闲聊扯淡,当然也谈论谈论天下大事,知道吕望有本事,所以要请他来帮忙。
这时候吕望年岁老大,正在海滨隐居,这三人就写信给他,让他到周来给想办法。吕望也说:“我听说西伯昌是个很贤明的人,善于奉养老人,何不去看看呢?”
于是就到了周,出谋划策,终于把文王从监狱里弄了出来。这时候大概是文王受命七年的时候。
上博简《举治王天下》里说“惟七年,(文)王访于上(尚)父,曰:‘我左串(患)右难,吾欲达中持道……’”,这个“七年”恐怕也是文王受命后的七年,就是文王从羑里出来不久,来拜望吕望。
汉代的纬书《尚书中候·雒师谋》里也说是“望公七年”,说明汉代的时候仍然有这个说法。大概是文王早就从祖父古公那里知道了吕望,但是一直无缘相见。
一直到了他受命之年的时候,才想起来全力寻找,吕望终于来到了周,还是为了拯救正在坐牢的文王。
我认为这个说法最接近事实,可这个说法也不怎么流行。究其原因是吕望的故事都是传说,传说这东西往往是不在于是否是事实,而在于古怪离奇,越古怪离奇越吸引人,越容易流传广泛、久远,反之就很难流传。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人们的想象很丰满,而历史事实大多很骨感,越是那些丰富详尽、离奇古怪的说法越往往不可靠,越是那些看上去简简单单、干干巴巴的说法却往往才是真实的记录。
而吕望为了救文王才被邀请到周的说法就太干巴了,没什么传奇色彩,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除了保存在《史记》等不多的几本书里,别的地方就见不到了。
从后世流传的一些书,比如《六韬》、《太公兵法》、《太公金匮》和其它一些故事看,吕望学说的中心思想就一个——“造反”,教人怎么把国家搞强、搞大,然后使用武力占据天下,所谓的“王道”。
而他那个时候,在帝乙、帝辛时期,殷商还是比较强盛的,对商王说“王道”,人家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诸侯那里呢,除了周人之外,大部分国家还是真心把殷商奉为老大,也没产生什么“王道”、“霸道”的思想,甘当顺民。
也不是不想当天下的老大,而是知道这事儿很难做成,操心费力不说,主要是危险性太大,成功的几率不高,这个从周人伐商的历程就看出来。
据《诗经·閟宫》里说周人从大王亶父开始就谋划“翦商”,结果死了两位周王(季历、文王),失败了N次,最后牧野这次成功了,还带有很大的侥幸色彩。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跟在老大后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好,自然而然,吕望的观点就有点不大招人待见。
这之前,吕望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一直当无业游民。就这么着,日月逾迈,吕望也年岁不小了,一事无成,最后弄得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疯疯癫癫的,《尉缭子·武议》里说当时的人都叫他“狂夫”(《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尉缭子》里作“狂丈夫”)。
人大抵就是如此,有高才,有大志,却屡遭挫折,一旦心理素质不过硬,就会出精神问题。
心理素质过硬的,毕竟是少数!
在这方面,孔老夫子做的比较好,能用平常心来对待,考不上公务员,就下来当民办教师,搞民办学校,收收学生,讲讲课,整理整理古书,一辈子勉强还过得,后世也落得个好名声;而吕望大概就没做到,所以精神出了问题。
不过呢,还有一种可能是吕望故意这么干的,因为据他自己说:“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他的这段话见《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周書·陰符》。
这个《周书·阴符》,应该就是古书里说《太公阴符之谋》,后来通称《太公阴符》,据说就是吕望写的书。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狂就是故意这么搞的了,并不是真的疯了。
周与殷的实力差距还是挺大的,吕望能抓住殷的内讧及与东夷交战的机会,一击成功,看来是现代歼灭战的鼻祖。据说他去封国,莱人与之争,他先以缓行,然后急进,后世的拿破仑的一些战法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靠佯狂出名,大约魏晋比较流行,后来也有很多人效法,直到今天也是——有水平的狂,固然会出名,但这个比较累;没水平的,单靠狂也能出名,而且不用受十年寒窗之苦,只要敢放炮敢骂人敢发疯就成,方便省事,是捷径,真好。
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在他们眼里传统文化一钱不值,专家学者都是狗屁,而同门同好者当然都是狗屁不如了。可真要让他们讲点什么了,他们要么找各种借口搪塞,要么就是满嘴跑火车,一塌糊涂。
狂会出名,却真心顶不了学问,很多情况下某些人狂的程度和学问的程度恰成反比。
不管怎么说吧,“狂”总归还是有益的,钱钟书先生说“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不过在吕望这里就例外,70岁了还狂,照旧有出息。
当然,吕望就属于又有水平又狂的那种,不是仅仅一个“狂”字了得。
不管是真狂假狂,反正是在他70岁以前境遇惨淡,这是不争的事实。人混到这个份儿上,生活自然也落魄得很,大约衣食都难继,因为他不善于经营,《说苑·杂言》里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种田的收获还不够买种子的钱,打鱼的收获还不够买网、修船、交税的钱,这样混生活的能力日子咋过?
《盐铁论·贫富》里还说他“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就是他在朝歌当屠夫,挣点儿钱还不够自己花,老婆孩子都养不了。他的老婆一看,这样不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吕望连吃穿都混不上,不能再跟他了,就和吕望闹离婚。
想把吕望一脚踢出去,所以说不是吕望休妻,而是吕望让老婆赶出了家门,《说苑·尊贤》里就说他是“故老妇之出夫也”。
不过呢,说吕望没被启用过似乎也不太确切,《孙子·用间》里也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鬼谷子·午合篇》里说:“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史记·齐太公世家》里也说“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说明吕望曾经当过殷王的官,大约是因为出身卑微,有才能也白搭,不被重用,空有一身本事不能施展,一怒之下辞官不做了。
从此就对殷商怀恨在心,誓要灭之而后快。大家要知道,后来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吕望是最大的支持者,也是意志最为坚决的,是什么原因?我看这个是和吕望曾在殷朝做过官而遭遇鄙视有关。
他就是要施展自己才能灭掉殷商,让殷商的老大看看,你不重用我是你最大的失误,含有报复的意味。
总之,吕望在发达之前从事过很多低贱的职业,他在黄河的渡口棘津当过客店里迎接客人的服务生,同时也负责卖食物,可因为和人结了仇被解雇了;给一个叫子良的贵族当家臣,大约是不会办事,被赶出来了;在殷都朝歌当过杀牛的“屠佐”,就是屠夫的帮手,或者是牛肉店里的伙计,可也没干长久就失业了。
所以《战国策·秦策五》里载姚贾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这段时间是吕望最倒霉的时期。
总之吧,古人的思想里,一个人有本事只是一方面,还有重要的一方面是得势与不得势的问题,就是还必须得有人用你,才能发挥作用,否则连家都养活不了,所谓“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
现在我们一般都知道是吕望在渭水垂钓的时候,被文王聘请到周的,而先秦的文献里,这类说法却不多见。
只有《六韬》、《吕氏春秋》和《韩非子》有这样的说法,《六韬》里说太公望钓鱼是在渭阳,《吕氏春秋·谨听》里说“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韩非子·喻老》里说“文王举太公於渭滨者,贵之也”。《吕氏春秋》说的“兹泉” 一作“滋泉”,大概也不是个什么专门的地名,因为 “滋”就是水深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深渊边钓鱼。
先秦典籍主要是说他在屠牛朝歌的时候被文王发现的。《楚辞·天问》的说法比较详细,说吕望在朝歌的肉铺里卖肉,大概生意也不咋滴,主顾不多,闲得无聊,坐在那里敲着杀牛刀伴奏,放声高唱流行歌曲。
恰好文王到朝歌去朝见殷纣王从这里路过,侧耳一听:额滴神!歌词里貌似还胸怀大志,肯定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得见见。
于是文王就来拜望,二人一聊,很投机,文王说您有本事,干啥还当屠夫?吕望说:“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大喜,觉得吕望真的是个贤人,就给挖到周去了,这便是《淮南子·修务训》里说的“吕望鼓刀而入周”的故事。
?
昨天讲到文王重用吕望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剪伐大商,准备夺天下。
不过要夺天下呢,文王还有点心虚,怕招人非议,他问吕望说:“我听人家说:不要改变古人的制度,不要更换惯常的做法,不要暗地里搞计谋,不要擅自制定新玩意儿,不要重新创造新玩意儿,否则就是不祥。你说我该怎么办?”
吕望说了一番很著名的话:“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
这个是《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周书》的说法。
《六韬·文韬》里的说法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后来那些造反的、叛乱的、弑君篡位的,经常拿这几句来当说辞,成了“造反有理”的最大的理论支持。
天下既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自然人人可以当皇帝,人人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就看谁更有本事。
那么要夺天下,具体该从哪里做起呢?太公望的建议就是先从用人开始,多招有本事的人来帮忙。
他对文王说:“您现在虽然屈居于一人(指纣王)之下,却能伸于万人之上。要想成大事儿,只能多启用贤才然后才能办到。”
于是文王就行动起来,亲自去拜见的贤人有六人,通过寻访来的有十人,招呼来的有千人。
友之友称为“朋”,朋之朋称为“党”,党之党称为“群”,就这样友友、朋朋、党党、群群,宛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用此手段网罗了一大批心腹之士,为夺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人津津乐道文王启用吕尚,其主要的目的就为印证作为一个统治者,要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观世》里说,文王不过是千乘的诸侯,而纣却是个天子,作为天子的纣没启用吕望,结果丢了天下;而本是诸侯的周启用了吕望,结果得到了天下,这就是“知之”与“不知”的区别。
而从贤人这边说呢,有本事,有才能,还得具备发挥的条件,就是要有贤明的主子启用你,“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后可成”,否则空怀锦绣,只能在河边钓鱼。
这就不能不说吕望入周时环境。周人本来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部族,势力也比较弱小,开始大约主要靠游牧为生的,兼营农业,和夷狄杂处,生活得不怎么样。
和殷商相比,周人就比较自卑,他们称殷商为“大邑商”、“大邦”、“大国”,自称为“小邦周”或“小国”。
到了后来武王的时候,周人做大了,要灭殷,也开始自称“大邑”。比如《武成》里说“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臣附于大邑周”,这明显是羡慕殷人,跟着学样儿。
不过这个称呼连广大的周人都觉得不合适,没流行起来,直到后来武王灭殷之后作《商誓》,还说“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斯小国于有命不易”,周公作《大诰》、《多士》也说“我小邦周”、“我小国”,还是自称“小国”、“小邦”,不称自己为“大邑”或“大国”。
周人想说明:我一个小国怎么会得到天下?是因为我有天命,“天命在朕躬”,即使是我一个小国,照样扳倒大邑商。所以自称为“小邦”、“小国”也颇有自豪的意思。
古公亶父的时候,周人被夷狄排挤得在豳这里蹲不住了,只好放弃了豳邑,跑到了岐山南边的周原,古公还到一个姜姓部族的邰国那里去入赘当上门女婿,“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才算稍微安定下来。
但四周还是一圈儿虎视眈眈的夷狄部族,处境并不安稳。不安稳归不安稳,野心却是不断萌动,据《诗经·閟宫》里说古公亶父迁到岐阳之后,就“实始翦商”,就是开谋划篡夺殷商的天下。
不过就我个人感觉而言,《閟宫》的话有点儿吹牛,当时周人穷的那个样,连吃饭都困难,人穷志短,哪里可能有夺殷商天下的雄心。
真正意义上投靠大商的,是亶父的儿子周王季历,这个是《古本竹书纪年》里的明文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季历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王,有宏图大志。他投靠了大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
“牧师”的原来是负责养马的官,但是后来有权力了,就能主管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本来规定是牧地,但是后来就不限于此了,而成了能管理一方事务的地方官员。“牧师”这个官职到周代仍然保留,《周礼·夏官·牧师》里说“牧师,下士四人。” 郑玄注:“主牧放马而养之。”
商王文丁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周人牵制西北的戎狄,而周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殷商的支持下和戎狄开战,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大概开始也仅仅是想把周做大做强,想图个好日子而已,未必有得天下的雄心。
可是周王季历非常能打,频频用兵,而且是赢多输少,结果周勃然作兴,势力飞速壮大。势力大了,心也就大了,开始觊觎殷商的天下,自然影响到大商的稳定了。
文丁一看,这么搞下去不行,周人是只狼,不知道什么时候养壮了把我咬一口。于是他派人把季历招到大商,把他囚禁在塞库这个地方,没多久季历就死在了那里,一般认为是文丁把他杀了,所以《竹书纪年》里说“文丁杀季历”。
文丁干掉了季历,对周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阻碍了他们飞奔的脚步,同时也和周人结下了梁子,在周人勃勃的野心里又添了一把复仇的火焰。季历死后,他儿子昌即位,就是文王。对于文王来说,大商与他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门心思要报仇。
《古本竹书纪年》里记载帝乙二年的时候,周人伐商,这个时候的周王是文王,说明文王为了替父亲季历报仇,也兴兵伐过商。
当时周人的势力虽然经过了季历时代的迅猛发展,可是你得看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纵向比周人的势力是空前壮大了,可是横向比就比殷商差太多了,远不足以灭商。
因为这时候周实际上还比较穷,经济实力并不雄厚。《楚辞·天问》里说“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尚书·无逸》里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也就是说,周文王虽然是周族的老大,可是还得披着蓑衣、扛着鞭子去放牧;或者穿着很卑贱的衣服去干农活儿,否则也混不上饭吃。
可见这时候周人的生活状况仍旧不大好,根本没法和殷商相比,所以文王这个时候伐商报仇,自然也不能成功,只能忍着,继续当商王的臣子。
这就是文王的高明之处:能屈能伸、能软能硬、能长能短、能粗能细、能进能退。
当然文王也不会闲着,而是继续为伐商打基础,利用武力和利益,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断虞、芮之讼、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邘……,还收服了一堆临近的小国
这里面据说主要是吕望给出的主意,《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就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我们看看《六韬》里就会知道,太公给文王的建议,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各个方面。比如周文王伐邘的时候,曾经咨询吕望:“我准备兴兵打仗了,先揍谁?”
吕望说:“密须氏老是对我们或服或叛,犹疑不定,就先揍它”。管叔说:“不好吧?密须氏的国君很贤德,是位闻名天下的明君啊,我们讨伐他恐怕会落下不义的名声。”
另外,王晖先生考证:伯邑考曾经被立储,但没即位就死了,所以他也和先王一起受到祭祀。伯邑考死后,才立的发当太子。
总之这事儿有点不明不白:古书上说伯邑考是被纣王杀的,按理说纣王要除掉心腹之患,文王是首诛才对,可为什么纣王只杀了伯邑考却把文王给放了?这个实在无法理解
如果伯邑考真是纣王所杀,那么这也是周人的深仇之一,储君被杀能不算大事?
可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主要理由之一是为父报仇,并没有说为兄报仇的事儿,可见武王没把伯邑考的死算做纣王的罪状之一。
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大的可能是古书里说纣王杀伯邑考给文王吃的故事是战国时代的人杜撰的,不是真事。
伯邑考是病夭,他的死和纣王无关,所以周人没法把这个罪名罗织到纣王头上。
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间很长,贾谊《新书》里说“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就是说文王在羑里被关了整整七年才放出来,不管这个时间是否确实,总之是说文王坐牢时间很长。
在坐牢期间,他百无聊赖,就推演易卦,把八卦互相重叠,才有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当然这个也不太可靠,因为根据考古发掘,在殷商中期的时候就有了六爻的卦象,说明在文王拘于羑里之前已经有了重卦了,那不是文王的功劳。
还有个故事是他热爱流行歌曲的嗜好不改,在幽囚的情况下,竟然还作曲填词,做了一首歌叫《拘幽操》,抒发自己坐牢时的感受,见于《琴操上》。
不过看那歌词不像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他在歌里唱“遘我四人,忧勤勤兮”,就是说我遇到的四个贤人,忧心忡忡地奔波操劳,就是想救自己出去。
吕望助武王伐商,在讲周公的讲座里已经讲过,这里按下不提。
这里再说说妲己的下场,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故事。
崔豹《古今注》里说是太公望用玄钺斩杀了妲己,到了《封神演义》里,是说妲己被活捉了,要处死,她本来就是九尾狐狸精,长得太漂亮,又有狐媚之术,结果刽子手看见她就手软脚麻,杀不了她,是姜子牙用陆压送给的宝贝“斩仙葫芦”才把妲己处死了。
而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的说法,妲己不是被姜子牙杀死的,而是被殷纣王的儿子殷郊所杀。
殷郊也见于《封神演义》,说他被妲己迫害,要被杀头,广成子救了他,并收为徒弟。学艺成了之后遵师命下山去帮助武王伐纣,可是被申公豹给说反了,反过头来帮助殷商的军队打周人,最后被后为姜子牙和燃灯打败,引入岐山,受犁耕而死,被姜子牙封为“値年岁君太岁之神”。
而《大全》里说不是,说他是纣王的王后姜皇后履巨人足迹怀孕所生,生下来是个肉球,被拿到殷城郊外扔掉了。神仙申真人从那里路过,把肉球捡了去剖开,生出个小孩来,把他抱回水帘洞,让贺仙姑当他的乳母把他养大,给起了个法名叫“唫叮呶”,正名叫“唫哪吒”
这里说唫哪吒是殷郊,而不是《封神演义》里说的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的哪吒,《大全》里也专门有“那叱太子”一条,就是《封神》里的哪吒,是托塔天王李靖之子,可是没说他生下来是个肉球。到了《封神》里才这么说,大概是把《大全》的里说唫哪吒(殷郊)出生的故事给移植过去了。
因为唫哪吒是在殷商的郊外被捡到的,所以又起个大号叫“殷郊”。
殷郊帮助周人伐纣,在牧野击败了商军。妲己本来是个妖雉,就是野鸡精(这个和《封神》里九尾狐的说法也不一样)。
见殷商亡了,就要变化逃走,结果被殷郊用法力捉住并斩杀了,化成了一股黑烟而没,殷郊因此被玉帝封为“地司九天游奕使至德太岁杀伐威权殷元帅”。
这里明白地说是玉帝封的,不是姜子牙,可见那时候还没有姜子牙封神之说。
中国的传说里,九尾狐狸精妲己到这里就完了,可是在日本却没有。九尾狐狸的故事影响太大,也流传到了日本。
日本的传说里说,九尾狐狸精是出生在天竺(印度),专门变成美女蛊惑帝王让他们亡国。后来游荡到中国,它在夏代变成妹喜,让夏桀亡了国;在殷代变成妲己,让殷纣亡了国。殷纣王死后,它就逃离了王宫,可大师姜太公不肯放手,到处追杀它,务要除之而后快。它的法力不是姜太公的对手,不得已,漂洋过海逃到了东瀛,也就是日本,躲藏起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还变成了周朝的褒姒以及印度摩揭陀国的班足太子妃子华阳夫人,是在唐代的时候才从中国跑去的日本,是不是她又变成了杨贵妃?这个待考。
原来,九尾狐狸在日本躲了两千多年之后,终于耐不住寂寞,在鸟羽天皇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时期),仍旧变成了一个美女,叫玉藻前,进入皇宫,魅惑当时的鸟羽天皇,大得宠幸。
鸟羽天皇听信玉藻前的谗言,把国政弄得一团糟,祸乱频仍。而且没过多久天皇就病了,御医们想尽了办法,医药罔效。
当时的阴阳师安倍泰成看到皇宫里妖气弥漫,就知道是妖物在祸害天皇,向天皇报告,天皇就让他暗中追查。
一种说法是泰成的先祖、日本三大阴阳师之一的安倍晴明追查的玉藻前。安倍晴明是日本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在日本赫赫有名,关于他降妖捉怪的故事很多,但是他在1005年就去世了,鸟羽天皇1103年才出生,所以他不是鸟羽天皇时期的人物。
而安倍泰成的事迹在日本没有什么确切记载,只说他是安倍晴明的后人,还有说是晴明的五世孙安倍泰亲的儿子,就是晴明的六世孙,说法比较乱,怀疑他是文学作品里虚构的人物,历史上并无此人。只因为从晴明开始,安倍家族多出阴阳师,才根据这个创造了这么个人物。
如果说鸟羽天皇时期安倍家的阴阳师,从时间上讲很有可能就是安倍泰亲。
泰成很快就查到了玉藻前的身世,原来就是从中国逃来的九尾妖狐,并用阴阳法诀把她打出了原形。玉藻前见身份败露,一阵妖风逃得不知去向,天皇的病因此痊愈。天皇知道自己竟然宠幸了一个妖物,非常羞愧,也非常恼怒,下令泰成追杀玉藻前,一定要干掉这个妖狐。
有意思的是,安倍家族实际上是妖狐的亲戚,有很密切的血缘关系。传说安倍晴明的母亲就是和泉国(今大阪)信太森林中的千年白狐妖葛叶,为了报答大膳大夫安倍益材的救命之恩,化成美女以身相许,给益材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安倍晴明。
所以晴明也被称为“白狐公子”,之后的安倍家族的人身上都有妖狐的血液,他们的法力也来源于此。这个可能是因为传说中安倍晴明的脸型长得象狐狸,人们才给编了这么个故事。
就像中国唐代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因为样子猥琐,“状类猕猴”,所以就有对他怀有敌意的好事者写了一篇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来挖苦他,说他真正的生父是一只成精的白猿,一个道理。
玉藻前逃到了那须野(在日本本州岛的枥木县),恶性不改,经常吃掉妇女和儿童。那须野领主须藤権守贞信接到居民的举报,说女人、孩子不断莫名其妙地失踪,知道是妖物作祟,上报到天皇那里,请求派人来捉妖。
鸟羽天皇就任命三浦介义明、千叶介常胤和上总介广常为将军,阴阳师安部泰成为军师,带领八万军士到那须野去帮助贞信捉妖。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斗法,捉妖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玉藻前也耗尽了法力,最终被三浦介和上总介联手杀死。
安倍泰成封印了玉藻前的尸体,它却变化成了一块巨大的毒石,里面都是它的野心和执念,因此能散发出强烈的毒气,杀死附近的人、动物和植物,它周围寸草不生,所以村人称之为“杀生石”。
其实这种有毒的石头枥木县现在还有,多是散布在火山口附近,火山喷出的硫化物及砷化物有剧毒,天长日久浸入石头里,这些石头也就成了毒石,人或动物沾上了就会中毒生病,并不神秘。
(话说xxx去日本旅游,还特意带了这样的一块石头回家)
周围的村民对这块石头非常恐惧,多次请高僧为其镇魂,可他们法力不够,都被石头喷出来的毒气毒死了。直到日本的南北朝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会津元现寺的第一代主持玄翁和尚来了
才用强大的法力把杀生石破坏。玄翁用禅杖把杀生石击碎,碎块飞散到日本各地,不能再害人了,因为它的名头太响,一些寺庙就把部分碎块捡去,当做神物安放、供奉。还有的说这些碎块化成尾先狐和犬神这两种妖兽,成为了被各地的使役术师控制并驱使的“式神”。总之到这里九尾狐妲己才算彻底被消灭。
这个故事在日本很有名,有大量的文艺、文学、美术作品都在讲玉藻前的故事(这也正是说法混乱不一致的原因),九尾狐狸也就成了日本著名的“三大邪恶妖怪”(酒吞童子、九尾狐玉藻前、崇德上皇大天狗)之一。
而九尾狐的妖法最为强大,所以也被称为“三国(即天竺、中国、日本)第一大妖怪”
大家熟悉的日本动画片《火影忍者》里的主角漩涡鸣人身体里就封印着九尾狐,虽然鸣人的本事不济,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九尾狐在鸣人体内爆发,其“查克拉”威力无穷,谁都不是对手,也就是取自这个民间神话。
现在回到周初。
话说武王胜殷之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用俘虏来的活人祭祀周的先人。
周师军队都是白盔白甲,大概是给文王挂孝。武王祭祀的时候,是吕望扛着殷纣王烧得糊焦囵吞的尸体,这时候才把纣的头砍下来,悬在白畤(一种旗名,《史记》里称“大白之旗”)上,率先进入周庙祭祀,然后杀了很多殷商的贵族献祭。
杀人做祭品的祭祀方式,应当是周人跟着殷人学来的。殷人喜欢杀人祭祀或以活人殉葬,现在又轮到了自己的头上。
上面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出自《太公六韬》、《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太公阴谋》,都是出自《太公》一书。那么大家看看,周人在整个灭殷过程中可谓费尽了心思,什么手段都用。
这就是吕望大师的教诲,使周人最终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成功;吕望本人也因此成了周朝的头等功臣,名标青史。
古今人们的思想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做事不在于过程而在于结果,无论过程中你用了什么阴损的手段,只要胜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寇;在日常生活中呢,也是一样,无论用什么手段,你胜了就是君子,败了就是小人。
兵法就是“诡道”,就是比谁更诡诈奸狡,比谁的办法更有效、更容易获胜,没有正邪之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我们有句古语叫“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在兵法谋略上,不仅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要善于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总之别做什么君子!
周人的做法被伯夷、叔齐骂了,算是为君子所不齿,可文王、武王照旧是“圣哲明王”的典范,阴谋大师吕望照样是圣贤良佐的代表,因为他们是成功者!
所以说单就做事而言,成功才是王道,过程、手段如何都是次要的,只要行之有效、能达成目的——这就是吕望大师《阴谋》之书的精髓!
武王克殷之后,万国来朝,可也有不买账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故事,见于《六韬》,说武王伐殷之后,诸侯都来朝见,只有一个丁侯不肯来朝。
武王老大不高兴:“丁侯那孙子瞧不起我,要不要派人去扁他?”
吕望说:“不用,你看我画个圈圈诅咒他!”
吕望就在竹简上画了丁侯的像,射了三箭,分别射在头、口和肚子上,结果那边丁侯就病了,痛苦不堪。找来巫师给占卜,巫师说:“是周人在作祟,用巫术害你呢。”丁侯害怕了,就到周来请求举国为臣。于是,吕望让人在甲乙日把丁侯像头上的箭拔了,在丙丁日把射在口上的箭拔了,戊己日把射在肚子上的箭拔了,丁侯的病就痊愈了。
四周的方国听说了这件事,知道吕望法术高强,怕得要命,都来称臣纳贡了。
——看了这个故事,大家想到了什么?对了,就是《封神演义》里陆压教姜子牙用“钉头七箭书”射死赵公明的故事,就是根据《六韬》中吕望射丁侯的故事改造来的。
根据《逸周书·世俘》的记载,武王克殷杀了纣王之后,战事并没有结束。
首先是纣王的重臣飞廉、恶来父子都没死,特别是恶来,继续带着一支军队与周人对抗。
恶来的“恶”当作“亚”,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官职名,殷商时期的“亚”很多,殷墟卜辞里称为“多亚”,因为亚、恶古字通假,所以才写成“恶”,“来”是他的名字,他是飞廉之子,一个大力士,勇猛善战。
他不肯投降周人,于是周武王就命令吕望去追杀他,《世俘》里说“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太公望命御方来”是个倒装句,就是“命太公望御方来”,“御”本来是使马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进”义,是进击、追杀的意思,和后来的抵御、防御的意思不同;“方来”据陈逢衡、于鬯、陈汉章等人的说法就是恶来。
吕望追杀了恶来三天,到了丁卯日回来,向武王献俘,说明大获全胜,《史记·秦本纪》里说“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说明恶来是被太公望打败杀掉了。
另一个说法是恶来是被武王射死的,《尸子》里说武王“亲射恶来之口”,就武王亲手射恶来,射中他的口,致死。不知道是武王在和恶来作战的时候射的,还是吕望抓住了恶来之后射的,反正是把恶来射死了。
恶来被杀了,他老爸飞廉却跟着纣王的儿子王子禄父也就是后来的武庚投降了周人。
周武王为了收服殷人的心,就封纣王的儿子王子禄父于卫,仍然居住在殷,其都城仍称为“商邑”。可是禄父身服心不服,后来成王时与三监叛乱,又自立为王。在这场叛乱中,飞廉是积极的参与者,说明飞廉不像儿子恶来那么死心眼,他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反扑。
成王平叛,兴兵伐三监,进攻商邑,杀了录子圣,飞廉就发挥自己“善走”的才能,跑到了东夷的奄,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这里本来也是商人的都邑,盘庚在迁殷之前就居住在这里,所以也称为“商奄”或“商盖”。
飞廉在这里和东夷人一起造反,抵抗周人,这就是周人所谓的“东夷大反”,于是周公就开始东征,攻克了商奄,杀掉了飞廉,一部分东夷人南逃到了江淮地区,一部分则被征服成了周人顺民。
而这时候西方的一支戎狄叫奴徂之戎,不断地侵扰周人,让周人非常头疼。为了抵御他们,成王就下令把征服的商奄之民西迁到了邾圉这个地方(《汉书·地理志》称为“朱圄”,在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让他们去对付奴徂之戎。这伙西迁的商奄之民,就是秦人的祖先。
这个记载见于清华简《系年》,证明了秦人虽然兴起于西戎,而实际上他们本来是东夷人,老家是在东方的奄,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
其次,纣王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很多殷商的臣属方国并不服周人,于是周武王只能派吕望四面征伐。
这时候对周人有利的情况在于,殷商被干掉了,没了老大,那些臣属方国就树倒猢狲散,要么投靠周人,要么就想方设法求自保,可都是各自为战,形不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所谓“群龙无首”,面对强大的周师,他们没有力量真正地反抗,因此周人就抓住时机把他们个个击破。
据宋代司马光《稽古录》说,克殷之后,“太公留镐京,与周公夹辅成王”,也就是说太公望和周公旦都留在镐京一起辅佐成王,但是从典籍来看,克殷之后二年武王就死了,到了成王之时,吕望就不是太师了,而是周公。
同时吕望和周室的故事就不太多了,最多见的是周公,比如《尚书》的《周书》部分,写了那么多的事儿,竟然没提到太公望的事儿,甚至连名儿都没提过;《逸周书》虽然提到太公望,可是事儿比较少,最多的还是周公,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呢?《尚书大传·大战》篇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纣王自杀之后,周武王进入殷商,可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殷人,就把太公望找来问:“进入殷之后该怎么办呢?”
太公望说:“我听说,喜欢某个人,就连他屋上的乌鸦都喜欢;讨厌一个人,就连他家的墙壁看着都烦!我的意思是‘咸刘厥敌,靡使有余’,您说怎么样?”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憎恨殷纣王吗?进入殷商以后,不管好歹把殷人都灭掉算了,一个都不剩下。这就是“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的出处。
武王不同意,说:“这么个搞法恐怕不行。”
召公小跑着过来建议:“没有罪的就让他活着,是咱们的敌人的都杀掉,不要留下后患。这样如何?”
武王还是不同意:“这么搞也不行。”
周公又小跑着过来进言:“臣听说一个方法:让殷民各安其宅,各自种他们的田地,不要讲究什么过去、现在,只要是仁义的人都可以亲近他们。就是老百姓犯了错误,也要说百姓没罪,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这样如何?”
武王听了大喜,“旷乎若天下之已定”,就是豁然开朗,就象天下已经平定了一样。
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太公望就是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对治国安民这方面没有研究,他对待殷人的方法简单而又残忍,近似后来的“屠城”,把城里城外的殷人都灭了就完事儿,纯粹是武将的作风。可是这样可能激起殷人对周人的更大仇恨,殷人更不会安定了,所以武王不同意
召公的办法是把殷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反对周人、顺从周人的,这些人让他们活着;一类是和周人为敌的,这些都要杀掉。但是这个办法的基础就是要清算旧账,照旧会引起殷人的不满,所以也不好使。
周公的办法是既往不咎,殷人只要不造反,就象以前一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这样殷人就会接受周人的统治,天下也就安定了。
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太公望夺天下是很不错的战将,但是治天下就比周公逊色。所以,克殷后治国平天下的,还是周公出力最多,而且他也是周王室成员,周人自然要竭力地推举、颂扬他了。
不过呢,情况也未必如此,据一些古书的记载,克殷之后,吕望的阴谋仍在继续。
《淮南子·道应训》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说武王伐纣灭殷之后,把太公找来问:“寡人讨伐纣夺了他的天下,这是臣杀其主、下伐其上。我怕后世的人学我这样,用兵不休,争斗不已,这该怎么办呢?”
其实武王是怕后人也学自己这样儿起来造自己的反,夺自己的天下,一直很害怕。
太公给武王出了一个十分阴险的主意,可以看出他对治天下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他说:“王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事儿就象是打猎,在没获得野兽之前,老是怕它伤得轻抓不到它;等抓到了它,又怕它损伤的肉太多。
王如果想长久的占据江山,就必须塞住民众的口鼻耳目,让他们多干些没用的事儿,把教育搞得复杂点儿,让他们都安心在体制内干活;可以让他们尽量发泄情绪,却不要让他们懂什么道理,这样他们自然就会丢掉他们的头盔,而戴上学者的鹬冠,扔下他们的刀剑,而拿起奏事的笏板。
给他们制定三年之丧的制度,可以让他们子孙不繁盛;大力宣扬谦让是美德,就会让他们和睦相处而不争斗;用酒肉来结交他们,用音乐来娱乐他们,用鬼神来吓唬他们,用繁文缛节来约束他们的才能,用厚葬久丧来掏空他们家产,让死人含珠玉、穿纶组来耗费他们的财物,让他们种地的时候起很高的田垄来用尽他们的体力。
他们家里贫穷了,族人减少了,一天到晚因为贫穷而担忧苦闷,这样还能折腾啥事儿?坚持这样的原则来改变一下社会风俗,您就可以长有天下而不会失去了。”
这些主意够阴险吧?阴险归阴险,而自古迄今的当权者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招数,因为它们的确行之有效。可是呢,这阴谋,屁民们却认识不到。
比如后来儒家讲周礼,极力推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咧、“三年之丧”咧、“礼乐教化”咧、“繁文缛节”咧、“大办丧事”……,受到人们的追捧。
可是屁民们不知道这是周人统治者故意设的局,搞的阴谋,还当成好事津津乐道、极力奉行,有些直到今天还盛行。
追根溯源,这都是吕望大师的主意!周人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周朝延续了800年!
《太公金匮》也记载过类似事儿,武王问太公说:“仗打完了,可是民众官吏们还都不安分,贤者能人心神不定,我怎么才能安抚他们?”
太公回答说:“那就不需要什么兵器了,照样可以守住国家:可以让他们把耒耜当成弓弩,锄杷当成矛戟,簦笠当成兜鍪,锁斧当成攻具”。
让国人别再惦记打仗的事儿,而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经济,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主意不错。
武王听了太公话,首先做出姿态,把马散到华山之阳,把牛放到桃林之野,把战车、甲胄存在库房里,把兵器用虎皮包起来收走,让作战的将帅都成为诸侯,表示自己再也不打仗了,以此安定天下人的心,然后一步一步地施行那些措施,比如制定祭祀、朝觐、耕藉、养老、教育等等制度,于是“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天下果然太平无事,熙熙而乐了。
据《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二引《周书》的说法,从此武王睡觉的时候不关大门,表示自己不再担心害怕;出门的时候不带佩剑而拿着笏板,表示自己心中再无仇怨。
当然从史实的角度去考察,事实并非如此。上面说了,武王虽然灭了纣,可是不服的殷商敌国还很多,不得不东征西讨,一直在不停地打仗,局势混乱得很。周人一直搞不定殷民,武王也是忧心操劳,直到把自己累死,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避免三监叛乱和东夷大反,很是混乱了一阵子
克殷之后,太公望的另一项功业是帮助周建立了金融制度,《汉书·食货志下》里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周代的“九府”就是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內、职金、职幣,这九个部门都是主管钱财的;“圜”就是钱,“圜法”就是货币政策,使用的货币有金、刀、泉、布、帛,都给规定了计量单位,便于流通,这也应该是一项不小的功绩。
他给周制定了这个货币政策,后来又把它带到了齐国,所以齐国的货币体系比较独立且完善,其刀币(刀化)一直很有名。

再往后太公望就没有多少帮助周王治国的故事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