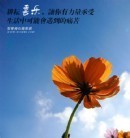朱东
虽然我们说,中庸之道唯有中国的先哲知之,但是关于中庸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确实世界性的,持续性的。
只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西方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途,而中国人则是逐渐的从正途上开始走偏。
我们今天对中庸,尤其是对中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叫做中。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比较明显的应当是有两宋的哲学家们完成的。比如北宋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应当说是奠定了这种观点的基础。南宋的朱熹又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则不仅彻底确立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种确论,而且对其起到了普及与推广的作用。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之后的一千年中,始终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官方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
我们确实不能仅凭这两句话,就认定这几位儒学巨人在思想上完全走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言论,至少表现出了外向性的,形式化的倾向。于是,当这种观点普及于民间之后,就必然在其简化的过程中,变成了近似于几何式的思维,即凡事求其两者之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当然,论及几何式的思维方式,自然要以西方为鼻祖。事实上,西方的哲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就是用这种几何式的思维方式,来演绎他的中庸思想的。简单的说,他认为在人的品德中有两类亚德,一种是欠缺,一种是过度。也就是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状态中,是不存在美德的,只有发现并选择了二者的中间,才可能产生叫做卓越的美德。
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观点,或者也是为了让人们更有效的运用他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举了好多这样的例子,来阐述什么叫中道。比如他说,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和猥琐之间的中道;不卑不亢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虚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
听着都有道理,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逻辑问题。
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一方面用极端和中道来定义好的品行和坏的品行,因此接下来的任务似乎应该是就每一种情感或行为,用这个定义来解释好的和不好的品行。但实际上,他在考察有些品行时,他是先有了对这些品行是好是坏的评价,再武断地根据他的评价和以上定义,指出它们所谓极端或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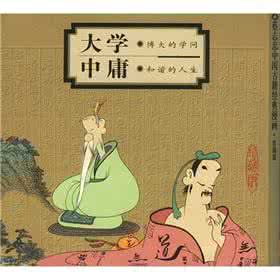
也就是说,是把自己先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以自我绝对正确为基础,来评判是非,选择中道。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真可谓是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思考问题。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不正是极端的表现吗?
第二,导向问题。
如果凡事都要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那么就是在过与不及两极之外,又增设了一个第三极。显然这个第三极是与前两极是对立的,所以不是化解了好盾,而是激化了矛盾;不是消除了对立,而是强化了对立。其结果是在原本两极对立的情况下,又让两极都将这个第三极作为与自己对立的对象。于是,虽然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但是怯懦的人会说勇敢的人鲁莽,鲁莽的人会说勇敢的人怯懦。
所以,在这条几何化的中庸之路上,人们得到的不是通过与天的合一,而相互融合,而是分裂冲突的更加剧烈了。而其根源则是,这种几何式的求中之策,本身就不符合天道。
而中国的先哲们所规划的中庸之道,显然不是建立在这样简单的几何式的思维方式上,如果一定要用几何式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大约应当是这样的——那就是除去过与不及两点,在过与不及之间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称之为中。
所以,真正的中庸,是自由的中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