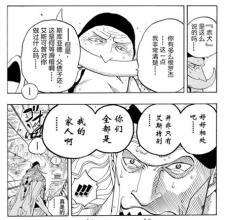摘要: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单一、职责不明,需求表达渠道不畅、机制不完善,呈现“碎片化”和不可及性倾向,导致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着设施单一、使用效率低,医疗护理资源不足、服务人员专业水平低,精神慰藉服务缺失、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难以实现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明晰各类主体职责、构建“共担、互补、共享”机制,畅通需求表达渠道、构建老年人积极参与的激励机制,祛除“碎片化、构建养老服务无缝隙供给机制。
关键词:中国城市社区;满意;耦合机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5%,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1.3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2025年将达到3亿,2034年将突破4亿。同时,我国人口老年化呈现“快速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等现象叠加的特点。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独居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空巢困难老年人等特殊老年群体人数的增加,使得各类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日趋迫切。
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老年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提出“养老服务应以社区为基础向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1992年联合国《老龄问题宣言》中强调要“以社区为单位,让老年人尽可能在家中居住”,提出了不同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社区养老,即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重要方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就开始得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1993年民政部等13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提出85%以上街道兴办一所老年公寓(托老所),正式将社区养老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中;2001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区老年服务星光计划”;2006年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城市至少要有一所相当面积的具有指导、示范、辐射、培训等多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提出:在城市社区养老层面,重点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动中心、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养老设施,推进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增强养老服务功能,使日间照料服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到2020年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社区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养老服务政策,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的探索实践,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整体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亟需探索创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提高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度与满意度的耦合,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公平可及[1],促进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单一、使用效率低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群体和养老服务需求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进一步加大,政府主导的标准化、机构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服务需求,同时政府养老服务供给组织链条加长,服务难度也大大增加[2];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大多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来配置的,在人口流动加快、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这一配置标准造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中老年服务类产品偏少,而且设施的配置与老年群体的空间分布不相匹配;目前,城市社区在娱乐文化设施和日常生活照料上的养老服务供给是最多的,但是依然存在着数量和质量方面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现象,有的城市社区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内设棋牌室、娱乐室、图书室,老年人可以在此看电视,打牌下棋、喝茶聊天、看书读报,有的城市社区还有老年食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无偿、低偿、有偿的餐饮服务,许多城市社区还有户外健身场地,设有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但是很多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偏少、样式单一,而且长时间不维修、存在安全隐患。有些活动场所,由于不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或与老年人的兴趣不符而无法使用,造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使用率低,迫切需要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适老性改造。
(2)医疗护理资源不足,服务人员专业水平低
医疗护理服务是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养老需求,但是我国有的城市社区并没有相应的医疗护理设施与资源,有的社区虽然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室(站、所),但是还存在着医疗护理人员数量少、学历职称偏低、医护场地狭窄、医疗设备简陋等问题,医护人员大多是中专和专科学历、初级职称,全科医生严重偏少,专业水平与能力无法满足社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医养需求。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多数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室(站、所)的印象是“技术水平不强、专业水平不足、医疗设备不够”,老年人到社区卫生服务室主要是量量血压或一般感冒去开点药,重病、大病、急病就会去到市里的大医院看病,城市社区医疗护理水平不利于老年人在社区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目前,城市社区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极度匮乏,一个社区的养老管理员一般只有一个人,而且大多数是身兼数职、极少有专职人员;养老服务人员大多是50岁以上的女性或低龄健康老年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工资水平都不高,工作的积极性不强、队伍不稳定,服务能力有限。
(3)精神慰藉服务缺失,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难以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老年人对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日趋迫切,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与高层次的趋势[3]。但目前我国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精神养老服务大多局限在休闲娱乐活动上,忽视了老年人的亲情需求和再就业需求。城市社区老年人在退休后,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自身的社会价值无法体现,心理会有落差感,特别是空巢独居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压抑感和空虚感,易发心理疾病,新闻报道中发生的老年人自杀事件从某个侧面验证了老年人精神养老服务需求的急迫性。据统计,目前全国城市社区4000多万离退休老年人口中有500多万各种类型人才,仅有不到20%的人得以继续发挥“余热”[4],如果可以合理适当地对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进行再开发,不仅可以减少社区、家庭和政府的养老压力,还能满足城市社区老年人在精神上的需求,提升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老人群体的主体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现实中面临着老年人参与意愿强烈而缺乏参与机会的矛盾和困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