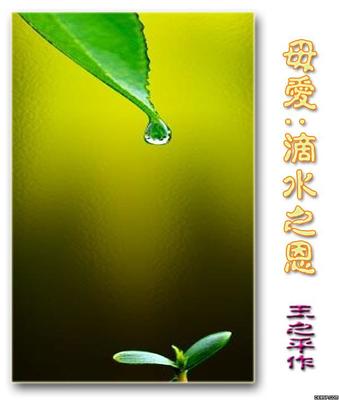1
当赤裸裸站定在这采光充足的大厅和比采光更充足的、如万炮齐鸣的几十双明亮眼睛的前面,心——反倒一下子煞定——“咝咝”有声的。刚才进屋前和在屏风后脱衣时那一阵嚼心的羞愧尴尬、整个心身的紊乱,似乎都异常可笑了。整个屋子,除了炭在画纸上的“嚓嚓”声,还能隐隐可闻隔挺远的球场上的几丝喧闹。再就是自己能感觉到我的怦怦心跳了。
——我,像一只“哗”地蹿出水面的白海豚,被定格水面上了。
下面灼目的光波,不,那不是阳光,是来自心灵的目光——对我来说那每道光都是一根针芒啊。我又像一只刺猬,浑身就是被这样的针芒包裹着。可,这些面目清秀得带点病白、目光专注得近于空冥的、跟我年龄相仿的美术系的学子们,你们能读懂我吗?读懂多少?我在你们的目光里到底算什么?
如此地展示我的青春胴体,或许算是值得了吧。不是说“女为悦己者容”嘛。眼下的我,也可谓为悦己者们容了。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仅此而已吗?仅此?
其实我心底的紊乱是在好长一段时间后才真正平静下来的。这时,我才发现,大厅的另一端,学子们背后,靠在窗上还有一双眼睛,发出有别于我眼前的光芒——他是以一种注目但绝不空洞的目光,凝望我的。那眼睛在述说着什么。我感觉到的,那目光才是真正在读我呢,那目光才有可能读懂我……可我,却读不懂他,读不太懂?只有两句我读懂了——那就是爱意和鼓励。像在说:亲爱的,别怕,有我在这儿呢。
——他就是带我来这儿的梵朗老师,我生命的第一颗星,第一颗亮星。
几年后,当我被缠身的庶务消蚀着,我心头的这缕星光随着岁月磨损渐次黯淡些了,当我怎么也没法儿从女儿和我身边的人眼里再找到这缕星光时,我才愈加觉出它对我生命的珍贵。我想,那星光该还在我永远怀念的那两个人的眼睛里闪烁吧?
2
认识梵朗是一个傍晚,西天把一片滴血的晚霞掬捧在那里,恰似我的心情。当时我正用一种还不算太狂野的腔调,叫着——让童华离开,说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他也被我逼得心冷,指着我鼻尖回了我一句极绝情的,愤愤而去,再没回头。
望着童华的背影,我并不留恋,只觉得不该这般伤他。可,又能怎样?有这么个老同学老乡随在身边,我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哪能达到……可当我带着一半轻松一半无奈的黯然往回走时,一声呼唤让我停下来——这是我第一眼见到梵朗。是的,他就像驾着金车飞马的阿波罗降临到我身边。人这东西真怪哟,童华追我三年,又是知根底的熟人,我除了那么点同情,对他别无好感。可就在这抬眼的一瞥间,我竟对这个体貌潇洒的陌生人一下子就心动了,而且不久就爱上他了。
梵朗说我不仅长得美,而且让人疼爱,让人心底里疼爱。他说这不是每个美女身上都能外化出的一种情愫。“……我半生描摩过不少模特,中国的、外国的、各种肤色的,我总是远远地审读她们,对她们的身体是当‘圣物’做心灵的膜拜——用线条色彩跟她们交谈,从没产生过凡心和欲念……可对你……”他这样剖白又说我,用了不少我似懂非懂的术语名词。我在他的目光和剖白中,很快就下定把一切献给他的决心,而且为我这决心为能遇上他而心底默默亢奋着。当然,只是亢奋而已。
梵朗从国外回来不久,是“师大”特聘的导师,他身上有不少奇异的东西。
一天,当我在众目下裸立了一个多小时后,穿好衣服告别时,他留下我,他把一个存折放在我手里。我不知所措,他动情地说:“快去医院吧,把你父亲的医疗费付清。”
这是让人发狂的一天,我整个心身在涌动。可我又像那风那云一样,没来处也不知去处。从医院出来后,我独自在街头徘徊很久……心,海海漫漫的……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给他打去电话,用发颤的声音说:“老师——你,要了我吧——”
3
梵朗从没对我说过“我爱你”的话;他总是说“我心疼你”。
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爱得如火如荼。他的爱是我用心灵和血肉感知的。在他面前,我永远是个怯怯的小女孩。可我又倾心地为他绽放,愿意让他每个细胞每根神经每个毛孔都充满我的爱意。这是我的所有哇。只是性爱,肯定不是他的长项。我们的爱,往往是引桥太长,主桥太短,这让我稍许遗憾。因为我的肉体自从被他浇灌、自从为他绽开之后,逐渐变成一张贪婪的网,总想把这唯一定向随时随地整个地吞咽,永存在我那网里。可他,总是在无限地柔情蜜意后,说:“好啦好啦,曼儿,别疯啦,快去站好——”那话那样子极像一位无奈的将军说他顽皮的士兵。尔后,他就又开始用眼睛和画笔跟我的裸体交谈了——那么凝神那么热情,眸子里满是自负和笑意。
而我,能把自己变成他一张张美妙的画儿,又是多么令人心醉。他让我摆什么姿态我就摆什么姿态,他让我站多久我就站多久。我那点肉体的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是啊,有多少妙曼的少女身躯能如我幸运。当初为父亲的病,不曾想过……我不愿再为他人做模特,我愿一生一世永远为他一人做模特,把自己的灵与肉完全融入他的画中。
我搬进了他为我买的大房子里,用上了我曾梦想过的一切,身边又是我最爱的人陪伴着欣赏着。我今生还有什么欲求?我,一个窘迫得几乎走投无路的小女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即使有一天,他说“曼儿,你该走了”,我也会含笑地吻别他,如他所愿地离去。
童华偶尔打电话来,他知道一些我的事,也算摆正位置比较理解了吧。他可是满嘴挂着爱的。眼下对他,倒正经有些关爱了——如歌中祝愿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甜畅的心,就像满盈盈的月光,无处不在。我常常在夜睡中,无由就醒来了,静听身边那细丝如歌的鼾声,望着他酣然睡态,我问自己,这一切是我吗?
4
可生活,是有节奏的。这天,梵朗说他要出去些日子,让我在家好好待着,听音乐看看书啥的,别惦记他。我什么都没问,一副乐意地点头乖乖的样子。不用说,我心在流泪,心里早有的一些遥远的朦胧的想象,逼近了。但是,那能安慰我的一贯知足论——继续用它柔顺的小手抚摸我的心。从早到晚,前庭院子书房卧室,我走走坐坐,无事做,连邻院那对年轻夫妻打羽笔球时夸张的笑声,我都琢磨好几遍。于是我又一张一张反反复复翻看他画我的那些个画。是的,能让自己在他的笔下如此光彩夺目,她不枉活这一生。是的,满屋子满院子明媚的阳光,逐渐驱走心底的烦闷,像在告诉我——我青春的生命和未来是足以能赢得无边好运的。莫愁莫愁。
他干什么去了,其实我知道。因为走得匆忙,他出门时把手机忘在家里了,我看到了他忘记删除的短信——朗,我回来办事,可能要多呆些日子。飞机今天下午3点到。爱你的慧。这是自从认识他那天起,我就曾想到过的。这么多年,才情如此出众的大艺术家怎么可能还是单身?可那——是他的妻子还是他情人?他们相处多久了?那女人长相性格如何?年龄多大?她跟我等同吗?看来,她肯定恋他,可他还爱着她吗?
我虽然压根儿不愿思谋这事,可这些疑问总往脑子里钻,也像无所不在的阳光。
那天,梵朗回来取手机时,我正好从卫生间走出来。我脸色苍白,眼中可能还有泪——我刚刚呕吐过,还没来得及把心里的那个大疑惑澄清。他看着我,忙抱住我问怎么啦?是不是生病啦?我紧晃头说“没事没事”,一面把他手机递过去,脸上是平和的笑。
他亲了我一下,似乎有所指地说:“好好在家等我,可不许胡思乱想啊。”我又是点头,乖乖的样儿。直到从窗里望着他的车开走,泪才彻底从眼中蓬勃涌出,一发不可收。其实,这泪有一半为幸福而流,因为我断定自己怀孕了,算下来,起码有一个月多。
我想,我不必再为未来多想什么了,因为肚子里的小生命将把我和他永远地扭结一起了,没有什么再能使我们离散。即使有一天,他说“小曼,你该走了”,我也会和我的孩子一起吻别他,轻松地离开这里……那一天,我只盼望仍能有这么充足的阳光。
5
梵朗说,怀孕女人只有一个幻想,便是那飞天的小天使。他搬来几大本画册很有兴致地翻来指给我看。而且还特意买来一对精美的挽弓搭箭的小天使摆在我床头。
他说,从原始心理学分析,希腊神话中小天使的形象就是从怀孕女人的幻想中升华出来的。自从知道我怀孕,他给我讲了许多希腊神话和圣经的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小天使、爱神和圣母玛丽亚,他说“这也是胎教”,而且说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西方文化。不知怎么,这话听起来让我有点冷。他快活得像个孩子,经常趴在我肚子上久久谛听。他守我的时间多了些,柔情蜜意得让人心颤,性爱几乎成了抚爱,这让我忍隐着失落。更让我失落的是,他经常接到电话就匆匆离去,而且每逢这时际,脸上笑容僵了,话也含浑。我知道他有难处,可不,谁能没难处呢,何况这样的极品男人。每到这时我总是说“快去,快去吧”,一边帮他整理衣服找领带,脸上仍是笑。
一天,童华打来电话,说他知道一些梵朗的情况,我虽然厉声警告“不要你管”,可还是听他把话说完。他说——这个姓范的画家,绝对有老婆,可能在国外,听说他老婆家特别有钱。他说:“小曼,不要幻想了,他不可能堂堂正正地娶你,快离开他吧,你欠他的钱,我来帮你还。”实话,童华越来越让我感动了。近来他给两家报社拉广告,收入挺可观。可我还是不能怂恿他。我用和蔼的口吻对他说:“童童,别想我的事了,我是不会离开的。你还是自己赶快找个合心的姑娘吧。”他一下挂了电话。
我坐在阳台上,望着天边的两颗星,一遍又一遍听着他喜欢听的那首格林卡的小夜曲。那乐声像温存的水波久久地抚慰着我,那乐曲的每一层柔曼的音波都浸润到我心的深处……后来,直到几十年后,那乐声那音波都随时在我心头涌荡。
三天后,他回来了。我平和地说了我的想法。我说:“梵老师(他好久不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了),你不要有什么担忧,更不必为难什么。为了报答你(我也没说爱),无论怎样我都会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成人的。即使是一个人,孤立无援……”
梵郎没说什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暗夜里,他脸上有一种肃穆,冷冷的不常见的。让我隐隐担心。其实我怎能没有他呢?我可以不要未来,孩子怎能没有未来呢?
6
保姆小青进了我家,是个爽快也很勤快的小姑娘。我们俩相处得很好。为了生个健康宝宝,她经常陪我去散步。我们还一起到超市上买来那么多玩具、婴儿所有的用品,还买来一只小摇篮。当我眯着眼、哼着歌、想象着晃动那摇篮时,我想我会是这世上最坚强的女人的,因为我要做母亲了,我会无所畏惧地面对一切人生的风浪。
小青是钟点工,午来晚走。她对我对这个家羡慕极了。她说:“曼姐,你可真有福气,梵老师这么爱你。他人又帅又有学问又有钱。”这话,让我心里不太是滋味。
他不在的时间越来越多了,那催命的电话总来。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心烦忍着,为了腹中的宝宝我也该愉愉快快的,不是嘛。童华的电话仍时不时打来,我仍然不准他胡说八道,也没告诉他怀孕的事。不知怎么,无论是地上的灯光还是漫天的星光,我总找不到他的所在。直到后来很长时间里,依然如此。这就是我跟他共同的悲哀吧。
临产了,B超说脐带绕着婴儿的脖子,必须动手术。在送我进产房时,梵朗伏在耳边说了我盼了很久、可他从没对我说过的三个字——“我爱你”。我见他眼中有泪光,而我的眼泪早大滴大滴地涌出。是的,这三个字多珍贵呀。但愿这三个字和他眸子里独有的星光能伴随我一生。让我永远为他为我即将见面的宝宝祈福。
是的,当我躺在产床上时,还以为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一梦醒来,我的身边空空,宛如整个世界的毁灭,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小青那张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脸……家还是原来的家。是啊,它仍属于我。可从心里,它似乎从来都没属于过我呀。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抱走了,我没见上一面。我无论怎样地伤心哭叫,怎样地逼小青都没用。
五天后,小青递过一封信来:曼儿:
实在对不起了。这也是我永生的遗憾。
眼下,我们的儿子正跟我在一起——我们已是在阳光充足的悉尼。他长得七分像你三分像我,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天使……放心吧,我们会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会把他培养成小艺术家的。
曼儿,我是爱你的。可我毕竟欺骗了你。我结过婚,缘由种种,我没法跟她分手。我们的事,一开始她就知道了——我的一生一直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谅解了我,但要我把孩子带走,因为她不能生育也不想生育。
房子留给你了,产权早立在你名下。留在你卡上的钱,足够你过一辈子。
但愿我们在梦里在画中相见吧……
辜负你的梵朗
这年冬月落雪时,我还在痴痴地望着那小摇篮,和那满墙的他画我的画。我总琢磨着,阳光照进来和没照进来,那画中的人大不一样。我问小青,小青也答不出。
又过几天,童华来接我,让我跟他一起回老家过春节。我疯了似地捶打着他,揪他衣服,让他带我去悉尼,去找梵朗、找我的儿子、找那个有阳光的画中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