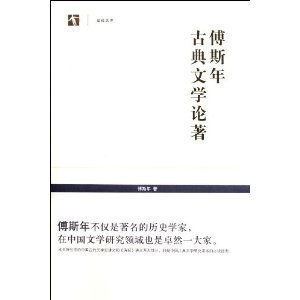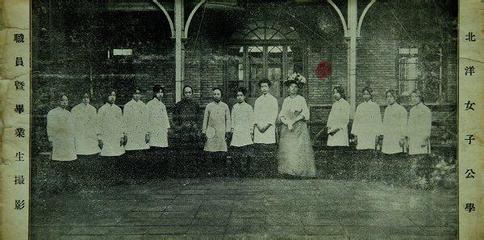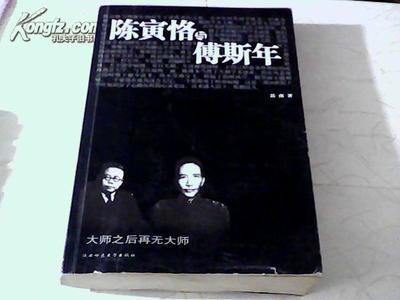摘要:“五四”之后26年主客易位,毛泽东已是一党领袖,跃跃欲试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但傅斯年还是傅斯年,傅斯年就是傅斯年,依然保持着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不失大体。
(1945年7月1日,中共领袖在延安机场迎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代表团。右一为毛泽东,右六为傅斯年。来源:网络。)
宋江一流 堂哉皇哉
书、儒不是祸乱的根源,苛政、暴政才是祸乱的根源。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以参政员身份,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一行,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商谈国共合作事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欢迎。
行前陈寅恪致函傅斯年,不看好他们有陆贾、郦生说动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调侃“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
访问团在延安停留4天,因北大的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晚与傅斯年深谈。“五四”之后26年主客易位,毛泽东已是一党领袖,内掌约130万军队,外有强悍苏联扶持,跃跃欲试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但傅斯年还是傅斯年,傅斯年就是傅斯年,依然保持着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不失大体。
夜谈之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和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傅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此处“我们”应指傅斯年、罗家伦等当年“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你们”应指蒋介石、毛泽东。
对傅这句话的解读,有人认为是“狡猾识趣”(岳南《南渡北归》),有人认为是“挖苦毛”(周为筠《文化没有两岸: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笔者浅见,傅这句话的潜台词既有自嘲,也有自谦。所谓自嘲,是指“五四”时期固然轰轰烈烈,如同流星般的陈、吴;所谓自谦,是指为蒋、毛成大业的主角登台,暖场演出。
同行的左舜生无礼、浅薄,竟然不分主次、不分场合,向毛纠缠要见念念不忘的影星蓝苹。哪壶不开提那壶,枉为参政员,毛冷言谢绝。傅斯年按照士大夫的儒雅传统,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爽快答应。
7月5日,毛泽东题赠条幅,书晚唐章碣《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另附短信称“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笔者百度查证大量《焚书坑》诗出处,均为“坑灰未冷”,而非“坑灰未烬”。)
(1945年7月5日,毛泽东赠傅斯年条幅,并附短信。来源:网络。)
对毛泽东题诗尤其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有多种解读,例如“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笔者浅见,毛赠诗用意两层:一、互谦;二、自得。
所谓互谦,是对傅斯年自谦的互动。傅斯年是国士,成名极早,凭“五四”运动总指挥一事就可青史留名,毛泽东十分清楚。毛勉强算半个北大校友,准确说是北大工友。傅自谦自己如流星般的陈、吴,毛也自谦即使如傅而言,蒋、毛是成大业的项、刘,也是没读什么书。毛在附信中说得明白,傅“过谦”,他述诗“广之”。既然是“广”,或者扩充傅的功绩,或者扩充自己的不足。
所谓自得,既是在学问上显露功底,又在国事上暗示雄心。就学问而言,傅斯年学术功底深厚,中西文化合璧,毛泽东没有机会以延安整风的手段让其臣服;而是平辈论交(条幅落款“书呈孟真先生”),在史学大家面前,自信展示自己的史学积累。就国事而言,秦始皇以为焚了书、坑了儒,就可以江山永固,实际上还是“帝业虚”、“空锁祖龙居”;不读书的人照样造反,在北大学问不如傅、名气不如傅的人照样指点江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
毛泽东的自得,与6年前的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遥相呼应,隐约也是20年后“书读得越多越蠢”(毛泽东《“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的“反智化”引子。毛在文革时再将《焚书坑》诗题赠政治战友、铁杆粉丝江青。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焚书、坑儒、愚民,保不了江山永固。不读书的陈吴、刘项纷纷揭竿而起,一呼万应,很快埋葬外强中干的秦朝。书、儒不是祸乱的根源,苛政、暴政才是祸乱的根源,才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最大威胁。失民心者失天下,“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黄炎培回到重庆,很快写了本《延安归来》一书出版,称赞中共的民主,“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感觉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傅斯年的观感另类,大相径庭。
据罗家伦披露,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单独聊一夜时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是自由民主的斗士。既不可能崇拜蒋介石,更不可能崇拜毛泽东,反左倾立场更是鲜明的“一根筋”。1938年,他给蒋介石写信状告孔祥熙贪腐、忧虑失去民心时,分析“抗战以来,政治上有一甚大之危险,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急遽左倾是也。”(《上蒋介石》,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85页)他与李济闲聊时也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话锋一转,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
毛泽东对傅斯年很快彻底死心。1949年8月14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对胡适、傅斯年、钱穆3人点名批判,并扣上在大小知识分子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的大帽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