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40年个人感言<?xml:namespace prefix = "o" />
因为种种原因,为数不多的个别曾经下乡知青浮出水面,在政界商界崭露头角,仅仅这一点,知青下乡,就被不少人莫名其妙渲染为什么“青春无悔”。对于这样一种浅薄无知的逻辑,相信只要亲身经历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绝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以自身经历来驳斥这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的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由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那一代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带来多么难以估量的世纪性大灾难。回首古今中外历史,希特勒也好,秦始皇也好,任何历史上的暴君独裁者,都没有这样的损招。
追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根源在于所谓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源自毛泽东臆想的理论——知识分天生就带有原罪,必须与工农结合才能够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故此,从1949年后共产党获得政权后的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以邢燕子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掀开了上山下乡的帷幕,但其时不过是极小范围的折腾,并未大面积成为国家行为。只是到了60年代中后期,当成千上万的大中学学生停课闹革命,疯狂的浪费大好青春年华,无处可去,就业上学都无门,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一大难题后,毛泽东才无可奈何却又是落井下石般,大规模将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抛向边疆农村。一则缓解青年就业出路,二则防止被释放心中恶魔的学子一旦醒悟心生反骨,危及政权稳定。
在当时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人压根不知道如此大规模驱赶城市青年下乡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知识青年本人及家庭只是出于生存本能抵制,或者无奈消极的服从。当然也不排除,在那个特殊的洗脑年代,也有部分当事者对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谎言深以为然而踊跃加入其中。
40年前的1975年,笔者不幸也添列知识青年下乡大潮之中,未能躲过那一劫,以自己亲身经历,见证了那个荒唐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细微末节。正是这个政策改变了我父母哥姐一家人的命运,从重庆迁移到了峨眉山市。
上世纪60,70年代之交,居住在重庆渝中区解放东路的我们一家,哥哥姐姐还有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被无情的卷入知识青年下乡的大潮之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隔壁邻居两个女中学生都不幸成为下乡对象,彼时重庆市中区知青下乡被统一安排在川东地区的黔江地区酉阳秀山武隆等,出于对那个陌生的大山地区的恐惧,他们曾经求助于我们,希望能够以亲戚名义,下乡到我们老家渝北沙坪一带,亦即退而求其次,重庆附近的农村总比偏远的川东大山地区强。其时我姐姐倒是幸运,年龄超过中学生却又只是小学毕业,故被当局划定为“超龄生”,未被列入知识青年行列,得以逃脱下乡的厄运,按当时土政策即可安排工作。(曾经有过重庆大钢、港务局的机会,只是那时家境贫寒,无力贿赂街道办事处主任而泡汤。)但是1971年,知识青年下乡的厄运却不商量的降临到我哥哥身上。可悲的是,几年前少不更事的哥哥还傻不拉几的成天不上课,去动员高年级的下乡对象,其方式是骚扰性质般让其家庭不得安宁,令其不胜其烦,抗拒不过,被迫下乡。如今火石落到自己脚背,哥哥一下子着了慌,面对要么云南支边,要么黔江大山区插队的两难选择,哥哥没了主意,恰好其时父亲从西藏建字部队整体撤回四川,支援新建成的成昆铁路落脚峨眉。那时天真的我们误认为重庆大城市知识青年要下乡,峨眉小地方应该可以躲过一劫,于是匆忙决定举家搬迁峨眉。孰料,峨眉虽是小地方,毛泽东的光辉同样不留死角——到了峨眉,单位依然隔三差五催促哥哥必须下乡!可气的是,连在重庆得以豁免的不属于知识青年范围的姐姐,也胡子眉毛一把抓被强行列入下乡对象。那个年代小人物的命运怎么能够对抗大时代?好在其时恰逢征兵,哥哥应征入伍,总算躲过下乡!但姐姐却被他们紧紧盯住不放。与之对峙几年,姐姐就是坚持不下乡,等到1975年我高中毕业,单位神气起来:不管怎么说,你家无论如何得下乡一个,没有商量余地!(当时政策规定多子女父母身边可留一人照顾,一般而言都是老幺留在城里可以豁免不下乡。)不得已,为了年龄超大的姐姐坚持不下乡,40年前的1975年9月,作为末代下乡知青的我被迫下到农村去。
好在峨眉县小,我所下乡的农村距离家的位置也就20多公里,往返也还算方便,与那些去云南的支边青年和偏远山区知青相比,我的处境相对好很多。但是那个年代的我,求知欲极强却得不到满足,放弃求学增长学识的大好时光,成天在田地里与当地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争那些本来就得不到基本物质满足的农民利益,一直到1980年才受惠于顶替政策回到城里参加工作脱离农村。
那时虽然没有如今的资讯发达,全都被蒙在鼓里,懵懵懂懂,但渴望求知,渴望摆脱农村愚昧而艰苦生活却是人之生存本能。当时脱离农村的渠道也有,比如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当兵,局部招工等,但那得贿赂掌管知青生死大权的公社大队干部,舍此无他。后来听闻过此间种种惨象。为了脱离农村,有人自残,也有女知青奉献贞操,种种手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个人而言,顶替父亲参加工作,到了国企,算是幸运。而相当一部分同龄知青,因熬不过农村生活,被骗进入铁路大集体(集体所有制),这一进如同嫁错人一般定了终生。当初信誓旦旦不影响“三招”(招工、招生、招兵),后来全是戏言,所有进入大集体的知青都如同关进囚笼一样成为二等公民,在许多方面都被歧视,待遇也与全民企业相差甚大。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回首那段知青经历,可谓惨痛惨烈。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君王,没有哪一个敢于这样草菅人命一般,把青年学子如同牲口一般驱赶到偏远乡村,受苦受难,令其在长知识,长身体时心身倍受创伤。时至今日,相当多的当年知青因个人文化素养被下乡耽误,以及所谓国企体制改革,下岗失业,人到中年,却万念俱灰——所有这些,难道还要让知青们青春无悔???
从个体看,每个知青都因上山下乡运动备受摧残;从国民整体看,整整一代人学业中断,人文素养缺失,乖戾之气充斥,全体国民素质因此大踏步严重倒退,乃是知青下乡最为根本的祸患!如此祸国殃民的损招,还好意思鼓噪什么“青春无悔”???
再从理论上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但之前他又信誓旦旦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此悖论,如此矛盾,如此精神分裂,不是玩弄普通百姓于股掌的愚民术是什么?以绝大多数过来人的知青亲身经历看,哪个知青从那些自身素质低下,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身上得到过良好的精神素养?相当一部分知青下乡后困于生存窘境,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浑浑噩噩,不单自暴自弃,同时也危及当地农民正常生活秩序。如此“双输”局面,难道还要重演,才令一代学子不“青春无悔”?
对于那些患上精神狂想错乱症的人而言,最好的办法,不妨让他们的子女主动放弃学业,再来上演一幕新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是否会发自内心大呼小叫“青春无悔”。(诡异的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对知青运动,一方面口头赞颂,另一方面却暗地里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那里。)
事实摆在那里,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毁了知青个人的青春年华,更整整毁掉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令其成为行尸走肉般的空壳。纵观当年知青现状,除开个人凭借自己的醒悟和努力,稍稍有些良知学养的极少部分知青,尚能反思反省外,那些极个别的曾经的知青依仗父母庇荫爬上高位的官吏,即使身为掌控百姓生死大权的重臣,也难以有所作为,因为那个时期的底色已经难以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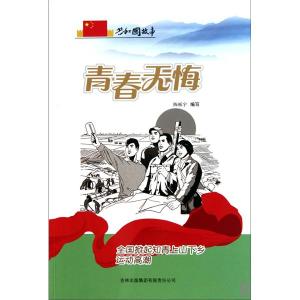
知青下乡,当代中国难掩之痛!却被无耻文人任意涂抹打扮,歌功颂德,粉饰美化,不知居心何在。据悉,北京已经有人紧锣密鼓在张罗筹建什么知青纪念馆,不单从舆论上肯定那场祸国殃民的下乡运动,还企图以永久性的纪念场馆让人们对其恬不知耻的颂扬赞美。如此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为真,岂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匪夷所思?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巴金老人几十年前就倡议建立文革纪念馆,让人们记住那过去惨烈的一幕,警醒人们绝不能让其借尸还魂,重蹈覆辙。但这样的建议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与此同时,若干年后,怪异的是,修建知青纪念馆,意在为其大唱赞歌,却有人津津乐道并付诸行动?难道这就是神奇国度的神奇之处?!
知青下乡,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罪孽深重?由不得御用文人鼓噪,听一听曾经的知青们吐露心声,方能明辨是非,分清黑白。我们有理由相信,若不是当年整整一代人被愚昧的驱赶到偏远山乡和边疆,而是按部就班升学就业,得到正常的社会滋养,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我们及其子女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常言道:百年树木,十年树人。那失去的十年,那下乡的一代,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我们现在能够轻易盖棺论定的!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