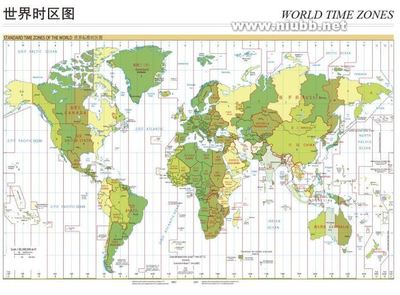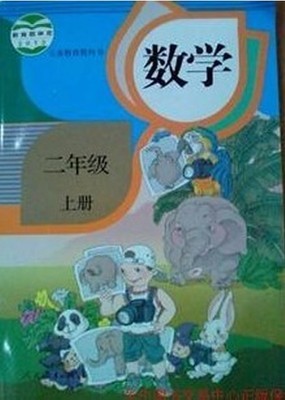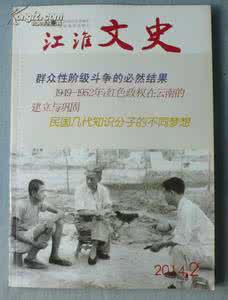
一
我们知道梦想有两种:一种是大的,宏大的梦想,从国家出发;另一种梦想是从个人出发的。1930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其实,真正的梦想是从每一个个人出发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20世纪的中国大致上是由三代人决定的:一代人我们可以称之为“80后”,第二代人可称之为“90后”,第三代人可称之为“00后”。换句话说,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这三代人的梦想就是那个时代决定中国方向的梦想。他们的梦想迄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乃至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以胡适等为代表,在政治上以毛泽东等为代表,他们的梦想的较量和竞争、挫败和成功,又决定了中国的未来;190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在年轻的时候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整个20世纪就是由这三代人所决定的。
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人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这是一个80后在100年前发出的响亮声音,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曾付诸实践的梦想。我在20岁时就读过这番话,40岁以后重读,对宋教仁那一代人的梦想有了更深的体会。它不仅是具体的,也是超越的;它不仅是关乎制度的,也是关乎人格的。
今天我们的梦想,关乎个人物质层面的多,关乎社会需要少。而100年前80后的梦想可以如此的宽阔。虽然那只不过是宋教仁一个人或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正是他们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1913年3月18日,两天之后宋教仁将要被子弹击中。那一天,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发表演讲,主题是从革命党向普通政党转型。他认为,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之前是革命党,是为了推翻清王朝而存在的;革命成功之后,必须转型为与其他政党地位平等的普通政党。他说:“革命党与政党先后事实上说,本非同物,就性质上说利国福民、改良政治的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态度、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他比较了革命党和普通政党的异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分是——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当时有人说,听孙中山演讲,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演讲,坦诚动人,是大实行家;听宋教仁演讲,条分缕析,是大政治家。一个80后的年轻人,竟然用自己的梦想主导了那个历史的段落,他的死足以令一个国家的历史改弦易辙。
那个时代,如果只有宋教仁孤身一人孤独地站到历史舞台上,就根本无法去尝试这样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去推行他的梦想。在他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曾3次出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是1885年生的;做过众议院议员的李肇甫岁数更小,是1887年生的;还有宋教仁早年的同学,1884年出生的胡瑛,他最后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这个名单可以继续开下去。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80后有那样的梦想,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精英,同样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有相当多的政治共识。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 ,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当他们的君主立宪梦破了之后,1911年的冬天,他们都选择了共和,张謇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共和的士绅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1912年8月,在宋教仁主导下,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党派成功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党参与的国会参、众两院直接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选举虽然有教育和财产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口参与了选举,但大体上是公正、公平的。在那个短暂的时光,宋教仁曾为梦想成真欢呼过。
当宋教仁们忙于在中国推行他们梦想的时候,比他更年轻的,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暗杀了重要的革命党领袖陶成章,此事成为他一生得意的杰作。同是80后,他们的梦想也并不相同。1881年生于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他跟宋教仁就很不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后来自述,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二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周树人说自己颓唐了,历史就翻到了90后那一代。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得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放的视野,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气质,有新的方法论,他要给中国引入全新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胡适迅速成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寸。他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
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人一贯倾向于一步登天,一夜之间造出个天堂来。胡适把新的方法论带到青年学生和知识界面前时,人们确实耳目一新。很多人嫌他浅薄,他也确实没有那么高深莫测。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他的话明白如水,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他不相信社会的进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他担心那将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看来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他们的不同梦想根本上影响了未来中国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有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萧楚女、毛泽东,有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有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有孟寿椿、康纪鸿,有王光祈、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吴俊升、杨钟健、康白情、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主张国家主义的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则创立了中国青年党;孟寿椿、康纪鸿等则创立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大批的人则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他们都在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有自己的梦想。王光祈是一位音乐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不幸在留学德国时英年早逝了。他离开中国之际曾写下一首去国词:“山之涯,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依。”不料这一去不是短别离,而成了永别离。1936年,因积劳成疾,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德国,没有回到中国实现他少年中国的梦想。当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间,要把中国变成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时代的激荡中,最后他们的梦纷纷被撕裂了,分别做起了各不相同的梦,一批人做了共产主义的梦,一批人做了三民主义的梦,一批人做了国家主义的梦,也有人做起了教育救国梦、实业救国梦、文学梦……各自奔着自己的梦想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1919年之后的30年,中国就是这一批90后不同梦想之间的角逐、竞争。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实现这样的梦想,即使这个梦想最终没有落地,他们也此生无悔。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生命、真实的梦想当中,不管是英年早逝的王光祈,还是那些活的更长寿的90后们,他们都没有虚度此生。
三
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做梦的142个人中,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看见了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了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很不相同。在这些做梦的人当中,有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者3人,加之下一期补登的朱自清和梁漱溟,实际上做梦的有144人。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更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空想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的梦想是,把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的共产主义理想捏到一块儿;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都是梦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 田地三四亩、种菜一二垄。令人遗憾的是,在144个人的梦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梦、法治梦。只有一个作家楼适夷,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着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最珍贵的当是这样的公民梦,很遗憾的是做桃花源之梦的人远多于做公民梦的人。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非常漫长的过程,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那一群,也是这个民族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一群,很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但是他们同样活在一个古老的中国,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他们没有成为一个以公民为志业的知识分子。
此时,鲁迅那张年轻的脸已变成一张冷峻的、横眉冷对的脸,用他那惯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和笔调针砭现实。他向来是反对做梦的,看见那些人做着桃花源之梦,他写下这样的话:“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预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把这些人嘲笑了一番。在4月15号的《文学杂志》上,他还发表一篇《听说梦》的文章。文中写到: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写得怎么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鲁迅是不做梦的。不做梦,也是一种做梦的方式。这是1933年的中国,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我们看到他们梦的质量,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四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又会怎样做梦?1897年出生的章乃器在90后里是偏小的,他是一个银行职业经理人,也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6年3月,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题目叫《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发表在《平民》周刊第4期。他虚构了一个叫黄子孙的人,1945年元旦做了一场大梦——
他梦见孙中山先生没有死,在连任了两届大总统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孙先生已八十高龄,但还很健康,整天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每天写日记,名为“社会报道”,发表在每一份报纸上。
他梦见国共没有分裂,共产党在友善的空气中成为独立组织。
他梦见全国人民都以主人翁身份热心国事,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同情,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各政党间的政见也大同小异。
……
他梦见,由于市场的开发无可限量,国民收入比20年前提高了10倍,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
他梦见蒋介石5年前就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军职,到各国考察政治、经济,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非常欣赏美国人民自由、平等、公开、坦白的作风。他环游世界归来,继林森之后被选为第四任总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触民众方面,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许多已被杀害的人们都活着,而且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都在国营大屠宰场里工作;大大小小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有些变成了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有些改行到医院做看护去了;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在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人被分配在大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做助理秘书,负责每天给主管拆信……
我们都知道,在那20年里,他所梦见的一切都未曾发生,那是黄粱一梦。“黄子孙”也许就是做黄粱梦者的子孙。他所说的都是梦境,真正是黄粱一梦。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他在1946年11月4日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政府改组,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孙科、宋子文,还有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环坐讨论国事。行政院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国共两党的军队根据整军方案进行了整编,向“军队国家化”的理想跨出了一大步,敌对情绪差不多已完全消失;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进行民选总统、议会;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
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做他的梦想。真正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中国正处于国共大打出手的前夜。在他的梦中:一篇大触当道之忌的社评一发表,即为万民争阅,有人建议封了这张报纸,不料当道者却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家事就是众人的事,人人得而议论,我怎么可以堵众人的嘴不让讲话呢?……报纸的言论,错误的不去理它,有理的我就采行,不更有益于国吗?……报馆是封不得的。”这段故事传为美谈。
政府对报馆毫无特别限制,办报如同开小店铺一样,不须特许,不须登记证,或开或关,自生自灭。
记者节那天,男女老幼自发地会集在能容纳10万人的广场,为新闻记者加冕。他们用报纸折叠成王冠模样,给所有记者戴上,上面写着“真”、“正”二字,一方面称他们是真正的记者,一方面说他们代表着真理和正义。加冕完毕,万众欢呼。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可以称为民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梦。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这一天是中国的记者节,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
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报纸,既有属于执政党的,也有属于在野各党派的;既有代表大企业家的利益,也有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各种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非触犯刑法上的诽谤罪,要被告上法庭,“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广大人群虽然没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大书,但他们都懂得三民主义,都能正确地了解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只要不把人民当人看,不管报纸印得多么漂亮,卖得多么便宜,也没有人看。
这个“九一之梦”同样也是黄粱一梦。1948年9月,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有点像鲁迅,目光冷峻,他说:“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老于世故,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声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
五
政治学家萧公权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有一次问了杜威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什么?”杜威想了想,回答说:“中国文化过度了。” 胡政之说的“人们老于世故”,在“中国文化过度了”这句话中可以找到答案,世故、早熟,把人际关系看作第一等重要,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
胡政之的确是很了解中国的,他不像王芸生书生意气,什么“九一之梦”、“做一个现实的梦”,都是白日梦、南柯梦。什么“二十年一梦”,都是黄粱一梦。梦注定了还是梦,注定了都要在一夜之间陨落。
胡适微笑着,这是他的招牌笑法,跟鲁迅的横眉冷对构成了最鲜明的反差。鲁迅一生走不出老绍兴的阴影,走不出闰土、阿Q,走不出那个土谷祠。他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阿Q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自己。阿Q有一条辫子,我们都有辫子,人人都有辫子,别以为只有别人有辫子,却看不见自己的辫子。
相对而言,胡适要阳光得多,也开放得多、包容得多。在他脸上看得见真正发自生命内心愉悦的那种笑容,他希望用这样一个姿态去面对苦难的中国,一个古老的中国。他的主张从不过激,他始终坚持得寸进寸,从每个人出发,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离开北大前不久,1948年9月4日曾在北平电台作了一个题为《自由主义》的演讲,阐述他的自由主义梦想。他说,“在近代民主国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许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
仍然是一点一滴的求进步,也就是他在1919年提出的“得寸进寸”。贯穿他一生的就是得寸进寸,不急不躁,他没有改变过,所以他一直在笑,一直笑得很舒展。他的学生、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听说蒋介石政府要胡适入阁做官,极为着急,发电报劝阻他:“与其入阁,不如结党;与其结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言论思想方面,不适合直接从政而卷入权力的漩涡当中。决定未来命运、方向的也许不是政治家们,而是那些作家、思想家们,没有他们,那个中国就是苍白的中国。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鲁迅永远活着,胡适永远活着。而很多曾经有权有势的人,随着肉体生命的消失,永远地消失了。权力是一时一地的,短暂的,而思想、精神是永恒的,可以穿越时空。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爱因斯坦已说得很清楚,真正可贵的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当然是有梦想的个人。
一个时代要戛然终止,内战要决出胜负,胡适和傅斯年那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痛苦。他们知道自己追求的那一切也许都没有机会、没有可能了,他们即将离开大陆。1948年12月31日,他们在南京长江边上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同样是陶渊明的作品,可是与他的《桃花源记》不一样,这首诗中却有着“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的悲怆,师生二人背诵这首诗的时候,潸然泪下。可以想见他们为什么落泪,那一代知识分子无论做着什么样的梦,怎样不同的梦,那一刻就是他们梦断的时候。梦断了,以后的命运不可预测。他们的眼泪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他们的眼泪是民国最后的一滴泪,他们的眼泪一直流到今天,流在历史的深处。历史的深处有无数的误会,其中就包括那些不同的梦想,以及梦想与梦想的角逐。
[作者系著名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等,同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已出版著作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