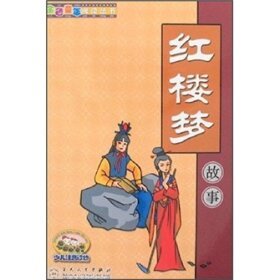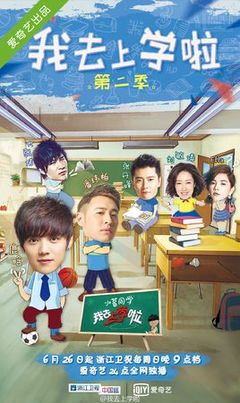“季羡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北京大学东语系,甚至整个北大。1962年中国的政治气候非常适合父亲安家。北大领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我和姐姐看了这种情况很不舒服,很不理解,心里顿时感到一股寒意。之后,每当我们看到母亲一个人孤单地睡在客厅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就忍了下来,没有说什么。现在看来,夫妇在中年分室或分床而居也是人之常情,可那时候我和姐姐很难理解,母亲恐怕也难以接受,不过母亲向来是逆来顺受,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建议我也搬过来和父亲他们住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根本没有打算那么做。那时,我和姐姐都已经结婚,有了各自的家,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父亲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意思。后来,有人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和你住在一起,好照顾你们。他嘿嘿一乐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新家就这样安置好了。父亲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家度过了1962年、1963年两年平静的生活。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父亲家带来了相对的平静。父亲忙着他的著述和各种社会活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姐姐则开始了为维护这个家庭的默默努力。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北大家里去看望,干活,送东西。我们那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父亲的工资则是我们的十多倍,我每个月都要给叔祖母和母亲一些零用钱。姐姐则给她们添置一些衣物。父亲每月给母亲一定数目的钱做生活费,要她记账,至于够不够,他不再问。因为他不肯再掏钱,母亲也不敢再向他要钱。缺了就拿自己的积蓄弥补。母亲常为此而为难。我和姐姐去北大的家,父亲是不拿钱出来的,都由我和姐姐贴补。我们如此顾家,引起了我爱人和姐夫的不满,这竟成了以后我们感情上不和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父亲一家的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和谐、温暖的。每个星期天中午,总有一顿团聚的午餐。我们还经常邀请李铮夫妇参加。当然,父亲有吝啬的一面,也有浪漫大方的一面。他每逢“五一”、“十一”、“春节”,总要邀请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的我的五舅、舅妈和我们全家一起外出游玩,吃大餐。
我们几乎玩遍了北京各处景点,如故宫、天坛、颐和园、动物园、大觉寺、樱桃沟、八达岭等,吃遍了多处著名餐馆,如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
1959年、1960年我和姐姐分别结婚。可是直到1962年、1963年、1964年,我的儿子季泓、女儿季清、姐姐的儿子何巍才分别出生。有了第三代,全家都为此而欢欣忙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之火重又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农村“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父亲、姐姐和姐夫,我和我爱人都要去农村参加“四清”。孩子只好交给叔祖母和母亲照顾。平静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故乡之行
暴风骤雨过去,父亲动了思乡之情。他自打从德国回来,还一直没有机会回清平老家看看。在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特别是九死一生的“文革”后,他想起了老家。1973年暑假,叔祖母先行去济南,随后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孩子一行五人,回到了祖籍山东省清平县的官庄。我们从德州下火车,然后乘长途汽车,到清平下车,便有村上的驴拉的板车来接。
这是我第一次到祖籍探望,那一马平川的黄土地,稀稀拉拉的树木,无精打采的庄稼,黄土砌成的矮房,那就是我们季家的原籍,就是我们的根。到了村里,我看到我祖父卖剩下的那五间瓦房还在,那是在当地政府特别关照下保留下来的,已经破旧得不能住人了。我还看到小时候父亲站在里面躲避母亲追打的水塘,拣枣吃的枣林,那些也都还在。我们住宿的三间屋子是别人家准备结婚的新房。这时村里的老百姓,呼啦啦地全来了。门外场地上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从穿着上看,他们是十分贫穷的。绝大多数的小孩都光着屁股,赤条条地围拢在那里。他们的脸色又黄又黑,毫无光泽。他们把我们当成天外来客,犹如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终日围观,不肯散去。他们为我们睡觉的床上装上了蚊帐,可是满屋的跳蚤却使我们大受其苦。
父亲带着我们去祖父母坟上磕头,会见他的妹妹季香和其他很多亲戚朋友。他小时候的哑巴朋友还在,两个人比划着说了一阵。父亲和他的妹妹、亲人和老乡之间虽然亲情浓厚,可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日积月累,沧桑巨变,天上地下,怎么说得完、说得清楚。他们谈了很多,但是更多的是无名的激动。村支书从全村搜集来一些肉、蔬菜,招待我们。他们包的水饺,馅子用的是带皮的肉丁,但味道鲜美极了。他们做了一个烧茄干,其味道之美,风味之殊,真是一绝。我惊叹民间竟能有如此叫绝的烹调手艺。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屡屡让他的妹妹吃菜,可她低着头一个劲地说:“俺不吃呢。”几天内,我没见她动过一次筷子。对此,我感到十分压抑。那时正是夏季,村上的孩子大都不穿衣服。我给他们照相,眼前站着的是一大群赤身露体的孩子,就像到了非洲原始部落。父亲曾从北京给村里寄过很多书。这时一看,连书的影子都没有了。据说都用去卷了烟,有的擦了屁股。父亲感到很惋惜,随后就再也不寄书了。可是后来父亲还是为家乡建立了图书馆和小学。在官庄的几天,父亲的心情很好,兴致勃勃。他曾试着去井里打水,别人替他把水打上来,可他又挑不起那挑水,只好作罢。
离开官庄,我们一行又去了济南。济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叔祖父购置的那所四合院仍在,只不过东南北三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由别的人家居住,只剩下西屋由二姑的儿子住着。于是我们便都挤在那里。父亲会见了许多朋友。
父亲和我们一起游览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等名胜,品尝了济南特有的饭食:甜沫、油粉、油旋、烧饼果子、小笼蒸包、虾子茭白、蒲菜包子……父亲、四舅,我和孩子们还专程去洛口镇看黄河。那河依然宽阔,流淌的依然是那浑浊浓稠的黄泥水。那座有名的跨河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上。我们沿河走去,正巧看到一位渔民捉到了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鲤鱼。黄河鲤鱼誉满天下,父亲慷慨解囊,花五元钱把鱼买下,雇车回家,请我的三舅掌勺,一鱼多吃,足足地品尝了一通。
这次回济南,唯一不愉快的是有关翻建济南房屋的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济南的那所四合院,属于我们家的只剩下西房五间了,多年失修,已经摇摇欲坠,非修不可了。叔祖母思虑一向颇远,想把济南的房屋翻建一下,作为后方基地,以备不时之需。可是,父亲却没有那个打算,那时他经济上并不宽裕,在建房的事上不是很情愿。此前他已经点过头,也拿出了一点钱买砖买瓦,但到济南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买材料花钱多了,翻盖了房子又没有用处,于是不肯再出钱,甚至对叔祖母有所怀疑。这使叔祖母很为难,心里极不痛快。母亲和我私下里也不满父亲的做法。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后来落实房改政策,政府又把整个院子还给了我们家。不过很快,整所院子就被拆除,改建成居民小区了。到此,我们在济南的家便已不复存在。
孤家寡人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
在文章的前面,父亲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还乡》里讲述的故事,老母亲被儿子遗弃;一个则是父亲自己实际上遗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又通过遗弃别人而达到了成为悲剧性人物的目的。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非常劳累、疲惫。
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胀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致、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譬如,一次他自己更换床单,之后颇觉伤感,竟至暗暗流泪,感叹无人关照。实际上,我姐姐经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父亲不让姐姐换,理由是嫌换得过勤会把衣物洗坏了。他常对阿姨说,衣服穿不坏都洗坏了。姐姐自然也常常替叔祖母和母亲更换衣物,父亲就会感到冷淡了自己,心里就不愉快起来。父亲有这种自外于家庭的内心情结,就使他在感情、亲情上很难完全融入家人之中。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因为他听有人说我造了假账!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只落得,家就是他,他就是家。“求仁得仁”,“悲剧性的人物”,都实现了,他创造了人间奇迹,确属应该庆贺:“快哉!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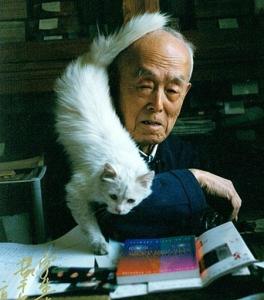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