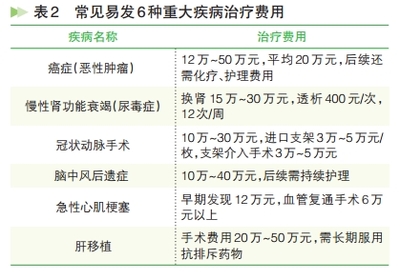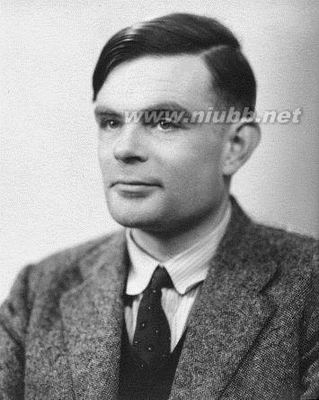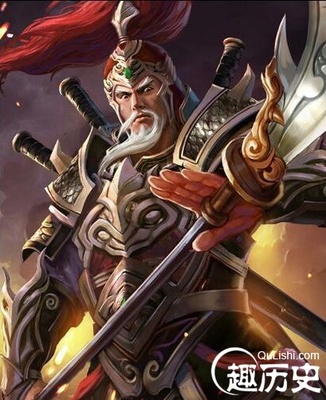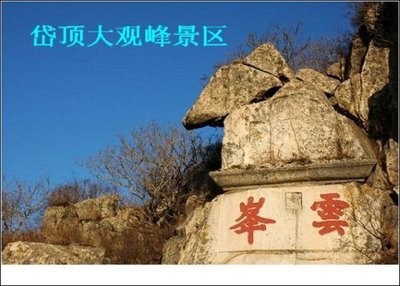范旭东已经成为范氏家族后人现世生活的一个局部,有据可查,但无处抓挠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林红在电话里再三拒绝采访,她说:“我现在走到上海大街上,问我的同龄人,你们知道自己吃的盐是怎么来的吗?没人知道,没人知道范旭东是谁。”
范旭东是林红的外祖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被视作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14年到1945年,他第一个用几口铁锅建造了精盐厂,第一个办起制碱厂、烧碱厂,第一个创建了硫酸铵厂,第一个建立全国精盐协会,第一个在川西南开辟出新的战时化工基地,在这里,他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发明了“侯氏制碱法”。
企业家与科学家的最佳拍档
林红在电话里说“没人知道范旭东”,这话还有一个后文。她紧接着说:“但是人人都知道侯德榜。”这话没错,在侯宝林的相声里就提到过“他做的碱疙瘩好吃”。“外祖父去世以后,侯德榜没了可以商量出主意的人,”林红说:“他能做的就是给孤儿寡母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范旭东在1945年10月4日下午三点去世。资料中记载,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后因为民心所向履职。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11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能够保障范氏后人生活无忧,就是林红所说的“物质上的帮助”。
范旭东是企业的经营者,侯德榜是企业的技术领袖。范旭东比侯德榜大7岁,从1921年到1945年,共事24年,这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合作向来被认为是珠联璧合。
南京化工(前身是永利南京钅亚厂)的退休职工张定国曾经就此采访过很多当年的老职工和侯德榜的秘书,他分析说,两个人合作成功首先是因为两人大目标一致:振兴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侯德榜和范旭东都是留洋学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对于技术的推崇、爱国心和抱负是一致的。
其次,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是很淳朴的。
范旭东非常佩服侯德榜的技术水平,侯德榜也曾经将自己在海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送给范旭东作礼物。“从我对范旭东女儿和侯德榜秘书的采访来看,他们之间很少有那种世俗的往还,送东西啊什么的,很少。”张定国说。按照林红的回忆,在外祖父去世以后,侯德榜和范家也是不通信的,只不过有时侯德榜来上海出差,顺便看看外婆。这两个人都没有太大的物欲,范旭东除了喜欢每天喝老母鸡汤和牛奶,生活并不奢侈。侯德榜在生活方面更是叫人放心。据他的秘书回忆,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常常午餐就是一碗阳春面。他去美国纽约购买仪器的时候,为了给公司省钱,连公共汽车都不坐,每天步行,回来的时候,张张票据都非常清楚。
第三,他们合作起来分工非常明确。范旭东主管公司经营,侯德榜主管技术。
四十年代,侯德榜在重庆的制碱法开发曾经遭遇挫折,是范旭东顶住内外压力,继续支持侯德榜,才有最后“侯氏制碱法”的成功。在抗战时期,他们可以说一个主内一个主外。1937年,天津和南京相继失守,公司将设备和200多名技术骨干运送至重庆大后方,整个转移过程就是侯德榜负责的。而范旭东这个时候考虑的是解决永利迁移之后的资金问题、在西南重建新的化工基地的问题。张定国总结说,范旭东是个实业家,而侯德榜是个科学家。范旭东能够完全尊重侯德榜的科学事业,侯德榜的技术力量也能够为范旭东挣钱。
事实上,除了事业合作以外,这两个人的私交不可谓不深。
范果恒曾经讲到一个小细节:在武汉码头上船前往重庆的时候,父亲不小心把两皮箱的日记、资料遗失到江中,他的第一反应是要跳进江中打捞,是侯德榜死命拉住了他。1939年,范旭东的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一路上就是侯德榜护送的。1945年范旭东去世,也是侯德榜打电话通知范果恒的。所以范果恒对侯德榜的感情一直比较深,解放以后,她还常和丈夫去北京探望侯德榜。
范旭东和侯德榜虽然合作好、交情好,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张定国1963年进入南化工作,曾经见过侯德榜几次,在他的回忆里,侯德榜完全是一个朴实的知识分子形象:“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苍老,个子不太高、内向、不太爱说话,一到工厂马上就换工作服,像个老工人一样。”相比之下,范旭东的脾气非常直率、相对火爆,容易发脾气、容易得罪人,也容易交朋友。范果恒曾经回忆说,有朋友来家里坐,如果抽烟的话,范旭东会径直站起来把窗户打开,也不管客人作何感想。“文革时候,侯德榜是靠边站的,”张定国说,“他几次要求不拿工资,免费出来搞科研,但是‘四人帮’不同意。他最后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果换了范旭东,他恐怕忍不下来。”范旭东除了事业,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侯德榜则喜欢听听音乐。另外,范旭东衣冠楚楚,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习惯喷一点进口香水,这样讲究的生活习惯也是侯德榜所没有的。
有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两人之间的差异。当侯德榜的制碱法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英商卜内门公司的驻华代表李特立来找范旭东,要求合作。这个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碱销售市场,看到永利公司在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能量,也很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对于李特立的要求,侯德榜和范旭东反应不一样。范旭东当场就骂走了李特立,而侯德榜则委婉地说,不妨跟他们接触一下。“他这话是有潜台词的,”张定国说,“因为侯德榜追求的是技术,所以他希望合作,能够得到一些技术支持。但是范旭东不。一个是科学追求,一个是经营利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民族感。”
张定国作为南化的员工,开始接触范旭东的事情是在“文革”当中,他负责跑档案馆,抄写批斗展览需要的相关材料。抄着抄着,他发现范旭东并不是宣传中所说的那个“坏极了的资本家”,于是开始了对一个真正的范旭东和他的后人的寻找。1985年夏天,他第一次按响上海巨鹿路888号的门铃,见到了范果恒。“有一件事情,她从1985年一直跟我讲到2003年,”张定国说,“她说,以前一直说我父亲是被国民党气死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他就是太玩命,积劳成疾,累死的。”
后人的生活和回忆
事实上,林红从来也没有见过外祖父范旭东。早在她出生的三年前,范旭东已经去世。那时候,林红的母亲、范旭东的长女范果恒还在美国学习音乐,没有能够见上父亲的最后一面。林红对于外祖父的了解,都是从外婆和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外祖父是个很严肃的人,家里的书房和实验室都是不准孩子进去的,吃饭的时候也不准讲话。”
范果恒2003年在南京出席纪念范旭东120周年诞辰活动的时候,曾经回忆了一桩小事,这个事情印证了女儿林红对于外祖父“严肃”的推测:范果恒小时候随父亲和永利公司住在天津,那时候永利公司有个网球场。有一次,范果恒想去打网球,她爸爸就跟她说:不行,这是给员工预备的,你没有这个特权。
1939年,范果恒21岁的时候就和妹妹范果纯一起被送到美国留学,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范旭东。1945年,范旭东在重庆突然病逝,她因为战时交通不便,没有回国奔丧。一直到1948年,已经成家的范果恒才带着不满1岁的大儿子林毅坐美国的运输舰回国。在这以后的50多年里,和父亲范旭东相处的日子一直是她生活中不断闪回的片断。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曾经对来访者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走得太早了。”
在范果恒的回忆中,即使在父亲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拘谨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父亲的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多了。两个女儿出生以后,父亲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母亲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事实上,范旭东当年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永利公司的经营上,至于家庭,则完全由妻子一手打理。林红回忆说:“外婆总是把头发剪得比我还短,然后全部往后梳起来,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她的脚也是缠过不久就放掉的。”
对于范旭东的家人来说,他的妻子无疑是更亲近、影响更大的人。范旭东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他死后,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妻子当家。在林红的印象里,外婆也是一个严厉的人,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婆掉眼泪。从1948年开始,永利公司每年向范家遗孀赠送股息,作为抚恤金。应该说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因为林红知道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而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果恒买下上海巨鹿路的一层老洋房,用的就是这笔钱。
但是,在林红记忆中,老外婆仍然持家甚严:三个外孙、外孙女,从来没有零用钱,只有每天一毛钱来回上学坐公交车。林红的弟弟林翔喜欢集邮,那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只能靠自己每天走路上学,省下车钱来买邮票。家里有佣人帮忙,但是几个孩子从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夏天开始,一切就要自己打理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的午饭。而且和外祖父一样,外婆也是不准孩子在饭桌上讲话的。“她经常跟我们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林红回忆说。
在林红看来,外婆和外祖父最相似的一点就是不歧视女孩子。“范家没有什么男权思想的,”林红说:“外婆和外祖父一样,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很开明。我外祖父一生没有儿子,也没有说很遗憾的话。”范旭东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学习的都是和范家生意无关的专业。“我母亲是学音乐的,那时候,学音乐能当饭吃么?但是外祖父他们一点没有反对,他们觉得,只要子女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就去做。”
回忆起范家解放初期的生活条件,林红形容是“赤脚光地皮”——因为没有任何的房子、地皮和产业。范旭东的死非常突然,没有给妻儿留下什么遗产。他死后,妻子来到上海,由范旭东生前在金城银行的好友帮忙,把银行手上的一栋洋房租给范家人居住。这就是林红一家人现在住的华亭路上的房子。
范家后代的命运和华亭路这个街道的命运有着微妙的契合。解放前,范家搬进华亭路二楼二底的小洋房,这条街上的房子是以前犹太人贩鸦片挣了钱修的,算以前的高尚住宅区,按照上海一位女作家的说法,是“黄昏的时候会有小男孩在阳台上拉小提琴的”。后来,这条安静的街慢慢变成了上海的假名牌服饰集散地,“我每天下班推着自行车进来,挤得头都要点到地上。”林红说。慢慢地,范家的房子里又搬进很多不认识的人,共用一个院子和厨房,成了“七十二家房客”。记者见到林红的时候,她没有请记者去家里坐,她从院子里走出来,小心地掩上门,把院子里一桌兴高采烈的麻将关在里面。这种弄堂里的人际关系,对于范家的后人来说,是门新学问。
在2006年春天,他们的去向是这样的:
范旭东的妻子谢氏已经去世35年;

大女儿范果恒去世两年;
二女儿范果纯在美国的老人院里;
大外孙林毅1966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电筒厂工作,几年前去了美国;
外孙女林红从齐齐哈尔下乡回上海以后,在图书馆工作;
小外孙林翔在福建做教师;
大外孙媳妇肖苏苏几个礼拜前回到上海,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购置的巨鹿路的房子里。她告诉记者,这次回来就是准备把这层老房子卖掉。她非常客气地开门,穿过小花园,请记者上楼看看。
这些铺着柚木地板、镶着壁炉的房间,范旭东并没有住过。上海这个城市,十年就能走完百年的路,外祖父范旭东已经成为他们现世生活的一个局部,有据可查,但无处抓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