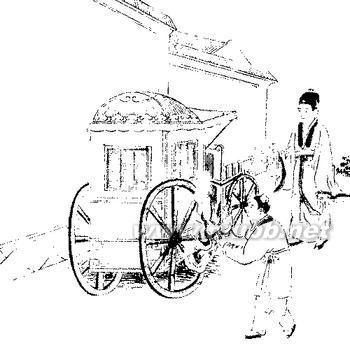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国家治理思想有着重大的转折和变化。秦朝的快速灭亡,使汉初君臣对法家思想展开质疑,以陆贾为代表,告诫刘邦不得“马上治之”,促使汉朝开始了武功向文治的转化。以贾谊为代表,给文帝上“治安策”,要求统治政策全盘改弦易张。秦制的遗产,汉朝的楚风,与国家管理上的儒学复兴交织,由此,中国古代的儒者开始正式从政。儒者从政又对儒学的发展方向形成重大影响。陆贾作为集儒术、道术、纵横术于一身的人物,把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结合起来,开创了政治儒学的先声,儒者从此由讽喻朝政走向辅佐朝政。贾谊对秦亡教训进行了深刻揭示,为西汉进行新的战略设计,以“古代最好的政论”讲述儒术治国,使儒学在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等级秩序、推进礼乐教化、弘扬民本思想、完善太子制度等方面形成了系统观点。这一时期的儒学,带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在儒家管理思想的演变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和皇帝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经过汉代的传承,秦的王朝体制延绵达两千年。学界把秦汉之间的制度传承概括为四个字——“汉承秦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汉代的各项制度规范多数出自秦朝。然而,强调汉承秦制者往往忽略了秦与汉的差异性。西汉王朝的开国者,多来自楚地,在骨子里渗透着楚人的不羁血性。汉继楚风,从而扭转了汉初国家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汉人对秦制的调整,秦制就可能延续不下去。从秦到汉,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延续性和国家管理的路径依赖,又可以看到文化的变异性和社会风俗对国家管理的重大影响。学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往往对汉承秦制较为重视,而在文学领域,往往会首先感受到汉人身上的楚人习气。汉代的制度框架是秦制,而汉代的精神状态是楚风。或者说,汉制即秦制,汉韵即楚韵。把握大汉文明的特色,这两者不可偏废。 在秦制与楚风之间,汉代走出了一条国家管理的新路。在这条路上有两个人值得重视,一是告诫皇帝不可“马上治之”的陆贾,二是以秦为鉴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他们的思想,不仅在汉初影响到当权者执政风格的变化,而且对以后的王朝体制如何治理社会起到了探路作用,最终走向以儒术治国。 陆贾是楚人,不过,他的学问来自儒家。清朝唐晏在校注陆贾著作时说,陆贾是荀子的学生,而且是谷梁学的祖师,排在汉代公认的谷梁学大师申公之前。正是这种儒学功底,为他扭转西汉治国方向奠定了基础。在秦末天下大乱中,陆贾追随刘邦,鞍前马后,以口才著称,战争中陆贾表现出来的不是儒家学问,而是纵横捭阖的游说才能。他曾经在刘邦进军关中时游说秦将,在楚汉相争时与项羽谈判。在刘邦建立汉朝后,陆贾列在首位的功绩是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不过,就管理思想而言,陆贾的最大贡献,是促使刘邦立国后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化。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是看不起儒生的,而陆贾难免显露出儒者本色,同刘邦谈话时常常引用《诗》《书》,所以遭到刘邦的叱骂:老子的天下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凭什么要遵循《诗》《书》?陆贾正色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历史经验看,吴王夫差,晋国智伯,都是崇尚武力的强者,结果却亡在了武力上。秦朝严刑酷法,迷信暴力,结果却断了自家香火。如果秦朝建立后改弦易张,“行仁义,法先圣”,陛下还能得到天下吗?刘邦说不过陆贾,就下令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写出十二篇治国镜鉴。“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 · 郦生陆贾列传》)可以说,陆贾在扭转汉初的治国方向上是有所贡献的。 陆贾之后,在治国理论上进行系统思考的还有不少人,沿着儒学路径向前走的代表是贾谊。贾谊是河南洛阳人,少年聪颖,“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18岁时,就被河南郡守吴公看中,网罗于门下。汉文帝时,吴公升迁到中央当廷尉,向朝廷推荐贾谊,于是贾谊被征召到首都任博士。 博士是秦汉设置的顾问应对官职,没有编制限制,没有具体职掌,以议论朝政为业。所以,博士能不能发挥作用,主要看皇帝是否重视。秦始皇时,“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虽有几十名博士却“备而弗用”。汉文帝时的博士就不一样了,文帝由藩王入主朝廷,在朝中缺少亲信,急需得力辅佐。而贾谊在博士中最为年轻,头脑敏捷,应对得当,在一群老朽冬烘先生中脱颖而出。“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的思想很杂,其少年的知识基础当以儒家为主,欣赏他的吴公又从李斯之学,贾谊有可能会受到其影响,司马迁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即对法家学说比较熟悉。他还跟随御史大夫张苍学习过《左传》,在汉代率先对《左传》进行文字训诂研究,汉代《左传》的流传实际是从张苍和贾谊开始的。另外,贾谊还受到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尽管刘歆称文帝时“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刘歆传》),但贾谊带有汉初儒者不同于先秦儒者的明显特色,即杂糅百家,兼习道法。这一过程,到董仲舒方告完成。 贾谊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渴望在政界施展才能。文帝也确实欣赏贾谊,很快就把他由比六百石秩级的博士提升到比千石秩级的太中大夫,相当于今日由副处一跃而进入司局。级别倒是小事,关键是他因为皇帝的重视而进入了决策核心。政策的变化,法律的修改,对诸侯管理策略的调整,都出自贾谊的提议。于是,文帝打算把贾谊进一步提拔到公卿之列。但是,朝中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大,一批元老大臣担心贾谊得宠,开始攻击他。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个特点,欲速则不达。如果贾谊停留在太中大夫的层次暂时不动,尽管元老仍然会讨厌新贵,但多半会看在皇帝的面子上容忍他。现在皇帝有意让他进入三公九卿行列,这就危及到开国元勋的地位。于是,以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为代表,下决心要把贾谊拉下马。他们对贾谊的评价是“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政事”,必欲除之而后快。文帝的帝位又是这些元老与吕氏争斗而得来的,朝中几乎没有文帝的亲信,他只有表现出对周勃等人的高度尊敬和信任,皇位才可稳当。所以,文帝只能牺牲贾谊,把他外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是当时唯一的异姓王,经过汉初的权力纷争,其他异姓王都已经被铲除干净了,只剩一个根本掀不起风浪的长沙王,这个王爷自己都提心吊胆,何况辅佐他的太傅。把本来在权力中心的贾谊派给长沙王,几乎同流放差不多。贾谊自己也灰心到了极点,凭吊屈原,写《鵩鸟赋》,摆出一副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架势。这个时候的贾谊,已经淡漠了儒家的进取理想,沉湎于楚风骚韵。如果当时有现在的医疗检测手段,恐怕能给他检验出抑郁症来。 天无绝人之路,文帝思念旧情,召见贾谊。时值文帝正在祭祀,便在未央宫的宣室询问贾谊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再次给文帝展现了他的才能。诗人李商隐曾感慨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给世人留下一个文帝对贾谊用非其才的印象。其实不然,在汉代,祭祀是政治行为中相当重要的活动,鬼神与国家安危大有关联。但是,文帝受制于大臣,不能把贾谊直接用到中央关键岗位,也是实情。这次召见后,贾谊的命运明显改观,他被改派为梁怀王太傅。同原来的长沙王太傅相比,这两个太傅大不一样。在长沙王那里,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在梁怀王这里,等于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梁怀王刘楫是文帝的小儿子,聪颖好学,深得文帝喜爱。让贾谊辅佐梁怀王,无疑等于明示:好好干,总有出头之日。贾谊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在辅佐梁怀王之馀,又开始上书朝廷,畅言国事。根据学界的考证,贾谊最重要的政治论述《治安策》,就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然而,世上不如意事总十有八九,意外往往会打乱事先的筹划。梁怀王坠马身亡,对贾谊的打击太大。史称“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而死。很明显,贾谊既为梁怀王的夭亡而哭,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哭。但一切都无法挽回,梁怀王死后仅仅一年光景,贾谊也郁郁而亡,年仅33岁。 秦王扫六合,睥睨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制。外表十分威猛的帝国,却被不读书的项羽刘邦推翻。高唱《大风歌》的汉高祖,以楚风的豁达消解了秦制的戾气,却未能改变自身的赳赳武夫形象。此后西汉的变革,开始于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这一儒学复苏过程,同叔孙通、陆贾、贾谊、晁错都有关系。叔孙通最先以礼仪形式为儒术见用于朝廷做了铺垫,然而这种铺垫并不具有思想史意义,仅仅是让刘邦感受到儒术对维护皇帝的尊贵有用而已。陆贾真正开启了汉代儒学之端,他以纵横家的口才留下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名言,并提出了取守异势的基本思路。贾谊实现了儒家学说与帝制关系的改造,使仁政王道与中央集权融合,同时又在具体治国方略上吸取了法家的具体举措,把国家制度与风俗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儒术为主的治国方向。晁错在贾谊的基础上,向法家靠拢,在儒术的外表中更多地注入法家的内涵。到了董仲舒则以诸家渗透的方式完成了儒家学术的大一统修正,汉制由此确立。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深得汉制的精髓。给汉制奠定儒家基础和王者形象的,以贾谊最为着力;完成这一演变过程的,则以董仲舒最为出名。 儒学复苏和儒者从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陆贾和贾谊的政治命运,是儒者从政的一个范本。严格来说,从陆贾开始,儒者从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先秦儒者不少,孔门弟子有的在政坛相当出色,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列国纷争,在秦完成统一后,儒者还能不能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谁也难以断言。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给从政的儒者敲了一记警钟。叔孙通为此不惜放弃儒家的思想内涵,可以用谀言奉承秦二世,可以用楚服换掉儒袍讨好汉高祖,进而可以用古礼夹杂秦仪设计出朝贺仪式取悦皇帝。在叔孙通导演的朝贺仪式中,刘邦发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这不是儒家从政,而是儒者在政治面前的屈膝,所以,坚守儒家信念的人鄙视叔孙通。陆贾则触及到了以儒术治国的本质,但是,陆贾的形象,更多地偏于策士和辩士。同贾谊相比,陆贾要幸运得多,这种幸运,正是来自于陆贾对儒术的变通。以陆贾获取极大名声的出使南越为例,在游说南越王赵佗时,陆贾说服赵佗的观点,来自儒家的夷夏之辨和孝悌之道,而打动赵佗的方式却是王国安危和利害关系,显然,儒家式的道义观念,法家式的利害算计,纵横家式的危言耸听,被陆贾糅合为一体。陆贾的这种策略,使他既能做到要求刘邦“下马”,又能确保自己安然无恙。当他给刘邦提出“下马”建议时,既强调“行仁义,法先圣”,又推崇俭约,要求人主无为。陆贾的聪明,还表现在对待吕氏上。当吕后把持朝政时,陆贾称病引退,悠游享乐。但他又私下给陈平出谋划策,让陈平结交周勃以对付诸吕。文帝能够当上皇帝,也有陆贾一份功劳。文帝即位后,陆贾又担任太中大夫,后来再度引退,“竟以寿终”。班固在比较陆贾和郦食其、朱建、娄敬、叔孙通等人后赞曰:“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可以说,陆贾以其灵活变通,为后代儒者从政提供了一个榜样。如果说叔孙通是内圆外滑的“识时务”儒者,那么,陆贾就是内方外圆的“善变通”儒者。 贾谊同陆贾有相似之处,就是在思想上都受到道家、法家的影响,其儒家基调虽在,却已经不能回归到先秦儒学,只能根据大一统格局调整自己的治国学说。但贾谊与陆贾的不同在于,他的行为不善变通,有点“一根筋”,这同他早年一帆风顺有关。吴公的赏识和推荐,文帝的器重和提拔,使他不知什么是挫折,看不到政治的险恶。他本来要一鼓作气,主持汉朝的制度变革,“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文帝当然乐意接受贾谊的提议,按照《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文帝虽然高兴,但周勃灌婴等人不高兴,他们本能地觉得贾谊以年轻新锐的角色冲击着元老勋臣的地位,于是共同发力,把贾谊赶出朝廷。对于贾谊受到排挤这一事实,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源自汉代刘向,认为贾谊才高遭忌,庸臣排斥贤能。“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这种说法得到后代的多数人认可,尤其是怀才不遇或者才高见弃者,很容易对贾谊产生同情心理。加上司马迁把贾谊与屈原合传,更会使读者类比屈原而产生联想。另一种解释以苏轼为代表,他专门写有《贾谊论》,认为贾谊自己处置不当。苏轼也承认贾谊是王佐之才,但不能“自用其才”。汉文帝不用贾谊,错不在文帝而在贾谊自己。“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绛侯周勃是拥立汉文帝的首席功臣,太尉灌婴统兵数十万与吕氏一决雌雄,他们与汉文帝的关系,要比父子兄弟骨肉更密切。贾谊一朝被重要,就不知天高地厚让文帝“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不比登天还难?贾谊要想站住脚,就应该“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以高超的政治见解打动皇帝,以优游浸渍深交大臣,“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试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是亦不善处穷者也”。所以,苏轼认为贾谊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苏轼之所以专门把贾谊拿出来大发议论,其目的是为儒者参政提供一种思路。“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平心而论,苏轼的议论不见得公允。例如,周勃、灌婴与文帝的关系,并不像苏轼说得那样和谐。然而,贾谊不能忍辱负重,确属其短。可以说,贾谊的悲剧,为儒者从政提供了两方面的教训。从与叔孙通、陆贾的对比来看,贾谊是真儒者,进取和狷介正是对先秦儒者精神的继承,而陆贾的圆融,有可能使儒者失去自我;叔孙通的不讲操守,更会以投机行为使儒者变质。贾谊的可贵,在于其守住了儒家的根本。然而,贾谊缺少了儒家通达的一面,经不起逆境磨炼,这又使其人生走向偏隘。平心而论,汉文帝还是尽可能采用了贾谊的政治主张。所以,班固才称其“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此后历代王朝,儒者从政,基本上不出叔孙通式的放弃操守、陆贾式的圆通和融、贾谊式的耿介狂狷三种类型。而三种不同际遇,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形成不同的影响。 《新语》和汉初政治的转向 陆贾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新语》中。综观该书,明显以儒学为基调。四库总目提要说:“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馀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对这一提要,余嘉锡有详细的考辨。但大体来说,提要的定位是恰当的。尤其是对这种流传已久、影响广泛的古籍,论证其思想影响要比考证篇章真伪更重要。哪怕是伪作赝品,当它已经被世人当作原作真品用于社会时,它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语》从汉代开始,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值得把它作为古代管理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来对待。 四库提要把陆贾作为与董仲舒并列的“醇儒”,说明《新语》的儒学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但陆贾在儒学基调中渗透了无为和道术思想,所以,今日学术界也有人把陆贾列入汉初新道家。总体上看,陆贾所倡导的,是适应大一统王朝体制,以清静无为的手段,建立可传之久远的理想王朝。《新语》现存十二篇,有些恐怕已经不是当时陆贾所作而是后人羼入,不过基本思想逻辑保持着一致性。 《新语》的主要内容,是从强调道德仁义开始的。陆贾认为,仁义是治国基础。他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构建“道基”作为社会治理的框架,这是陆贾不同于先秦儒学的地方,说明他已经有了以儒家为主线,杂采诸子,实现思想大一统的倾向。这正是政治大一统的学术化表现。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整体观察,使陆贾为“王道”确立了自然法意义上的正当性。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先圣”确立了人道,人道展开就是王道。“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此后由“中圣”确立了教化原则,贯彻王道。“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后圣”则用五经六艺把教化具体化,建立各种礼乐制度。“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道基》)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王道演化脉络,并赋予王道以最重要的仁义内核。“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坚持以仁义为治国准则,就可上承天命,下诛暴虐,忠进谗退,扶正祛邪;不守仁义,国家就会走上秦朝二世而亡的覆灭道路。 道既具有经验性,又具有先验性。道在历史,亦在人心。所以,道既有传承久远的历史佐证,又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自证。陆贾称:“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术事》)一部《春秋》,不需要追溯到五帝三代,仅仅通过鲁国的史事记载,遵循天道与人道,陈述人世善与恶,就足以把治道说清楚。“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由此,陆贾放弃了先秦儒学言必称三代的旧习,而是立足于当下,明确了自己为汉代新帝国确立治道的使命。追溯历史教训,也不必上溯桀纣,有秦二世的例证足矣。由此,陆贾实现了儒学的一个重大转化,不是“兴灭继绝”,而是面向未来。 作为新兴起的大一统帝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大规模和有效性之间寻求合适的治理准则。先秦时期的国家规模有限,五帝三王的直接治理范围并不大。而先秦儒学论证仁政王道,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规模问题。像孟子那样鼓吹“百里而王”,在战国群雄并起时代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要说秦以后的统一王朝。荀子设想的以礼制规范天下,尚未得到实践证明。要复兴儒学,必须直面大一统帝国的广大范围。对此,陆贾的方案是:以仁义为价值取向,寻求合适的辅政助手,奉行无为而治的基本策略。辅政者就像君主之杖,“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辅政》)秦的教训,就是以李斯、赵高为杖。 对于如何选择辅政之杖,陆贾深受道家以柔克刚思想的影响。他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说众,商贾巧为贩卖之利,而屈为贞良,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辅政》)作为君主,在鉴别人才上,应该明白“察察者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同上)这些论证,明显把道家与儒家合为一体。 治理国家依赖人才,人才并不缺乏。就像名贵木材,自然生长在山林,就看君主能不能用。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山野之民,身怀不羁之能、德配圣贤之美者也大有人在。“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资质》)要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就需要君主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进贤良,退奸佞。 在治理策略上,陆贾强调取守异势,清静无为。他批评秦政道:“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无为》)相对于成文法制,陆贾特别强调教化和楷模形成的习惯规范。“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同上)这里陆贾所言,已经是《中庸》的德治主张,遵循儒家倡导的移风易俗途径。所以,陆贾所说的无为,不同于道家的崇尚自然,而是儒家的君子垂范。陆贾对理想的治理臻境有十分具体的描述,他说:“夫形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至德》)显然,他和孟子描绘的仁政场面异曲同工,孟子以“制民之产”来实现仁政,陆贾以无为和教化来实现仁政。 鉴于秦朝建立的皇帝制度,在信息传递上有着严重的屏蔽和扭曲现象,陆贾提出,统治者必须注意“辨惑”。与荀子主张的“解蔽”相比,荀子侧重于认知偏差和技术性信息扭曲,而陆贾侧重于社会偏差和权力性信息扭曲。尤其是针对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教训,陆贾强调,有媚俗而造成的信息偏差,有媚上而造成的信息偏差,两者都要防范。否则,视之者谬,论之者误。儒者要做直言不讳的君子,“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辨惑》)对于君主来说,“夫众口毁誉,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殊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而目缪心惑者,众邪误之。”(同上),所以,用人区分正邪,是君主第一要务。由此,陆贾确立了后来为政“亲君子,远小人”的基调。

从思想角度看,陆贾并未对先秦儒学进行深入的理论发掘,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把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把道家的治术与儒家的权变结合起来,把面向以往的儒学改造为面向未来的儒学,把儒者讽喻朝政的本色转化为辅佐朝政的间色,进而确立了“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主旨(《本行》),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开辟了道路。不过,尽管陆贾绝不言利,而且倡导“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的政治局面,却在客观上为儒者追逐利禄提供了正当途径。 《新书》和贾谊的治国策略 贾谊的治国思想,以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为其立足点。正因为他对秦朝的政治失误有深刻的揭示,所以能够对汉初政治提出全面的转变方略。后人谈到贾谊,往往赞许他“其才雄,其志达”;“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均见明人《新书》序)。他力图使汉朝克服秦制之弊,实现长治久安,可以说,贾谊是在陆贾之后,为西汉进行全盘战略设计的第一人。 贾谊是主张“顶层设计”的。他在刚刚进入决策中枢时,就提出对汉初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人可能觉得这些变革都属于形式,但在古人眼里,改正朔,易服色,相当于重新搭台另唱戏,是最大的变革。贾谊甫涉政坛就提出这些建议,说明其志向宏伟。这种整体变革尽管因为汉文帝立足未稳而“谦让未遑”,但其重要性却摆在那里,并最终在汉武帝手里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从秦到汉,在国家治理上需要这种变化。秦朝的体制下,皇帝只相信自己,对所有人都高度戒备,“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上》)精明如始皇,则大权独揽;愚蠢如二世,则奸佞当道。这种体制的要害,在于得志的大臣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奸诈小人。好一点也只是算小账而不识大体的刀笔吏执政,差一点就是架空皇帝排斥异己的赵高之流掌权。秦朝之亡,亡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没有从兼并战争的暴力欺诈走出来。汉初陆贾倡导儒术,但执政者仍然是打天下时的功臣集团。贾谊的改弦易张,表现出由暴力向仁义、由功臣向文官、由夺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西汉军功集团向文官集团的结构性转变,是从贾谊开始的。 但是,秦汉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大一统和君主专制已经成为时代特色。所以,儒学要成为帝国时代的治国主旋律,就需要找到儒学之仁义王道与帝制之大一统王朝的切点。贾谊把这个切点定位在加强中央集权上。他的《治安策》被毛主席称为“写得最好的政论”,就是从中央集权角度评价的。其主旨有三:一是强化中央威权,二是富民安定天下,三是教化移变风俗。在手法上,礼治、法治、人治三位一体,并由此确定了汉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贾谊对汉代的王国问题和匈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王国问题是内政问题,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把一切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又集中于皇帝,郡县制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然而,秦朝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迅速显现,尤其是对原属六国地区郡县的高压统治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反秦战争以原六国后裔与秦国的冲突展开。因此,在秦亡之后,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采用了分封制。在大一统王朝尚未找到有效直辖不同地区的方法之前,人类的基本经验就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哪怕这种方法已经显露出弊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时,只能用它。那些批评项羽与刘邦采用分封制是“开历史倒车”、是“错误的选择”的说法,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刘邦先封异姓王,又待时机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实际上是很稳健的策略。但到文帝时,同姓王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在平定吕氏之乱时,同姓诸侯王不遗余力同讨诸吕,而文帝本来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势力还不及他们,朝廷与诸侯王的裂痕开始扩大。对此,贾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强调:“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亲疏危乱》)给他们以优厚待遇,但“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藩伤》)。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藩国强者先反,只有长沙王因其实力最弱,故能忠于朝廷。以此推论,贾谊主张,“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彊》)。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正是采取贾谊的策略。 对于匈奴,贾谊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策略。所谓三表,即用适当策略向匈奴示之以信、爱、好,讲信义,表关爱,显喜好,以德服人;所谓五饵,即“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汉书·贾谊传》师古注)。三表是以儒术感召,五饵是以权谋引诱。可见,贾谊的思路,是把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儒法两家兼用并举,一切以维护汉朝利益为宗旨。 为了保证汉朝的统治秩序,贾谊主张,以礼制规范社会等级。为了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主张在制度上改变诸侯王与皇帝君臣不分的各种称谓和待遇,清晰界定皇帝与诸侯王的尊卑等级衣服物品号令规范,“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等齐》、《服疑》)。除诸侯王外,整个社会都要建立明确的高下尊卑等级,“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阶级》)为此,贾谊专门强调,履虽新,却不能戴在头上;冠虽弊,却不能踩在脚下。 尽管贾谊的思想掺进了法家的术和势,但在对儒家的民本思想陈述中,还是承继了儒学的基本观点。“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由此,在具体的管理中,推导出疑罪从无、疑功从有的原则。“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同上)单从这一论述看,贾谊的思想,即便比起孟子的重民思想来也不算逊色。 在推崇儒术上,贾谊特别强调礼乐教化,“厉廉耻,行礼谊”,主张“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他认为,从秦以来,包括汉初,重用刀笔吏,以法规条文为务,以细节害大体。管仲曾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当今为了追求利益而不顾一切,杀害祖父母者有之,伤害养母者有之,刺伤兄长者有之,盗窃国库者有之,抢掠祭器者有之,伪造朝廷公文诈取粮食钱财者有之,不胜罗列。造成这种道德沦丧的根源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利益角逐。廉洁奉公遭人嘲笑,为富不仁被人羡慕,秦亡教训在前,需要下大功夫矫正(《俗激》《时变》)。矫正的路径只能遵从儒学。所以,贾谊在批判商韩之术败坏社会道德的同时,即便吸取法家的某些策略,也力求用儒学修正其过分逐利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贾谊在反对奢侈浮华的同时,注意到了政策逆反问题。他专门论证了“瑰玮”之政,即政策意图和政策效果的相悖。所谓瑰政,就是“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应对这种瑰政的方法是玮术,就是“夺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瑰玮》)。说穿了,贾谊开出的药方很简单,即崇本去末。只要真正做到驱民归本,智巧诈谋自然无所用,淫邪奸盗自然不得生。这一观点并无新意,但贾谊把它和政策评价结合到一起。正如当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仅仅强调诚实是美德,但现实却给欺诈者以优厚回报,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只有讲诚信者的回报超过欺诈者,才可能走上真正的道德建设之路。儒法两家的结合,正是在克服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反差上能够体现出新意。 按照贾谊的设计,君主的个人品德和示范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他专门论证了太子制度和保傅问题,对太子的教导培养有详细论述。由于他重视礼与法的结合,重视人对礼法的作用,因而对辅政官员的培养、选择、任用和考察都有相应的论证,具体内容在此从略。 整体来看,贾谊的儒学,在先秦儒学的心性修养方面并无大的推进,然而在实践运用方面结合秦汉以来的政治需要有着新的发展,其学说省略内圣而鼓吹外王,使儒学的发展方向变为政治儒学。即便是外王,贾谊也具有某种国家主义的倾向,尽管他用的词汇是天下,但天下的内涵却是王朝。此后,这一方向一直是帝制时代的主流,直到宋儒的理学,才把儒学发展轨道重新扭转到性理儒学。可以说,贾谊奠定了帝制时代政治儒学的基本取向。 有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政治儒学的实际效用。汉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不成文制度“将相不辱”,就是来自贾谊的建议。他强调,仁义和法制,是君主的两种工具。“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制不定》)君主运用这两种工具要格外慎重。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简单的特权,而是要给士大夫保留几分体面。儒学特别强调“耻”文化,士大夫的约束也主要靠廉耻。贾谊直接批评高级官员遭受刑罚的副作用,说:“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命众庶见也。”所以,贾谊主张恢复古礼,高级官员犯错需要谴责的,以“白冠氂牛,盘水加剑”示意其自行面壁思过,而不需要执缚系引;犯错需要问罪的,听到追究命令即自行前往有司,而不需要械梏镣铐;犯有大罪需要处死的,指令下达即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而不需要刽子手行刑。贾谊认为,这样做,高级官员保持了尊严,朝廷维护了体面。“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阶级》)此后,西汉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规矩,以丞相为例,得到皇帝的信任为丞相执政的前提,如果有人弹劾丞相(以御史大夫弹劾最为常见),皇帝将弹劾奏章留中不发,则表明保持对丞相的信任。如果皇帝在奏章上批“诣廷尉”(字面意为到司法部门接受审理),那么丞相就必须自杀以表清白。这种“将相不辱”,从儒学角度看可以保持丞相的尊严,从皇权角度看可以保证丞相对皇帝的绝对服从。政治儒学的内在矛盾,就产生于这种细节之中。当然,政治儒学的学理构建,贾谊只是开其端者,到董仲舒方告完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