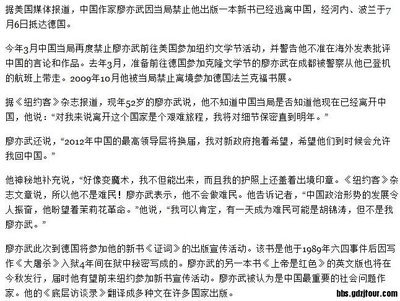——《中国纵横》读后
26年前,刚被纽约州立大学解聘的历史学教授黄仁宇,还在为他几经周折仍然无法出版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而焦头烂额。
之所以数度被出版商拒之门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本学术著作“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在中国历史领域,只有史景迁曾以这种风格写过。”黄仁宇在其自传《黄河青山》中写道。
黄仁宇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书出版一年后,已经声名卓著的史景迁在《纽约书评》上褒扬性的评论,竟然会成为本书(包括作者)跻身史学殿堂的一份“品质证明”。
已经去世的他更想不到的是,在他以“大历史观”而名扬海内的今天,迟迟才被国内普通读者所接触到的史景迁,却变成了一副“会讲故事”的十足趣味型学者形象——历史的误读往往就是如此吊诡。
在许多读者甚至学者眼里,史景迁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往往“很好看”,不过这种好看却让作品本身“看起来更像一本小说。”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就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我就是带着某种猎奇和消遣的心态翻开史景迁的学术自传《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的。
这部据说是其“一生论述精粹所在”的著作其实是一部论文及书评选集,共分五部分,即文化对话、儒学影响、中国社会、中国的革命及业师介绍。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我写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而呈献给大家的这本书所收录的都是我自认为最有代表意义的,它们最好地反映了我努力以一种公正的、全面的视角去考察中国的意图。”
在这些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0世纪,涉及人物从帝王到学者的论文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史景迁的宏观视野和问题意识。所谓宏观,不只是时间与空间的跨度,更是作者研究领域的宽广,从文学绘画,到制度经济、再到心理与性格分析,在史景迁笔下从来没有为研究方便而设定的“单面人”,而都是一些生活在具体的时代与制度下,有着生动的情绪变化与思想特质的立体的人。
而这种多维化的描述又与史景迁自身清晰的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让读者能通过他笔下的人与事清晰地触摸到一个个时代变迁中文化与历史的脉络。
尽管史景迁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欧美学术界曾被视为“野路子”,但他的思想并非没有“同道”——早在3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史学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而陈寅恪自己在此后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从50年代引诗证史的《元白诗笺证稿》,到60年代“以小人物见大时代”的《柳如是别传》。其史学研究思路与范式竟与素未谋面的史景迁有着惊人的暗合之处。
这一研究范式已经被当代史学界所高度关注,并将之命名为“新文化史学”,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而史景迁正是这一新研究范式内公认的大师和开创者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对于史景迁(包括陈寅恪)的不恭与调侃,实际上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一种诗学与史学研究中的“范式之争”。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在“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中,作出了精彩的评述。
在《中国纵横》一书中,这一“文化史学”的视野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对马尔罗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一系列描写中国的作品,学者赵毅衡曾惊异于国内知识界对之了解甚少,并将原因归结于中西方关注角度的差异。而在史景迁笔下,这一现象得到了更加中肯地评价:“把他(马尔罗)对中国的看法放在那些与他的生活年代距离最近的文学前辈们的中国观之中,要比把他视为一个革命的空想家更为有益。”
与此同时,史景迁的兴趣所及,从历史上的康熙大帝到现实中的钱穆这样的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也从宫廷奏折、笔记小说到个人回忆录,无所不包,他那支称得上出神入化的笔,总可以调遣到最合适、最优美的字词句章来写人状物叙事。因为这种杰出的才能,史氏曾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一笔三十一万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
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谈到史景迁的治学方法时曾说到,“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乐黛云强调,“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文化学者赵毅衡在其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的著作中也曾强调,对于西方借助中国文化资源而获得的文化成果,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并非没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要中国思想者作双重转化阐释——先还原到西方现代的文化动机上;再还原到中国当代的必要性中。
对于史景迁这样的史学大师,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正是这种“双重转化”,并在这种转化中重新找到其人其作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见,而不是一味纠缠于其“故事讲得好不好、细节说得对不对”式的吹毛求疵之中。把无心误读“变成”有意错用的人云亦云。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美)史景迁上海远东出版社
史景迁著作中译本一览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远东海外中国学研究·史景迁系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史景迁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模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一般做学问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博大精深,广引旁证,坐万分枯燥的考据般的冷板凳,另一类则深入浅出,走大众化的群众路线。史景迁完全是后一类的学家。在他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生涯中,几乎从来不发表专题论文,不参加史学会议,而专门从事发掘中国近代历史中有大众兴趣的题材,大书特书。史景迁是一位诗人般的史学家,很有个人魅力,他是耶鲁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一般的美国教授上课,通常有四、五十个学生,而史景迁则高达五、六百人,许多对中国历史毫无兴趣的学生因为史景迁的中国史教学而投入汉学研究。他每周三次上课,二次演讲,一次放幻灯录像,效果之优良,是别人难以匹敌的。
在写作方面,史景迁高度重视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结合。因此,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涉及独立的个人在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命运和挣扎,他把个人传记推到了顶峰,他写过康熙皇帝、洪秀全,也写过外国在华人士如利玛窦及一些平民百姓的独特传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