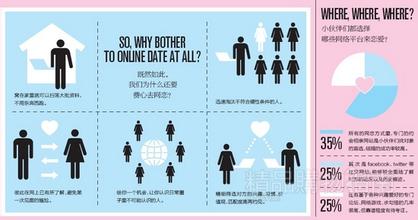系列专题:《认清贸易真相:贸易打造的世界》
10. 21世纪的世界经济 人们普遍同意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但对于"全球化"的含义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不想在此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深信,以最早期的全球化时代为背景,审视现在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什么是"全球化",还可以澄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现在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时通讯、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广告占据话语主导权的世界,它鼓吹形象就是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孩子,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看到的、关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趋势和争议。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本书,是因为我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代,世人除了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且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的制度结构,它往往隐而不显、演变缓慢;还会想了解大时代环境的循环变化。我们以过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通过探讨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今天所处的时代,以及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面貌。 因此,我们从反向切入,我们要问"全球化"不是什么。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总是由经济主导,有时,政治、文化的因素也扮演了主导角色。正如先前所阐述的,在过去,传教士、战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交流,同样,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译按:穆斯林国家类似红十字会的组织)等,也代表着没有获利心态的新型跨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网络。但它们无疑强化或抑制了跨地区的往来。追求利润的企业与非市场导向的组织相冲突时,企业无疑并非永远能压过后者的影响力:例如,国际社会针对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所采取的抵制行动,加大了某些跨国公司的成本压力,导致这一不人道政策的废除(跨国公司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为当时的白人政府提供帮助,迫害了大量黑人)。从俄罗斯到中非等多个地区,从纯粹商业的角度(例如天然资源丰富或劳动力教育程度高但成本低或两者兼而有之)来看,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资对象,结果外来投资却一直很少,这表明,不管是好或坏,当地的体制的确影响全球网络渗透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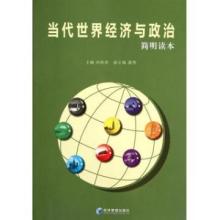
第二,正如上述例子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不像过去认为的,在于国家与公共领域不可阻挡的扩张,也不像今天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于国家的萎缩。事实上,正如某教授略带嘲讽的说法,国家只有在一个地方真正萎缩了,那就是在某些政治家的心里。如今,中央银行或许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设定利率,但在某些国家,中央银行可以设定利率,只是它们能这么做的时期很短,即使是50年前已列强国之林的国家,如今仍有很多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在网络、遗传学等新领域。现有或即将诞生的调查技术,使人类可以更大程度地掌握社会、市场。民意调查使今天的领导人,比罗斯福、丘吉尔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动向,更懂得如何让人民相信新观念或新奋斗目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工具是否同样高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两个世代前国力薄弱的一些国家(或不存在的国家)纳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影响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长幅度往往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儿童大部分(虽非全部)已享有小学义务教育,甚至往往享有中学义务教育;全球各地的游牧民族,大部分已被迫过上了定居生活,接受了国界与土地私有的观念,在某些例子里,他们因为政府修建水坝和其他工程而被迫迁居异地。此外,与世界经济进一步接轨,同时强化又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即使在最近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有些产油的国家,在靠石油收益而得以自上而下建立国家之前,往往没有办法向人民征税,进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影响人民;1970年时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之一,那时它只能粗略掌握境内人口数量。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有很多国家为了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人民的效忠对象常常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基本医疗、教育,以及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甚至美国部分都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