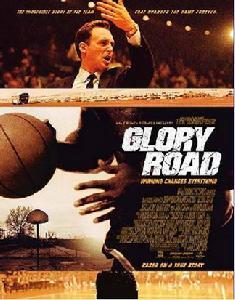北京编辑朋友传来一份对话活动的策划书,该活动围绕梁启超而展开,一共设置了三个题目,其中一题就是“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然而,该题目本身就不太梁启超,而是非常《新青年》,至少它带上了浓厚的《新青年》的思维色彩。在这个题目下,走向现代是一种选择,回归传统又是一种选择。

自1840年海运以来,传统与现代,或东方与西方,或新与旧,或古与今,作为一个问题始终纠结着中国知识人。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更加尖锐,当年梁启超面对过它,后来《新青年》也面对过它,并且他们先后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然而,真正对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产生影响的,而且是思维方式上的影响,显然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 《新青年》的文化态度很干脆,也很决绝,它一面倒地认同现代而排斥传统,并且把传统视为现代的阻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比如,陈独秀在《答佩剑青年》中,这样告诉年轻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革故更新”托出了陈独秀自己的新旧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传统与现代,在他那里变成了新旧器物,可以随时更换,而且必须随时更换。所以,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不独对政治发言,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论断:“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于是,《新青年》对现代之新和传统之旧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答易宗夔》)。作为新文化之子的毛主席,其《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不”之前,又加上了个“不破不立”。于是,文革流行的这“三不”加上“破旧立新”,其话语资源直接就来自几十年前以《新青年》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 然而,这主导了20世纪近一百年有关新与旧抑或传统与现代的话语权,并非20世纪的全部。当我们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这个核心年份定为现代的开端,我们不可忽略此前十多年,特别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如果说20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新青年》和新文化的时代,前一个十年从舆论角度讲,则无疑是梁启超的时代。那个时代,梁启超办的最重要的杂志便是1902~1907年的《新民丛报》。如果可以比较,《新民丛报》是新字当头,《新青年》踵其后,也是新字当头。但,它们的新旧观却截然两样,由此延伸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道路。 当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里宣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这是一个从新其内到新其外,又从新其个人到新其民族的扩展程序,可是这个程序里压根儿没有旧的或传统的存在余地,它们被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优胜劣汰了。但,早在14年前的光绪28年,即公元1902年,梁启超撰《新民说》鼓吹新民:“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各自新而已。”从国民自觉的角度,梁任公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看起来两个杂志先后新到了一起,只是梁启超的新,别有内涵,它非如后来的《新青年》把新旧打成截然两节,以新斥旧;而是力持新旧兼容,且推陈出新(此非推倒旧的,让出新的;而是从旧的当中推出新的来)。 这是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的开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里的要点不在二而在一。采补他者即鉴取西方,这是吾族走向开放与现代的必然之路,它也为后来的《新青年》所继承。但,因为《新青年》的“新”闪耀了一个世纪,却遮蔽了前此梁启超有关吾族走向现代之新的另一条道路。显然这是一条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但它对传统不是泥古不化,或原教旨,而是一种不断促其变化的积极保守主义。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此淬厉之淬,即让旧的东西淬火,以锻打出新;而淬厉之厉,是将旧的东西加以磨砺,使之焕然一新。惟其不断淬厉,传统的东西方才能保持新的活力。梁启超紧接着的比喻是精彩的,他把传统譬之为木,只有岁岁长出新芽,才能避免枯可立待;又将它喻之为井,必得涌泉息息不断,方可不致干涸。但,这“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这是一个精彩的新旧辩证法,也唯有梁任公才能作出这如此精彩的辩证。正是在回归传统的意义上,任公不惮自称守旧主义者,且为守旧二字正名:“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固有之谓也。” 走向现代,还是回归传统,在《新青年》那里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它只有一条路;但在梁任公这里,其现代之新,不是一条路而是两条路。什么是多元,什么是一元,这里就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二元对立的实质是一元独断,它不容二元并存,因此二元之间必然是你死我活。这样的表述很决绝: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即不把你堵死,我就流不了,不止住你的路,也就没有我走的路。在《新青年》那里,传统是现代的死敌,不塞堵,不终结,现代则无以流行。当现代与传统,变成这般不破不立的关系时,这既是传统的悲哀,也是现代的悲哀。 梁任公不然,他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论者,传统可以自新而走向现代,现代也须建筑于传统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当时流行于世者,无非新旧两种主义,一进取,一保守。有人认为“两者并起而相冲突”,但梁却主张“两者并存而相调和”。这是新与旧的调和,中西文化的调和,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在此,他特别推崇欧西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善调和者”。人之行走,设若去掉保守之一足,又何以进取。最后,梁启超的结论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心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比较梁任公与《新青年》,无疑,《新青年》奉持的是文化一元主义,正如梁任公则可以归属文化多元主义。走向现代和回归传统在梁那里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彼此调和。调和本身就是传统儒家的智慧,在不同对象之间“执两用中”而非非此即彼。梁任公儒生出身,且一生儒生本色,但他的西学知识,又远在同辈之上。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的20世纪初,任公以其韩潮苏海般的言论,中西兼顾,纵横捭阖,以《新民丛刊》为标志,树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梁任公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健康的时代,它为20世纪的文化局面开了一个很端正的头。然而,十多年之后,《新青年》其兴也勃,它以激进主义的言论取代了梁任公,亦成功地构建了它自己的时代。看起来,两个十年交替,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后来者未必居上。20世纪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以今回观,如果出于自由主义的角度,以梁任公的文化大度,对比《新青年》的文化偏狭,委实不难看出,《新青年》其实是梁任公的倒退。这种倒退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逶迤于今。别的不说,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居然还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便是证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