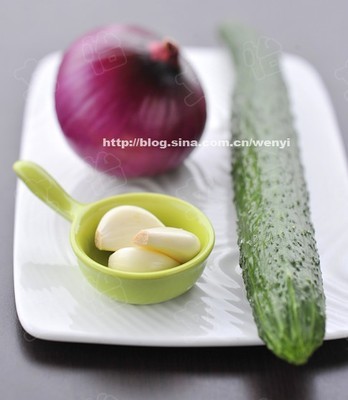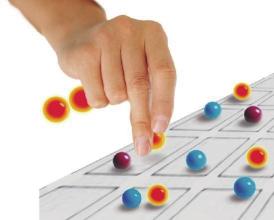改革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 1981年我毕业时,马洪老师安排我去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中心由马老师负责筹建,当时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工经所,然后就去了河南。 我去河南工作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河南省委从北京请了一个经济改革研究演讲团去河南演讲,这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人临时组织的团由王岐山带队。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杰听了大家的演说以后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讲得好,但你们不要光讲,能不能来几个人带我们做吧。”于是,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我和朱嘉明去河南。那时河南的经贸委、外贸厅、中行和贸促会这几个与外贸相关的机构经合并后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让我去当主任。当时王岐山比较有经验,他说:“江南,你去那边还是做副主任吧。”这样,我就到河南干起了外贸,当了副主任。朱嘉明则去了省体改委,做了一个兼职的副主任。 那时中国的外贸也是计划经济,出口所得的外汇全都由外汇管理局收走了。当时外贸出口是亏损的,怎么办呢?国家补贴。国家计委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外汇补贴的计划,比方说,给经贸部下达的创汇指标是100亿美元,然后就会提供200亿人民币的外汇补贴。经贸部再把这部分补贴下发到各个省、各个公司。我去河南的第一个春季就碰上了广交会,我担任河南代表团的团长,带队前往广州。那一年广交会出口形势很好,才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外贸出口计划的一大半,但却将计划中的全年外贸补贴花光了。这样,外贸公司不敢再和国外公司签约了,因为一签就超额亏损。那一年的总团长是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把我找去,说:“外贸补贴用完了,可是广交会才开了一半,怎么完成全年指标呢? 在那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其中有安排外贸计划。会议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参加的都是各部委领导,而我只是局级干部,也被莫名其妙地通知来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是姚依林点的名。会议最后的计划安排产生了矛盾,国家计委安排的外汇创汇指标说不能减少,否则必保的进口就会出大问题。外经贸部说无法完成,除非国家能多给点外汇补贴。财政则回应说,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要追加补贴,财政拿不出来。就这样吵得一塌糊涂。最后,我壮着胆子站起来说:我想谈点意见,行吗?姚依林说:“你说吧,叫你来就是让你发表意见的。”我说:现在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外汇却又没有补贴,如果我们将汇率贬一下值,出口收汇就会兑换更多的人民币,出口就不会亏损了,不就不再需要由国家拿出专门的外汇补贴了吗? 可能我提出的办法大家都没有准备,所以,也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讨论下去。散会后,王品清找到我,征询我的意见。我还是提议调整汇率,但他不同意,因为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事关重大,不能调。我说那就一个办法了:超计划外汇自留,由市场自由调节。什么意思呢?当时,特别是深圳那边,已经有了外汇黑市,官方汇率大概是5块多,黑市上炒到了将近11元。如果允许超额完成计划的外汇进入黑市自由买卖,挣来的钱弥补亏空,完全可以调动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当时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因为外汇禁止自由买卖,所以,我干脆进一步提出将深圳的外汇黑市合法化,让它流通起来。 王品清有些为难,说:“这能行吗?”我说,行不行先给总理打个报告吧,这是唯一的办法。王品清马上给外经贸部做了电话报告,部里当天就报告国务院。第二天一大早,赵紫阳总理就回了电话表示同意,并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研究并通过了这个方案。 王品清向广交会各个交易团传达了国务院的意思,让大家赶紧与外商签约。但有的省不敢签,怕万一政策不能兑现,产生巨大亏空怎么办。我们团的人就问我:“黄主任,别的省不敢签,咱敢签吗?”我当时就表态,敢说更要敢做,敢比划更要敢出招。所以,我们河南代表团就抢先签了一圈。要知道,先签的价格低,划算啊!别人一看坐不住了,也都跟着签。结果,那一年河南外贸做得很好,一下子赚了好几千万。 当年,姚依林副总理找到我,让我找几个人起草一个外贸改革的方案。我开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然后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让名单中的人调到河南去,我们围绕着汇率、汇率调整、外贸企业经营权开放,起草了第一版《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时其实很不经意的就完成了。 宝钢的故事更偶然一些 宝钢建设初期,全国一片声讨,人大代表严厉质疑冶金部长。有人计算宝钢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被称为“败家子工程”。在各种压力下,国务院集中几百个专家、学者在上海宝刚开了一个论证会。论证会提出了几种方案,全都建议宝刚下马,即“壮士断臂”、“五马分尸”,宝钢能停的停,能退设备订货合同的退,不能退的进口设备转到其他钢厂。马洪老师是会议召集人,带着我和朱嘉明一起去参加这个论证会。与其他人的意见不同,我和朱嘉明坚决反对宝刚下马。 我们主要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认为,专家们对宝钢上下马的计算思路有问题。如果当时是论证宝钢项目是否立项,他们的计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当时宝钢大多数投资已经执行。“壮士断腕”意味着抛弃宝钢最宝贵的整体综合世界最先进钢铁基地的优越性,且下马还要花费大量的退货理赔,施工队伍转场,项目移地再建等费用。如果以前的投入认赔,把宝钢的收益与今后的继续投入加“五马分尸”可收回的收益之间比较的话,收益率怎么计算都不低。关键的思路差别在于我们论证的基础不是零,而是眼前的现实。因而我们指出,如果从前决策宝刚上马是“傻子”(当时质疑宝钢项目者语),那么,现在决策宝钢下马就是“疯子”。

第二,我们认为,专家计算的宝钢产值不正确。专家们计算的宝钢产值是按照国内钢材调拨价格来计算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宝钢得200年才能收回投资。可是,宝钢生产的钢材不是普通钢材,而是进口钢材的替代品。以进口价计算的话,项目回报率就不差。我们仔细整理了一下,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表交给马洪老师。但在全国专家都要求宝钢下马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回京后的第一天,我去王岐山家,坐在他住的西屋聊天,正好姚依林副总理吃完饭遛弯儿进来。他主动跟我们聊起了宝钢,说宝钢下马的论证报告已经送到中央。借着这个机会,我大着胆子提出我们有不同看法,然后就阐述了我们的意见,并很意气用事地说,如果以前的代价不计,我就承接宝钢,保证盈利。姚依林听了很感兴趣,让我们赶紧再交一个报告给他。 报告送上去后,过了几天,国务院又通知马洪老师去宝钢组织二次论证。这回的结果大翻盘,宝钢项目继续建设。历史就是这么巧,如果我们没有随队参加宝钢论证,如果我们没有突发奇想换个思路想问题,如果那天我们没有去找岐山聊天,如果姚依林没有散步到他屋里,如果我没有胆量向他阐明我们的意见??,也许现在的宝钢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宝钢的事情,看起来更偶然一些。 数量分析后的结论 80年代,我和朱嘉明是做过一个有关经济预测的模型。这个课题的起因,是赵紫阳总理想知道2000年的“中国图像”,以便知道我们现在该干什么,说到底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远预测性描述。任务交到计委,计委只做5年的短期规划,那时离2000年还有20年呢,2000年的“中国图像”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一些大专院校也不愿意接这个棘手的课题。 当时,我和朱嘉明已经开始在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工作了,马洪找到我们,当时我们既不知道图像应包括哪些内容,又不知道研究的方法,但还是大着胆子接下了这个任务。 接了课题之后,我们先商量写什么内容。我们的资料里有很多国民经济统计手册,钢材产量、木材产量、每万人医生数量等,一共有好几百项。我说咱们就依葫芦画瓢吧,算出这些统计项目到2000年能达到的水平,不就成了经济的全景图像吗?于是,我们重新编了一个大目录,农业、林业、轻工业、重工业等,包括每万人拥有的教师数量,每万人的大学生数量、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先把这个目录列出来,这样我们就知道该研究什么。 怎么推算2000年的数据呢?想了半天,我们决定用线性外推法来计算。但这样的计算比较复杂,靠手工计算的话,要很长时间才能算好一个数据。正好那之前我曾被派到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学习过三个月,回国的时候,我在日本买了一个带模型的计算器。这种计算器带有公式,将数据输入,外推20年,结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们让秘书先将目录整理好,然后安排好数据,一个一个地推断2000年的情况,算完之后再加以分析综合。 这一分析,我们发现了几个大问题:到2000年我国的粮食完全不够吃,即便从国外进口,我国港口和铁路运力也不能把粮食送到人民手中。由此看来国家到2000年肯定要崩溃,怎么办?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国家按照以往的方式线性发展是无法持续的,只有通过改革,走一条非线性发展的道路,中国才有生存的出路,这样改革的必要性和唯一性便不言而喻了。但当时作为预防危机的手段,国家还是立即加大了散装码头和铁路的建设。而后的农村改革解决了人民吃粮的问题,散装码头成为我国煤炭出口的有力支持。 很多事物,如果经过数量上的统计分析,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那时经常讲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在计算过程中却发现,其实我们国家是一个资源极其短缺的国家。地大,但可耕的面积很少;物博,但可利用的效率极低。这些“地”和“物”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几乎成了全世界最低水平。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天天给各方面敲警钟,后来还写成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在客观资源条件下的中国战略发展模式,这篇文章后来被国内外80余家媒体转载。 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中国分三个阶段发展的战略设想。 首先是资源出口阶段,向国外出口农副产品、矿石、石油等原材料,进口技术装备,发展现代工业。发表这篇文章时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其次是资源转换阶段,中国自然资源匮乏,最丰富的是人力资源。但劳动力是很难出口的,那么我们用进口来弥补我国资源的不足,再将我们的劳动力附加在资源上形成产品出口,最后换回新的资源,是中国从资源出口国变为资源进口国,从产品进口转变为产品出口。我们提出的这个发展模式,后来被人简化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并广泛应用。 第三阶段,等到中国的整体科学技术再上升一个层次,我们就不再是简单地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是运用高技术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进入技术及技术产品出口阶段。中国现在已开始步入这个阶段。 最后,对于经济改革,我再说几句。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三点:一是坚持搁置争议,坚持尝试新鲜事物;二是坚持对外开放;三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