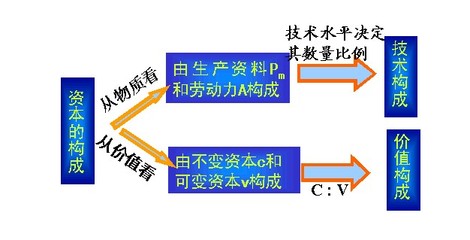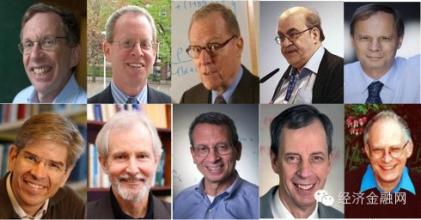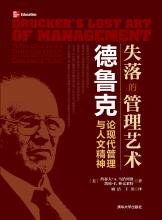作者:蔡鸿生
清初的岭南佛门是不平静的。自1644年甲申之变(顺治元年)至1680年平藩覆灭(康熙十九年),在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与复国、统一与割据的斗争持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禅林也风云密布。一方面,它成为遗民逃禅的政治避难所;另一方面,又被清朝新贵用作收拾民心的人间道场。在严峻的历史环境中,空门已经不是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是非中”的空白地带了。
清初的岭南佛门也不是清一色的。高僧与俗僧各行其道,前者“以忠孝作佛事”,融气节与禅风为一体;后者则出家谋利,与佛门清规背道而驰:“盖自正法陵夷,宗风不古,名虽出家,实为名利,徒登戒品,殊昧清规。所谓出家者,不过工文词,习梵呗,营屋宇,美衣食,置田宅,畜徒众,能事毕矣。如来门下,何乐有此![1]表面上都是暮鼓晨钟,实则清浊殊途,大异其趣。
明清之际社会变革对岭南佛门的冲击,其强度并不亚于滇南和江南。平南王尚可喜入粤,杀气腾腾,既带来社会生活的大劫,又给禅林梵宇蒙上一层“护法”的阴影。在腥风血雨过后,平藩竟然出来佞佛,这就只能是伪善,难免造孽扰民,弄得“十郡冤魂结宝幢”了。
让我们从这名南粤屠夫的“屠城”说起。
一 广州庚寅之劫
庚寅年,即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按民间的生肖纪年法,寅属虎,广州又名羊城,于是,“虎食羊”的惨剧便被用来隐喻清兵血洗广州的暴行了。
是年初春,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从江西经粤北南下,绕过肇庆和三水的明军,直下广州,驻营城北。南明的两广总制杜允和固守城内。经过八个多月的围攻,到十一月初二(阳历11月24日)城破[2]。杜允和率残部逃奔琼州,清兵屠城七日,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事变。
当年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一1661),撰《鞑靼战纪》(1654年出版)一书,其中写道:
大屠杀从11月24曰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3]
清初来华的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也在《从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1669年出版)一书,写下大体相同的报道: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4]
广州的庚寅之劫,在清初的诗文中,有更惊心动魄的描写。这些具有文献价值的篇什既是历史实录,又是社会舆论。听一听同时代人的控诉,平南王的真面目就无所遁形了。
屠城之后,尸骨狼藉,遍于街衢。有一位名为“真修”的和尚,“募役购薪,聚[]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番禺儒生王鸣雷,满怀悲愤,撰写了一篇祭文,内云: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骷髅,或如宝塔,或发山邱。便门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赢老就戮,少者发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岂无同姓,鬼食嫌疑。生妻在傍,冥漠未知。儿尚襁褓,母已生离。骨无人收,儿在背饥。亦有弱妇,仓卒入房,暮昏晨别,未拜姑嫜。断肌委尘,粉骨埋香。生不相见,良友巾帼。如何墓门,不远咫尺。嗟呼悲哉!浩浩黄云,潇潇暮雨,谁敛魂魄,而聚比户。野狐邻穴,野葵塞路,峥嵘荒馗,白杨衰草。大小号呼,同归乡土。回首西天,勿生劫道。[5]
这篇凄厉的祭文,犹如一份罪行录,将清兵屠戮之惨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著名岭南诗人梁佩兰(1630一1705),写过一首《养马行》,序云:“庚寅冬,耿、尚两王入粤,广州城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梁子见而哀焉,作《养马行》”。全诗如下:
贤王爱马如爱人,人与马并分王仁。王乐养马忘苦辛,供给王马王之民。马日龁水草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龁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瘠王怒王扑人。东山教场地广阔,筑厩养马几千群。北城马厩先鬼坟,马厩养马王官军。城南马厩近大海,马爱饮水海水清。西关马厩在城下,城下放马马散行。城下空地多草生,马头食草马尾横。王谕:“养马要得马性情,马来自边塞马不轻。人有齿马,服以上刑!”白马王络以珠勒,黑马王各以紫缨,紫骝马以桃花名,斑马缀玉缫,红马缀金铃。王日数马,点养马丁。一马不见,王心不宁。百姓乞为王马,王不应。[6]
当年的广州,从城北到城南,从东山到西关,墓庐变成了马厩。耿、尚二王的马政,荼毒生灵,是在屠城之后又添加的一项虐政。
清初游粤的江西诗人曾灿,是一名改僧服的明遗民,曾写过《羊城歌》,对圈地、输纳和劳役如何扰民,点滴无漏地记述下来:
羊城楼上鼓声急,羊城楼下兵马入。
西风刁斗彻夜惊,满城儿女皆垂泣。
一望烟尘昼不开,火光风势如崩雷。
马上折棰跨宝刀,一骑驱卤百人来。
白梧黑索满阡陌,男在东头女在北。
但闻男儿号哭声,不见妇人憔悴色。
可怜妻子属他人,更苦无钱赎一身。
田园圈去作王庄,华屋一朝成灰尘。
艰难留得余生在,甔石已空赋不改。
正供钱谷万难输,官吏私派百十倍。
征符忽下王师徂,老幼壮丁为役夫。
鞭挞骨肉血满野,楼舡高会吹笙竽。
吁嗟羊城亿万户,半销锋镝牛征赋。
白日阴风天欲寒,萧条闾巷无归路。[7]
顺治十七年(1660)耿继茂奉命移镇福建,广东便成为平藩的独立王国了。计自攻陷广州之后至康熙十九年(1680),尚可喜及其子之信、之孝坐镇广东三十年,集兵、政、财权于一府,平南王成了“南霸天”,号称“三藩”之一。两广总督吴兴祚于撤藩后上奏,历数平藩治粤的种种弊政:
粤民受逆藩数十年之害,利在锱铢,如盐埠一项,额课一十四万有奇,此盖千百商民凑合资本行运,逆藩以盐为利薮,强占盐田场埠,盐课无出,商民并累,此粤民受困之一端也;广属渡税三百八十余处,逆藩兵卒罗踞津口,重加税钱,又不许增船分载,往往人多载重,渡民被溺,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粤货至境,旧有落地税名目,逆藩创立税总店,铜、锡、铁、木之属已纳税者,重加税敛,下至鸡、豚、蔬、果,一概截收,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渔课旧额,通商五千四百余两,藩役委官重敛,苛征税银巨万,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至市舶一项,原与民无害,好徒沈上达乘海禁之日,番舶不至,勾结亡命,私造大船,出洋为市。”[8]
如此多端害民的平南王,令人深恶痛绝。据《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三载,新会有个打锡匠,闻雷震辄叹息曰:“雷霆何不向广州击平南王,而坐此轰轰耶!”就是这个备受口诛笔伐的尚可喜,竞然也曾多次敬佛:问道、铸像、修寺,等等,岂不是人世间的咄咄怪事。这段藩、佛之间的微妙因缘,前人似乎少加注意。其实,如果着眼于清初岭南的政教关系,对有关史实是不能不加以探索的。
二 尚可喜佞佛
尚可喜,辽东人。出身行伍,原为明将,驻守广鹿岛。天聪七年(1634)降清,授总兵。从入关到南下,屡建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9年),封平南王。次年攻陷广州,在南明故土建立起血腥统治。他给南粤民间留下的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
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面貌狰狞,两颧高耸,环目短髯,黄带蓝袍,纬帽不戴顶(时尚未设顶),鹰嘴靴,叉手而坐,犹觉其杀气勃勃也。[9]
“杀气”与“护法”形同水火,本来互不相侔。但在尚可喜身上,却表现为矛盾性的结合,这就耐人寻味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10]下面所列举的,就是平藩与佛门关系的若干史实。
清兵围攻广州吋,驻营于小北门外。顺治九年(1652),即陷城后两年,尚、耿二王便在原驻营地大兴土木,修造用以纪功的“得胜庙”,平南王建于左,靖南王建于右,奉祀“汉寿亭侯”,即被满洲人尊为战神的“关公”。[11]同年,平南王又于得胜庙后,另建太平庵,内塑佛像,并铸铁钟一口。钟重约1000斤,通高1.24米,1982年在该庵遗址发现后,移置广州博物馆。钟铭全文如下:
今上龙飞之七年,平南王奉命恢粤,二月初六师抵五羊城北白云山,结营山阿,凡九阅月。将士奋腾,兵马无恙。其间铸炮制药,随手而应,阴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赀建造太平庵,内塑佛像。爰勒之钟鼎,以志佛力于不朽,仍镌以铭。铭曰:鸣錞肃旅,以事南征。缘岩列帐,依[]分营。百举汇应,乃克坚城。爰溯佛力铸钟铭,用以永播其芳声!
顺治壬辰岁三月吉日,平南王建。广州府督捕通判周宪章监造。[12]
这则钟铭虽只有一百六十多字,却无异是一篇平南王与佛结盟的政治宣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尚可喜心目中,佛陀属于他的阵营,“兵马”体现“佛力”,从而赋予“南征”以无比庄严的性质。难怪战火一熄灭,他就燃起佞佛的香火了。
平南王对“佛力”的感恩,从城北的太平庵开始,逐步普及各地。顺治九年一年之内,他还捐铸一躯鎏金释迦如来铜佛,安放于番禺雷峰海云寺(原名“隆兴寺”)内,款识为“大檀越喜铸”。[13]
顺治十二年(1655)春,平、靖两藩请空隐和尚到广州河南名刹海幢寺说法。[14]空隐名道独,字宗宝,姓陆,南海人。长期主持罗浮山华首台法席,顺治十八年(1661)逝寂。他有两大弟子:天然和尚(函昰)和剩人和尚(函可)。钱牧斋撰《华首空隐和尚塔铭》,备极赞叹:“随身两膝无剩余,龙象踏蹴看二驹。[15]
清初岭南佛教的另一中心,是以戒律闻名的鼎湖山庆云寺。它也是两藩笼络的对象。顺治十七年(1660)撰立的《鼎湖山栖壑禅师塔铭》写道:
顷平、靖两藩,慕师高风,延至府衙问道。靖藩太妃,禀受皈戒,衬以名香、紫衣。时内翰铁山伍公,尝偕诸绅士敦迎法施。师唯一音演唱,庶类欣心。[16]
栖壑禅师名道丘,字离际,顺德柯氏子,曾充憨山大师侍者,是洞山宗石头下三十五代法嗣。他主持的庆云寺,“法堂常绕半千僧”,在僧俗中甚有威望,两藩慕风问道,无非是一种政治手腕罢了。
上行下效,顺治十五年(1658),靖藩总兵宫曾养性捐资修复西郊龟岗下的禅寺,名“西禅寺”。同年,平藩的部将文天寿,也捐资修寺,在广州东门外教场的观音堂原址上建东林寺。[17]东教场是前明的演武场,原置护国禅寺。文天寿步平藩的后尘修寺,合护法与护国于一举,媚上惑众,决不是无所为而发的布施。
康熙三年(1664),平南王为“祝禧佑国”,在广州城南明代龙藏寺故址修建大佛寺。据《南海百咏续编》云:
康熙三年,南疆奠谧,平南王自捐王俸营造兹宇。上为天子祝禧,制式悉仿京师官庙,世尊慈范亦摹之北匠云。
这座以“京师官庙”为样板修建的佛寺,形制十分庄严宏壮。乾隆四年(1739)广州知府刘庶撰《重修碑记》云:
其为制也:门以内有钟鼓楼,当前为天王殿,又进则为大殿峙其中。佛像尊严,金身雄伟逾丈,此则“大佛”之所由名也。[18]
该寺的金身大佛,共三尊,现已移置六榕寺。其质料、形体、重量和铸造工艺,《广州市文物志》记载如下:佛像“以黄铜精铸。三尊佛像皆盘膝坐,每尊高6米,重约10吨。手势各不相同,正中的为释迦牟尼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膝盖中间,右手掌心向上,放在右脚膝盖上,作说法的手印,代表现在。左边为阿弥陀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在盘膝中间,右手掌心向上放在右脚膝盖上作垂手接引印,代表过去。右边为弥勒佛,左、右两手掌心重叠平放在盘膝的中间是禅定印,代表未来。佛像仪态慈祥,铸造精美。各像均分为头盖、面部至肩、上身至腰、下身至盘膝坐和莲花座5段铸造,然后捍接而成。每段衔接准确,接缝小,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黄铜铸像。”大佛寺及三世佛铜像的营造,既是平南王“上为天子祝禧”的表忠壮举,也是他在清初岭南劳民伤财的物证。
康熙四年(1665),尚可喜的第十三女自愿落发焚修,使他又有机会来扮演慈父兼檀越双重角色。据《番禺续志》卷四十一云:
檀度庵在清泉街,康熙四年平南王尚可喜建。王有子二十三人,女十七人。其第十三女生即茹素礼佛,睹诸兄之横恣,忧患成疾,力恳为尼。王乃选宫婢十人为待者,建此庵为其静室。法名“自悟”,人称为“王姑姑”。
“王姑姑”从平藩府中异化出来,变成一名遗民式的尼姑,对岭南佛门有何意义,留待第六章去分析,此处暂略。
康熙十一年(1672),尚可喜及福晋舒氏,对岭南名刹海幢寺,作了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布施:
傍珠江南岸为海幢寺,故郭家园也。建寺始于僧月池,得平藩之增饰而益华矣,鹰爪兰乃郭园旧植,地改而兰茂,以亭盖之。平藩佞佛,龟峰、大佛、海云之兴造,其费不赀。[19]
寺内所有之绿色砖瓦,均舒福晋所布施。初,两藩营造府第,咨请部示,恳照王贝勒制式,得用琉璃砖瓦,以及台门鹿顶。嗣奉部驳:“民爵与宗藩制异,察平、靖两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请用绿色砖瓦之处,碍难准行。”时粤东启窑,砖瓦皆成,而未敢擅用,乃尽施诸佛寺,若越秀山之观音寺、武帝庙及大佛寺,皆此种砖瓦也。[20]
如上所述,平南王尚可喜入粤以后,礼僧问道,修寺铸佛,一次又一次地摆出“大擅越”的姿态,处心积虑嫁接衙门与佛门之间的因缘。这种“平藩佞佛”的历史现象,应该作何解释呢?
按满洲旧俗,佞佛乃其传统。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中每日的朝祭神有三:如来、观音、关帝。每年四月初八有浴佛之祭,响殿内祝辞如下:“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诞辰,偕我诸王,敬献于神。祈鉴敬献之心,俾我小子丰于首而仔于肩。”[21]尚可喜作为藩王,在信仰上与清室保持一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平南王入粤大肆护法布施,也自有其将武功托庇于佛力的动机。如前所引,平南王铁钟的铭文,念念不忘他的“南征”和“克坚城”,“阴有神助”,因此,才会“爰溯佛力铸钟铭,用以永播其芳声!”修大佛寺的宗旨,也同样是为了“祝禧护国”。可见平南王的佞佛,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并非普普通通的迷信。
此外,清初的岭南佛门,是遗民逃禅的渊薮。所谓“胜朝遣老半为僧”,乃是当年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作为新朝的一名显贵,平南王给自己蒙上“大檀越”的面纱,一再礼请高僧空隐和尚和栖壑禅师问道,多次捐资兴修庵寺,岂不是通过对佛、法、僧的皈依,表明自己放下屠刀,以此来粉饰太平,收拾民心么?至于岭南佛门作出什么反应,那可就因人而异,各有各的取向了。
三 岭南佛门的反应
如前所述,岭南是中国佛教的滨海法窟,历代高僧辈出。在明清之际,遗民僧构成高僧群的主体,他们对平南王佞佛的反应,有的持疏远态度,有的则加以逢迎,于贬抑谀扬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平藩镇粤时期的著名和尚澹归禅师,姓金,名堡,字道隐,浙江仁和人。他以遗民入道,诗文出众,名重一时。钱牧斋《寄怀岭外四君诗》之一《金道隐使君》,有句云:“毕落禅枝除鸽怖,多罗佛钵护龙蟠”,[22]从气节方面给予表彰。不幸的是,澹归和尚人在佛门而俗缘缠身,并非完全甘于寂寞,是个复杂的人物。清初史家兼爱国诗人全祖望,写过一首《肇庆访故宫》,对澹归与平南王的微妙关系,作了如下的讥讽:
辛苦何来笑澹翁,《遍行堂集》玷宗风;
丹霞精舍成年谱,又在平南珠履中。[23]
诗中所谓“成年谱”,指的是《元功垂范》一书。该书据平南王“家乘所录”,记述尚可喜自天启四年(1624)至康熙十二年(1673)的事迹,是一部年谱体的传记,也是一本“垂示子孙”的功劳薄。全书由澹归笔削定稿,托为“尹源进撰次”。
至于“玷宗风”,则是对澹归诗文集思想倾向的批评。传世《遍行堂集》四十九卷、续集十六卷。陈垣先生指出:“今所传遍行堂续集二,有某太守,某总戎,某中丞寿序十余篇,卷十一有上某将军,某抚军,某方伯,某臬司尺牍数十篇,睹其标题,已令人呕哕。”[24]尽管其中有应酬文章,仍难辞媚俗之嫌。尤有甚者,尚可喜死于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澹归闻讯发函吊唁,见《续集》卷十一的《上尚将军书》,内云:“惊闻先王遽捐宾客,虽乘彼白云,自返圆生树下,而眷兹黔首,共沈浊漉泥中。况今释(澹归法名)空门三世,结宇长城;倦翮半枝,移阴广厦者也。所恨卧病荒丘,不获泛舟珠水,虔修薄供,洁上办香。”这样动情的话,完全不是悼念的套语,而是晚节委蛇的自供。正如吴天任先生所说:“观长城、广厦云云,疑所倚于尚王者,或非泛泛。以故国遗老,方外缁流,而倚新朝王公以为重,极意颂扬,致为后世口实,终未免有玷清誉耳!”[25]
澹归得法于天然和尚,即被誉为空隐“二驹”之一的函昰。这位古道自持的岭南高僧,“于门庭设施,悉任外缘,意合则住,不合则行,未尝一言一语仰干豪贵”(今辩撰《行状》)。顺治九年,尚可喜捐铸铜佛,并没有博得什么赞誉,只得到一个居高临下的款识:“博山下二世雷峰隆兴寺本师天然昰和尚率大檀越喜铸”。[26]“率”字下得极有分量,类乎画龙点睛,可见这个老衲的高风亮节。作为澹归和尚的本师,天然在知人论世方面确实比自己的法嗣更有本事。据《胜朝粤东遗民录》记载:
平南王尚可喜慕其高风,以函昰开法雷峰之海云寺,因捐金铸铜佛高丈余置寺中,复广置寺产,俾成海邦上刹。尝以礼延至郡,一宿即告归。或问之,函昰曰:“平王具佛性而无定力,萧墙之祸近在目前,遑计其他耶?”后卒如其言。[27]

函昰对尚可喜所作的这个考语,既是鉴定,又是预言。从口气看,“具佛性”是虚,泛指他佞佛的种种举措;“无定力”则是实,揭示了平南王气质上的根本弱点。佛门提倡的戒、定、慧“三学”,是通向涅盘的必由之路。正如释道安所说:“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位居中间的“定”起关键作用,缺了这个“三摩帝”(“禅定”的音译),戒就不能落实,慧也无从生发。“无定力”意味着神散意乱,缺乏坚定性和专一性;“无定力”也意味着与正定静虑的背离,无法断除孽障,必将自食苦果。难怪天然和尚在平南王炙手可热之际,就觉察到他的要害是毫无“绝分散之利器”,决没有好下场了。
康熙十九年(1680),尚之信于“撤藩”后被清廷赐死,平南王父子两代霸业一去不复返了。广州大通寺主持成鹫法师曾赋《仙城寒食歌四章》,其中那首《尚公坟》,为平藩治粤及其“萧墙之祸”作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海珠海水流腥血,十万生灵冤莫雪。
杜康有力不借人,入室操戈凭曲蘖。
郎君本是拔山雄,一饮千钟双耳赤。
座上杀人如草菅,府中聚骨成丘垤。
承恩赐射中金钱,至尊含笑称“俺达”。
归来虎视故眈眈,神器妄窥狂力竭。
黄带长悬鞅望心,赭衣遽与繁华别。
烟销火灭脊原空,白骨衔冤死同穴。
孤坟快与梵宫邻,疏钟敲落城头月。
夜台沈醉酒初醒,猛然悟得无生诀。
起来若遇绵上人,从头汗马休重说。[28]
“孤坟”与“梵宫”相映成趣,是历史对平藩佞佛的无情讽刺。末代平南王“赭衣遽与繁华别”的最后一幕,留给后人的是如下的记录:
庚申(1680)八月十七日,赐死于府学名宦祠,焚尸扬灰。沈上达(平藩参将)家人钟姓者,收其骸骼余烬,瘗之西园报资寺。[29]
尚之孝兄弟赐死后,沈上达家人钟姓收其余烬,藁葬于会城外报资寺中,至今犹存。一题“平南王墓”,一题“唵哒公墓”。当撤藩时,其家不能携其余烬归辽东,而藁葬于粤,此惨刻之报也。今寺僧于清明日恒祭之。[30]
报资寺位于广州西园,东侧为芦荻巷,清初是一处荒僻之地。尚可喜父子埋骨于此,寂寞身后事,几乎被人忘却了。诚如上诗所言,寒食野僧祭孤坟,是既惨淡又悲凉的。岭南佛门对平藩佞佛的反应,经过三十年的沧桑变幻,其终极情景竟然如此凄厉,真是出人意外而又发人深思了。
[注释]
[1]成鹫:《出家二十颂后跋》,见《咸陟堂文集》,卷二。
[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
[3]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1版,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司徒琳着、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版,海古籍出版社,1992。
[5]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
[6]梁佩兰:《六莹堂集》,卷三,1版,26—2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7]曾灿:《六松堂诗集》,卷三,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册,1版,216一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清史列传》,卷九。
[9]《广州城坊志》卷二,引《粤小记》。
[10]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全明馆丛稿二编》,1版,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仇巨川:《羊城古钞》,1版,160、27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2]《广州市文物志》,1版,277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13]《番禺续志》卷三十六。
[14]黄佛颐:《广州城坊志》,l版,69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5]《牧斋有学集》,下卷,1版,1271一1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6]刘伟铿校注:《肇庆星湖石刻全录》,1版,28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7]《羊城古钞》,第276页。
[18]《广州城坊志》,第253页。
[19]檀萃:《楚庭稗珠录》,卷二。
[20]《南海百咏续编》。
[21]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下册,1版,314—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牧斋有学集》,卷四,165页。
[23]全祖望:《鲒崎亭诗集》,卷十。
[24]陈垣:《清初僧诤记》,1版,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香港版线装本,93页。
[26]注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谱》,初版,3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7]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
[28]成鹫:《咸陟堂诗集》,卷四。
[29]钮琇:《觚剩》,卷七。
[30]黄瑞谷:《粤小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