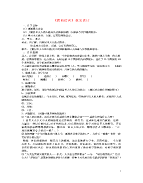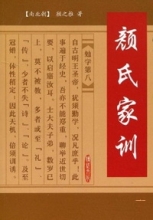一 颜之推生平简介
关于颜之推生平,缪钺先生著有《颜之推年谱》,逐年介绍,颇为详备。但因拙文所论与颜氏生平密不可分,不能不在此作简单介绍。此节除了笔者的评论之外,基本上根据《年谱》简约写出,读者可取《年谱》对照阅读。以下若无引号,则不一一注明出处。
《颜氏家训 . 诫兵》称:“颜氏之先,本乎邹鲁。”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五“诫兵”,《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8页)是邹鲁乃颜之推第一祖籍。颜之推为其长子命名“思鲁”,表明他对第一祖籍之重视。但其祖籍在邹鲁何地,未可详知。所幸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提到,西汉大儒颜安乐为其先祖之一。据《汉书》记载,“安乐,鲁国薛郡人。” (《汉书 》卷八八《儒林 . 颜安乐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17页)薛郡治鲁县,即今山东曲阜。则其第一祖籍在曲阜一带,与孔子实为同乡。《颜氏家庙碑》曰,曹魏时,颜盛(生卒年不详)为“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 (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金石萃编》卷一0一,《石刻史料丛书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第24页B面)《北齐书·颜之推传》记载:“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 (卷四五《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17页)说明在南朝和北齐的户籍上所记颜家地望是临沂。临沂即今山东临沂市北,为古齐地,则临沂是颜之推第二祖籍。颜家以此为著籍地望,则其第二祖籍也一样重要。
四世纪初,中国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因外族人起兵而造成的亡国,颜家自不能幸免。由于五胡起兵,西晋被推翻,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流亡江南,颜家也随着潮流迁移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并在此居住达八代人之久。建康实是颜之推第三祖籍。颜之推父亲颜协(487-539)在梁武帝(502-549)统治时期,在湘东王荆州刺史(治江陵,今湖北襄阳)萧绎(508-555)幕府作事。因此,颜之推于中大通三年(531)生在江陵。其后,他一直居住在江陵,直到被俘北迁。所以,在生活习惯上,他该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而且深染荆楚文化。他为次子命名“愍楚”,表明他对荆楚地区怀有深厚的故乡情。
颜之推父亲在他七岁时去世,他由长兄之仪(生卒年不详)抚养成人。十二岁入梁王子萧绎的卫西将军府(江州,江西九江)中听授《老子》和《庄子》,但因为不好虚玄之学,回家后即放弃老庄,转而研习儒经。十九岁时(547),颜之推进入作场,为湘东王萧绎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驻江陵。550年,萧绎世子萧方诸(生卒年不详)为郢州(治江夏,湖北武昌)刺使时,任命颜之推为萧方诸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随同到了江夏。(《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7页)
又是颜之推的不幸,他遇到了五胡之乱后再一次胡人起兵——侯景之乱。551年,侯景(? -552年)将宋子仙(生卒年不详)和任约(生卒年不详)袭击郢州,颜之推被俘虏。其间,几次都险些被杀害,仰仗侯景属下王責 (生卒年不详)帮助,幸免于难。不久,他被押往建康,滞留到侯景之乱被平息(552年),才回到江陵。此时萧绎已经称帝,任命颜之推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奏命校书。
这段校书经历时间不长,大约持续了两年。554年西魏(535-556)攻陷江陵,颜之推再次被胡人俘虏,并迁移长安。当年,他才二十四岁。此次北迁,满眼所见曾经是南迁中原士族魂牵梦绕的华夏神州已经变为胡风蔓延的“龙荒”,北方士大夫的后人颜之推根本无法接受。 他在长安羁留时期,无时无刻不思念江南。556年,北齐(550-577)将梁朝宗室贞阳侯萧渊明(?-555)送回南方,恢复梁朝。“凡厥梁臣,皆以礼送。”(《观我生赋》自注,《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23页)颜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同上)当时,一位叫李显卿(生卒年不详)的西魏将军很器重他,其弟李远(生卒年不详)军府在弘农(今陕西灵宝),推荐颜之推作弟弟李远幕府做事。颜之推趁此赴职的机会,逃到北齐。出逃之日,“值河水暴涨,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7页) “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同上,第623页) “时人称其勇决。” (同上,第617页)
颜之推到达北齐之后,受到齐文宣帝(551-558在位)的热情相迎。“显祖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同上)可是他回南的计划却终于落空,因为次年陈霸先(503-559)取梁而代之,建立陈朝(557-589),遣送南人的行动嘎然而止。颜之推在邺城留居,直到北齐政权被北周(557-581)消灭为止。河清年间(562-564),他被任命为赵州功曹参军,后任待诏文林馆,司徒录事参军,均非高官。但他在文林馆任职期间,谈吐过人,擅长文案,深得当时名人祖珽(生卒年不详)赏识,任他作知馆事。馆中文书皆由颜之推审阅并签署。不久即迁升中书舍人,为皇帝所重用。
颜之推在北齐积极参政,受到王利器的严厉批判。王先生认为这是他言行不一的自相矛盾:
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禅代之际,先起异图”,“自取身荣,不存国计”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其甚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得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见危授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靦冒人间,不敢坠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终于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叙录》,第3页)
不但如此,王先生还将颜之推之仕齐与庾信的“建业长安两醉游”相提并论。(同上,第4页)王先生所罗列颜之推言行确实是事实,但评价却未必恰当。正如王先生所言:“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同上)在那个胡人处于长期统治的时代,作亡国奴对于汉族士大夫,殊非首次。颜之推本人也已非首次作胡人俘虏,对前途的估计自然不会如从未更事的人那么悲观。他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从西魏逃到北齐,只为心中存着回南的一线希望,说明他的士大夫气节很坚定,早就洗去了甘为亡国奴的耻辱。到了北齐,一切都不由区区一亡命之徒决定,出仕为官,实亦无可奈何。人的心理很复杂,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笔者不知世上有几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之后,还能够、还需要以卵击石?在北齐期间,颜之推在在为华夏文化张目,冒了很大的风险(详后),与其儒者气节毫不相悖,何至于让王先生不可饶恕如此?明人于慎行(1545-1607))有言:“夫河自龙门,砥柱而下,天下之水皆河也,济独以一苇之流,横贯其中,清浊可望而辨。夫济固不能不河也,然无失其清,固难矣,侍郎倘亦其指与?抑以察察之迹,而浮游世之汶汶,固将有三闾大夫之愤而莫之宣耶!” (于慎行《颜氏家训序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一《序跋》,第618页)此乃得颜之推真心之论。王先生的评价对颜之推不但太苛求,也是不辞之论。以下将要详细陈述的《观我生赋》主题立意及其作者的人格操守,也会证明此点。
和平生活持续了二十年之后,颜之推再次遭到厄运。577年,颜之推四十七岁时,北周军队攻破邺城,他又一次被俘,再次回到长安。三次被俘是他三次铭心刻骨的痛苦和耻辱。由于三次俘虏他的人,在他眼里都是野蛮的胡人,已经超出了个人和国家的范围,悲悯个人和国家命运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慨。所以,他不但加入了邺城文人在长安的悲齐合唱,和了一首《听鸣蝉篇》,更重要的是在次年写下了以哭泣华夏文化为主题的长赋——《观我生赋》。
颜之推在长安生活了近四年之后,隋朝取代北周(581)。有人猜测,他的《观我生赋》若写于581年之后,还该写第四次亡国之痛。此乃不了解其《观我生赋》立意之所在而产生的错误联想(详后)。颜之推在北周统治下的四年当中,并未得到朝廷重用,他的生活甚至很窘迫:“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伸供养。”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第204页)此乃是颜之推自己所述。到大象二年(580),也就是北周的最末一年,他才任职位极低的“御史上士”。(《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8页)因此,他不可能对北周产生国家认同感。隋文帝代周,乃胡人取代胡人,于颜之推也并无振奋作用。
又过了十年左右,颜之推于隋开皇十年(590)和仁寿元年(601)之间,走完了艰难曲折的人生路。卒年六十余。
二《观我生赋》之立意
《观我生赋》大约写于578年,是唯一载于《北齐书·颜之推传》的作品。此赋没有序,但除正文以外,还有详细的自注,讲解语句所含史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篇带自注的作品,前此有谢灵运的《山居赋》和张渊的《观象赋》。据清人卢文弨(1717-1796)说,“赋中尚有脱文”,但“别无他书补正,意犹缺然”。(《颜氏家训注列言》,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一《序跋》,第631页)全赋内容之重点是颜之推一生当中的三次重大转折,也是三次人生厄运。这种以自己的身世遭遇作题材的作品在北朝很流行,比如李谐 (395-544年)的《述身赋》、李骞 (?- 550之前)的《 释情赋》、沈炯(生卒年不详)的《归魂赋》和庾信(513-581)的《哀江南赋》,都是此类作品。由于一些共同的经历,沈炯《归魂赋》和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史实更与《观我生赋》相似。从西晋五胡乱华到北魏末年,胡人侵扰中国并统治北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何以突然出现这么多书写亡国之痛的作品,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北朝文学中的亡国悲情》中详细论述。本文主要论述在此大背景下,颜之推作品的特殊性。同是写亡国之痛,二李和沈庾之作皆主要述及国家灭亡中的个人遭遇,而颜赋则把个人遭遇与华夏文化联在一起,讲述华夏文化的厄运和一己的人生厄运。这点不同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是汉族文化人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个人命运与华夏文化之命运息息相关的情感。
我们来看颜氏如何展开此主题,并围绕此主题抒情,最后将此主题推向高潮。《观我生赋》开篇第一句就点明了主题——胡汉对立,不可调和:
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
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
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
族分“华夷”的观念在上古便存在,但在春秋时期发展得更完善,孔子(前551-前479)的思想里就很明显。(关于孔子的民族观,请参考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0页)。 “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又是两汉《公羊》一派将孔子思想发扬光大后的新理论。《春秋公羊传》称: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97页)
董仲舒(前179-前-104)进一步解释:“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春秋繁露义证》卷四《王道》六,《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6页)何休(129-182))注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97页)汉魏《公羊》学者所解乃王道由内及外的渐化趋势。先夏后夷。换言之,王道所渐,从内到外,由夏及夷,而绝非反其道而行之。故用夏变夷乃是正道,用夷变夏则是反动。可是,颜之推放眼看去,却看到华夏文化在春秋之后,一直受到胡族文化侵蚀,以至于今日,面对胡族的强势毫无自卫能力,终成亡国之局的事实,因此深感悲哀,不能不抒发心中的感慨。在接下来的赋文里,他即一一展示了春秋以来用夷变夏的逆动趋势:
大道寝而日隐,《小雅》摧以云亡,
哀赵武之作蘖,怪汉灵之不祥。
这里“赵武”指春秋时期学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 (?- 前295),“汉灵”指好胡饼的汉灵帝(166-188在位),他们开了用夷变夏的先河。颜之推认为,这便是后来胡人肆虐、华夏文化受践踏的祸源。所以接下来,他写到了西晋(265-317)末年发生的 “五胡乱华”:
旄頭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
瀍澗鞠成沙漠,神华泯為龙荒。
这几句文字有两个典故指向华夏文化的悲剧。瀍、澗本是鲁地两条河流名称,代指孔子故乡,华夏正统文化之象征,“神华”更是明确指华夏神州。“沙漠”和“龙荒”皆指胡人故土。华夏正统文化之发源地以及所有华夏神州如今都已经变成胡人的领土,是何等的悲哀!
五胡乱华是颜之推出生以前的华夏厄运,沦陷区只限北方,他虽然耳闻,却未亲历。颜之推前半生生活在江南,那是五胡乱华以后,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的地区,本来很值得庆幸。但是没有人会料到,偏安的和平局面还会被胡人侯景打破,而且是从内部起兵。侯景是因与北齐皇帝不睦而投降梁朝的胡人。到了梁朝以后依然不服管束,最终酿成了梁朝几乎灭国的惨祸,建康城里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无人逃过了那场悲剧。远在藩镇的颜之推也未能幸免。不过颜之推并没有只关注个人的遭遇,而是更多地为“侯景之乱”使华夏文化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感到悲哀:
自東晋之违难, 寓礼乐於江湘。
迄此几於三百,左袵浹於四方。
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
就狄俘於旧壤, 陷戎俗於来旋。
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
鼖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
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
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
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
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
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
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
这段文字是描述颜之推被侯景军队俘虏后,押回建康城之所见所闻。他用了一系列悲悼华夏文化的典故和语汇:“微管” 、“《黍离》”、“《麦秀》”、“昭君” 、“鼖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还有一系列指代胡人肆虐的语汇:“左衽” 、“苦胡” 、“ 就狄俘於旧壤, 陷戎俗於来旋”。该赋主题再一次展现。
侯景之乱被镇压后,梁元帝在江陵即位。但是悲痛尚未抚平,西魏的胡人军队就大举南下,踏破了江陵城。颜之推又一次看到华夏文化被破坏的惨剧:
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
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怜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狀。
夺诸怀而弃草,踣於途而受掠。
冤乘舆之残酷,軫人神之无狀。
载下車以黜丧,揜桐棺之蒿葬。
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憀悢。
井伯饮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
留钏之妻,人衔其断绝,
击磬之子,家缠其悲怆。
此段文字虽然以写魏兵陷城后的惨状,也未离开主题。“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子卿牧羊於海上”等句,依然在痛惜华夏文化之被残毁,悲悯华夏子孙被蹂躏。作者写到北迁路上所见所闻,更是表现出他对华夏文化的悲哀:
若乃五牛之旌,九龙之路,
土圭测影,璇玑审度,
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
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宫之永慕。
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
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
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
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
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
对皓月以增伤,临芳樽而无赏。
他在通向曾是华夏文化中心地区的路途当中,看到的是胡化了的人民,听到的是胡人的音乐。那种痛惜着华夏文化被玷污,被糟蹋的伤痛,难以言说,只能“对皓月以增伤,临芳樽而无赏”。这段话突显主题的意图更清楚,不庸赘言。
如前所述,颜之推后来逃出了长安,到了邺下(河北临漳)。北齐虽然因为六镇起兵的影响,也一直涌动着胡化潮流,但是北魏洛阳的官僚和文人几乎都迁到了邺城,汉化的风气依然很浓厚。颜之推本人在北齐末年还进了朝廷为招揽汉族士大夫特设的“文林馆”,亲自为华夏文化的维系和发展尽一份努力。可是,这样的和平也难以长久。577年,北周打败北齐,邺下文人几乎都成了囚徒,颜之推也在囚徒之列,而且是俘回他经历千辛万苦才逃出来的长安。北周灭北齐虽然是胡人对胡人的战争,但是颜之推认为如果汉化政策在北齐得以实行,北齐可以不灭,华夏文化之正统可以恢复。可惜胡人当道,他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
唯骄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
惜染丝之良质,惰琢玉之遗祉。
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乱起。
这段话乃指北齐政坛最后一次胡汉冲突,及其所导致的国家灭亡,华夏文化恢复无望的结局。“武成”乃北齐皇帝(561-564在位);“夷吾”本是春秋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争霸中,使齐国强大起来的能臣管仲(?-前645),此借指汉人领袖祖珽;“狄牙”即易牙(生卒年不详),齐桓公(?-前643)时的乱臣,此借指胡人领袖穆提婆(生卒年不详)。那边场冲突是以汉人失败告终,所以颜之推无比痛心。(关于此次胡汉冲突详情,请参考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读史存稿》,第90-92页)即便如此,他在周军逼近的危急关头还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服皇帝投奔华夏文化尚存的陈朝。可是,依然事与愿违:
乃诏余以典郡,据要路而问津。
斯呼航而济水,郊向导于善邻。
不羞寄公之礼,愿为式微之宾。
忽成言而中悔,矫阴疏而阳亲。
信谗谋于公主,竞受陷于奸臣。
最后这一次努力乃是被得势的胡人高阿拉肱(生卒年不详)所破坏,故其赋依然未脱悲悯华夏文化的主题。
这一次又一次的厄运,仅仅归结为国家和个人命运,已无法解释得通,作者于是将其归结为华夏文化的厄运。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华夏文化犹且一再被蹂躏,作为华夏文化坚定的追随者和守卫者,又如何可以免祸:
余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
鸟焚林而铩羽翮,鱼夺水而暴鳞,
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夫有过而自讼,始发矇于天真,
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仁,
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
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榛,
广寿陵之故步,临大行以逡巡。
向使潜於茅草之下, 甘为畎亩之人,
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
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身。
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
此穷何由至,兹辱安所自臻?
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这段话万不可误解为颜之推悔为华夏文化坚守者之辞。其词貌似自悔,实则自嘲,自怜。自嘲自怜向来是自我坚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之正面坚持更为坚定。颜之推在最后一段终于说出了“观我生”的感悟:他之所以再三遭遇厄运,是自己很不合时宜地为华夏文化张目: “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榛”。在结束时,他使用了“泣麟”典故,大有深意。美国学者奥伯特 . 第恩( Albert Dien) 认为:“颜之推使用该典故,意在等待圣人来临。” (Albert Dien, “Yen here uses the allusion to the unicorn to mean that he awaits the coming of a sage.” Pei Ch’i shu 45: Biography of Yen Chih-t’ui, Bern: Herbert Lang & Cie AG, 1970. 183) 第恩的结论从何而来,不详。《春秋》经文本身仅记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九“哀十四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72-2173页)《左传》无多发挥:“西狩于野,叔孙氏之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往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同上,第2172-2173页) “泣麟”来源于《春秋公羊传》:“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试面,涕沾袍。(中略)孔子曰:‘吾道穷矣”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哀十四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52-2353页)何休注曰:“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太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 (同上,第2353页)则获麟预兆圣人将死,其道将亡。《孔子家语》 则说孔子自释为何而泣:“麒之至,为明君也,出其非时,而害吾,是以伤焉。” (《孔子家语》卷四,《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6页B面-17页B面)则获麟象征生不逢时,危害圣人。两种解释殊途同归。流行于两汉的公羊学派以固守“华夷之辨”“ 华夷之防”著名。颜之推用此公羊派之“泣麟”典故作结,与开头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相呼应,再次揭示了他的赋文主题所在。麒麟象征圣人和他所代表的华夏正统,既然已死,作者仍孜孜不倦地追求,并为之奋斗,所历身心痛苦,实乃自殉,何必怨天尤人?!作者自比孔子与华夏文化同命运之意甚明。赋文至此,悲悼自己与华夏文化同命运之主题达至高潮,既为作者命运一大哭,亦为华夏文化一大哭!士大夫殉道,执着且神圣,亦悲哀且痛苦,古今一理,令人泫然。
胡汉文化冲突是自西晋灭亡到北朝结束纠缠近三百年的多层面问题,但我们所见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在北朝文学作品中,此主题虽然一直存在,但时隐时现,从来不曾全面正面陈述。《观我生赋》把个人和国家遭遇与华夏文化的命运相联系,使胡汉文化势不两立的观念第一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在那个中国第一次经历外族统治,胡族处于强势,汉族处于劣势,华夏文化经历强烈冲击,蹒跚着试图站稳脚跟的时代,显得非常难能可贵。汉文化的优劣高低姑且不论,但她的确是可以在情感上平等给予所有华夏子孙慰藉的精神支柱。有人用文学的形式为她的遭遇痛苦,其意义之重大,无论怎么估价,都是不过分的。
三 颜之推之儒者风范与《观我生赋》之主题
从《观我生赋》立意观之,颜之推的思想深受《公羊》学派影响。《公羊》学派的民族思想从东汉以后就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即使在颜之推生活过的南方,其文学作品不如北方那样表现强烈的民族文化情感,但“华夷之防”和“华夷之辨”的儒家民族观一直是社会正统思想,无人挑战。侯景之乱时,梁朝诸大臣上笺萧绎劝进,赞扬他抗击胡人的功绩时,所据乃是儒家民族观:
夷狄内侵,枕戈泣血,鲸鲵未翦,投袂勤王。(《梁书》卷五《元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5页)
萧绎回应时,也是如此:
数钟阳九,时惟百六,鲸鲵未翦,寤寐痛心。(中略)率兹小宰,弘斯大德。将何用继踪曲阜,拟迹桓文,终建一匡,肃其五拜。(同上,第116页)
这里所谓曲阜,乃指孔子。桓文则指春秋时期尊王攘夷很成功的齐桓公(?- 前643)和晋文公(前697-前628)。在胡人肆虐时,人们自然会想起华夏民族观之祖孔子,怀念古代的攘夷英雄。推论及儒学世家的颜之推,道理也一样,经历了诸多胡人侵扰之后,自然会与儒家民族思想深深共鸣。
在《观我生赋》写成之地的北方,《公羊》学术的影响依然未坠。《魏书·梁祚传》记载:
至祚居赵郡。祚笃志好学,历治诸经,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魏书》卷八四《梁祚传》,第1844页)
梁祚大约是北魏平城时期赵郡(本治今邯郸,北魏移治今河北赵县)人,是时中原 之《公羊》学仍然后继有人。北魏洛阳时代邺下的情况不清楚,但洛阳为首都,离邺下不远,大约可从洛阳的情况推知邺下风气。据《魏书 . 儒林传》记载:
(刘)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魏书》卷八四《儒林 . 刘兰传》,第1851-1852页。也见《北史》卷八一《 儒林传》上《刘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16页)
刘兰是北魏洛阳时期人。他“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自有其道理。而且,洛阳时期的政治开明,思想活跃,各种思潮和学术都能够有立足之地,并不足奇。但他的行为“见讥于世”,即受到主流社会,或者正统学者的批评,就值得玩味了。“时人”并没有用学术的方式去反驳刘兰,而是用讥讽的方式。什么情况下主流社会会使用讥讽方式批驳别人?理所当然,无须讲道理的时候。可见,当时《公羊》学派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正统思想,所以刘兰抨击《公羊》为世人所不齿。
东魏北齐时期,《公羊传》学术也没有停息。比如:
李铉(生卒年不详),渤海人,曾撰《三礼》及《三传异同》。(《北齐书》卷四四《儒林 . 李铉传》,第584页。
张雕(生卒年不详),中山北平人,“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来就业者以百数。诸儒服其强辩。”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 . 张雕传》,第594页)
孙灵晖(生卒年不详),长乐武强人,“《三礼》及《三传》皆通宗旨,然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 . 孙灵晖传》,第596页)
在北齐时代,《春秋公羊传》不如两汉时期那么为人们热中,但是从上引三位学者的知识结构看,修习儒术的学者中也不乏兼通《春秋》三传者。兼通或即是当时习儒的风气,也未可知。无论如何,《春秋公羊传》的研习未曾停止,其思想的影响也不可能消失。北方人在经历了六镇起兵之后,写出了如李谐的 《述身赋》、李骞的《 释情赋》和羊玄之的《洛阳伽蓝记序》那样的篇章,就是儒家民族文化观影响的反映。这些作品,颜之推肯定读过,其中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情,不会不感染他。
不过,颜之推有如此强烈的民族文化情结,却还有其家世和个人的特殊背景。如前所述,颜之推所偏爱的第一祖籍在邹鲁地区,是孔子的家乡,儒家学说诞生地。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华夏文化的正统性和纯粹性。从创始人孔子开始,就一直强调这一点。春秋时期齐国成功阻挡了北方胡人侵扰,在尊王攘夷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霸主。当时孔子就对在齐国推行改革的管仲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激之情:“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道出了他对华夏文化的深切担忧。可见在齐鲁之邦,从很古的时候起,民族文化观念就很强。颜之推在北齐育有二子,长者名为“思鲁”,幼者名为“慜楚”。《北齐书》说,颜之推如此为儿子命名,以示“不忘本也。” (《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26页)缪钺先生指出: “‘愍楚’表示哀念故国(梁元帝都江陵,故曰楚)。”而“‘思鲁’表示怀思故乡(颜氏之先,本乎邹鲁)。” (缪钺《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第228页)但以我看来,在颜之推情感世界中,“慜楚”以示怀念故乡,而“思鲁”则以示坚持华夏文化。史家称其祖籍为齐地之临沂,则颜氏祖辈申报籍贯之际,已经土断为齐地人。为儿子命名属于私事,说明他在私下里,更看重与孔子同乡之地望,表现了他对华夏文化正统的强烈认同感。
当然,《春秋公羊传》学派对颜之推民族文化观的影响更直接。 颜之推偏爱的第二祖籍在琅邪临沂,即在古齐国区域内。该地区则是《春秋公羊传》学派的诞生地。《汉书 . 儒林传》载:“《公羊》氏乃齐学也。” (《汉书 》卷八八《儒林 . 颜安乐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18页)《春秋公羊传》的传者叫公羊子,什么时代的人不详,但却是“齐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3页)至西汉(前206-前22),尤其是汉武帝(前141-前87)时代,《公羊春秋》一派更是成为正统学问,立为五经博士之一。根据《汉书 . 儒林传》: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中略)年老归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中略)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中略)。唯嬴公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同上卷八八《儒林 . 胡毋生传》,第3615-3616页)
则西汉时期《公羊春秋》一派在齐地很盛行。颜之推祖籍齐地,当亦有受地域风气影响之可能。又同卷记载: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中略)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同上《儒林 . 严彭祖传》,第3616页)
该条史料所言之颜安乐(生卒年不详),是鲁国薛郡人。(同上《儒林·颜安乐传》,第3617页)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明确记载,颜安乐是其先祖之一。(《金石萃编》卷一0一,《石刻史料丛书》,第24页B面)颜真卿所撰《家庙碑》,直将家族历史追朔到远古时代,所有在历史上有名者,皆一一著录,可见颜家之重视家族传统。其家族之书法传统从南朝一直传到了唐朝,代有名人出,也证明其家族学问传承之紧密。颜安乐后人思想中有《公羊》学因素,盖理所当然。颜之推自矜祖籍邹鲁,也应与此有关。
到东晋之初,颜氏家族受《公羊》学影响,尚有迹可寻。《晋书》卷八八《颜含传》载:
于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含,含曰:“王公虽贵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有邪德乎!”。(《晋书》卷八八《颜含传》,第2287页。亦见《资治通鉴》卷九六“晋成帝咸康四年”,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24-3025页。文字略有出入)
颜含(265-358),即颜之推九世祖,迁移江左第一代。他不畏王导权势,坚守君臣礼仪,足见其恪守儒家原则。很关键的是他在讽刺冯怀时所用“伐国不问仁人”典故,正是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卷九载:“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至于我哉!’” (《春秋繁露义证》卷九“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267页)说明颜含不但非常熟悉《公羊春秋》典籍,也尊公羊学理论为思想指南。
从《北齐书》的记载看,在学问上,颜氏家族习《左传》而不是《公羊》。(《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7页)可能原本颜家传统学问就是《左传》,也可能是《公羊》学术淡化以后转习《左传》。颜家后人,也许学术专攻有所改变,但其家族保持儒家传统,却丝毫未变。《北齐书 . 颜之仪传》记载:
祖见远,(南)齐御史治书。正色立朝,有当官之称。及梁武帝执政,遂以疾辞。寻而齐和帝暴崩,见远恸哭而绝。(中略)当时嘉其忠烈,咸称叹之。父协,以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周书》卷三二《颜之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9页)
其兄颜之仪在隋文帝(589-604在位)代周时,也同样坚守儒家原则,拒绝在诏书草稿上署名。文帝向他索取皇帝符玺,他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 (同上,第720页)《公羊春秋》学派最讲君臣纲常。臣取君而代之,实违反纲常,所以颜氏诸贤有那些激烈的“正义”之举。
颜之推本人固执儒家传统,也与《观我生赋》主题相吻合。清人赵曦明(生卒年不详)说他是“坚正之士”,是对他人格操守最为切当的评价。(评语见赵氏《颜氏家训跋》,载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序跋》,第632页)他十二岁时进入萧绎府中听讲老庄,但很快就放弃了,转而研究儒学。他自己解释其放弃老庄哲学的原因之一是“性既顽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卷三 “勉学”,第187页)按说,他个性很不羁,该更认同老庄,而疏远儒家,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只能理解为,他从小受家世儒风的熏陶,老庄玄学很难为其欣赏。
颜之推之固守华夏文化,不仅表现在他的儒学造诣很深、而且表现在在朝堂上反抗胡人。北齐后主执政时期,发生了缪钺先生所称的第三次胡汉冲突,汉人方面以祖珽(生卒年不详)为首,颜之推即是干将之一。(关于当时胡汉冲突详情,请参考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读史存稿》,第90-92页)武平三年(572)二月,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颜之推即是立文林馆发起人之一:“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 (《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第563页)所谓“耆旧贵人”,乃指胡人贵族。可见颜之推抗胡之志甚坚,要为华夏文化留一清静之地。因为他深得祖珽欣赏,任他作知馆事。馆中文书都是他审阅并签署。不久就迁升为中书舍人,为皇帝所重用,引起了“勋要”的嫉妒,“常欲害之”。(《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8页)与胡化势力抗争,以至于不惜生命安全,可想而知,颜之推当时卷入北方人抵制胡化势力的行动有多深。
颜之推之固守华夏文化还表现在生活中。他总是站在爱华夏,反胡化的立场上。当很多汉人都以学习鲜卑语和弹奏胡乐器琵琶为时尚之际,他却拒绝如此,提醒儿子不要跟从: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教子”,第21页)
其他人教孩子学胡人文化,仅以能服侍公卿为满足,颜之推却说即便能因此官为卿相,也不愿意。他之抗拒胡族文化,可谓完全彻底,没有丝毫妥协。
抗拒胡族文化的同时,颜之推也致力于恢复华夏正统文化。设立文林馆已是其努力之一。隋开皇二年(582),颜之推曾上书文帝:“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45页)所谓“太常雅乐,并用胡声”指自十六国以来,胡人统治中原,华夏雅乐缺失,北魏诸皇帝,尽皆爱好胡乐,以至于将胡乐当作官方乐府,在正式场合演奏。(另文探讨)因此,固执华夏正统文化的颜之推不能接受。只是他对隋文帝了解不够,错将恢复华夏正统文化的希望寄托在隋文帝身上,而作此建议。结果当然是遭到文帝拒绝:“梁朝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345页)无论如何,颜之推的努力却实实在在。另一次恢复华夏正统文化的努力,是关于如何审定华夏正音。在隋开皇初年一次聚会上,八位音韵专家讨论了如何恢复华夏正音的问题,颜之推即为其中的关键人物。根据陈寅恪的研究,颜之推积极主张恢复的官话乃是西晋以前洛阳太学中使用的规范发音。(参考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在颜之推看来,晋朝南迁之后,正宗的洛阳官话已经“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七“音辞”,第530页)所以,他既不接受“南染吴越”的金陵官话,也不接受“北杂夷虏”的北方官话。换句话说,他要摈弃华夏音韵中的所有胡族因素。后来陆法言所撰《切韵》就是根据颜之推的“遗愿”,综合各地官话,尽量重构了西晋以前的洛阳官话。(另文探讨)
总之,从《观我生赋》以《公羊》民族思想贯穿始终的事实,说明颜之推不但对《公羊》学派民族思想非常熟悉,而且信奉不疑。其中,时代风气的影响,其家族传统和他个人在公私活动两方面的儒者风范,都为《观我生赋》的主题作了很好的注脚。
四 颜之推 《观我生赋》与庾信 《哀江南赋》之比较
人们一般都认为庾信 《哀江南赋》是亡国思乡作品中之最,自然比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更佳。甚至有学者指出《观我生赋》是《哀江南赋》的仿作。(周发高《颜之推 ‘观我生赋’ 与庾信 ‘哀江南赋’ 之比较》,《大陆杂志》 20:4 (1960年): 第101页)从创作时间上看,《观我生赋》晚出,可能受到《哀江南赋》的启发。同样以写作时间先后论,沈炯《归魂赋》、李谐 《述身赋》、李骞《 释情赋》也有启发之功。而且论主题思想和民族文化感情,则李谐《述身赋》和李骞《 释情赋》与颜之推的赋更接近。但是,若说颜之推完全因为受他人启发而作此赋,没有自己不得不为之的创作冲动,则笔者不敢苟同。若为仿作,早在沈庾二李作赋后不久,就该写成。颜之推的赋在二十余年之后才写成,说明他并没有赶作悲情赋的时髦。(据笔者考证,《哀江南赋》作于556年年末,与《归魂赋》差不多同时。鲁同群也有相同的考证,请参考他的《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19页)。则《观我生赋》在《哀江南赋》写成之后二十余年写成)如果因其赋与前人作品在内容上有相同之处,而贬低其文学价值,则更不敢苟同。笔者在比读颜之推 《观我生赋》和庾信 《哀江南赋》时, 所见之不同,远多于同,不妨陈述于此。
首先,两位作者经历不同,赋中所涵盖的内容也不同。颜之推所记之亡国经历,多半为庾信未曾经历。比如西魏攻陷江陵时,颜之推见证了江陵被毁的全过程,而庾信已在早前作为使者,前往长安。同是迁移到北方,颜之推是被俘去的,尝尽了北迁路上的艰难困苦,而庾信则是作为使者前往,各种条件均好。庾信也写到此次北迁情形,但笔者猜想他所依据全是听闻,或者想象。他早前作为使者北上,大约走同一条道,也易于想象。北齐灭亡,颜之推再次经历兵燹,而且再次被俘押往长安。此时,庾信正在长安享受优厚的待遇和平静的生活。即便同是经历侯景之乱,他们的情况也很不同。侯景攻建康,“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 (《周书》卷四一《庾信传》,第733-734页)但庾信几乎是不战而逃:“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同上)在《哀江南赋》里,他把守城一段写得很悲壮,但其实并非亲历。其赋文中叙述逃往江陵一段,倒是很真实的记录。颜之推当时驻扎郢州,并未亲见侯景入建康城的情形。但是,他两年后被侯景军队俘虏,押回建康,亲眼目睹曾是故乡的首都被毁之后的惨状,又为庾信所未见。
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同,两赋立意也迥然不同。如前所述,颜之推赋之立意在悲悯华夏文化,以及作为华夏文化之一分子的悲悯自我。故在颜赋中,开篇写华夏立国,内诸夏而外夷狄,然后写华夏文化的式微,最后至于灭国。而庾赋之立意则是悲悯故国,以及自我悲悯。所以,其赋开篇写庾家的昌盛和自己的和平幸福生活,然后写国家遭难,家族由盛到衰,自己深受其害。每次遭遇灾难,庾信都只看到国家,家族,或者自己的悲剧和苦难,而颜之推却总看华夏文化和自己的悲剧和苦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们对北迁长安的描述很不同: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
饥随蛰燕,暗逐流萤。
秦中水黑,关上泥青。
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
浑然千里,淄渑一乱。
雪暗如沙,冰横似岸。
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
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以上是庾信的描述,说的是别人的经历,虽然悲哀,却只有离乡之悲哀。
牵沉疴而就路,策驽蹇以入关。
下无景而属蹈,上有寻而亟搴。
嗟飞蓬之日永,恨流梗之无还。
若乃五牛之旌,九龙之路,
土圭测影,璇玑审度,
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
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宫之永慕。
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
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
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
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
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
对皓月以增伤,临芳樽而无赏。
以上是颜之推的描述,全是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不但写离乡之艰难和悲哀,更有华夏文化毁灭之悲哀。二赋立意不同,可见一斑。颜赋更有北方传统,而庾赋还是南方特色。
最重要者乃是两首赋风格迥异。《哀江南赋》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用对比的手法,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戏剧化,确显赋家之本色。而颜赋却无此意向。颜之推的赋从头至尾都用朴实的笔调,叙述华夏文化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小遭遇融入华夏文化的大遭遇之中。颜赋意在于传达他所坚守的天地正气,自然不可能写得那么色彩斑斓。《北齐书》作者评价此赋“文致清远”,应为的评。(评语见《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18页)我以为,他之所以如此作赋,并非(或者并非仅仅由于)才输庾信,而是其文学观与庾信不同。庾信之文学风格,正如《周书》作者所言: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赞》,第744页)
虽然庾信到了北方之后,情感有变化,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也不同,但依然不脱“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的基本路数。换句话说,他的文风还是非常注重形式美和夸张煽情。所以,初唐史家并未因为他写了《哀江南赋》和很多其他哀伤的作品,就认为他文风变化,而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他是“词赋之罪人”。杜甫说他的文章“老更成”,想必是指其文章有了质感,不再空洞无物,而非指其文学风格发生巨大变化。庾信的文章风格,几乎不可能为颜之推所接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 . 文学》中写道: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第267页)
众所周知,当时南北文风都受徐庾体影响,注重形式。颜之推对此种文风极为不满,只是无力改变,他自己绝不可能追随其后。此与其儒教家风密切相关: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迄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同上,第269页)
“湘东王”即萧绎,当时,任荆州刺史,驻扎江陵,故曰“西府”。这里所言《西府新文》,指萧绎尚未即位前,属下文人作品选集。该文集文学风格即在其藩镇流行的文风,与建康之流行文风相似。钟仕伦将“西府”文士广义化,在西府任过官的文人,尽皆归入,则当时文坛巨子如徐陵 (507-583) 、庾信、阴铿(生卒年不详)、王藉(生卒年不详)、刘峻(462-521)、裴子野 (469-530)、劉之遴 (生卒年不详),王褒(大约511-575年),江总(生卒年不详),等等,都属于西府文士。(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此处颜之推所指,显然不是广义的西府文士,而是偏爱时髦文风的人物。不过,钟仕伦对西府文士所作的分类,倒是很说明问题。他将徐陵 (507-583) ,庾信等归作偏好“今文”;裴子野和 劉之遴等偏好“古文”;王褒和颜之推等则居中。(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第289页)“新文”也就是“今文”,以徐庾为代表。王褒《幼训》曰:“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梁书》卷四一《王规传》附子《王褒传》,第584页)可见居中的王褒是新旧兼采。于颜之推父亲,恐怕连“兼循老释之谈”也在拒绝之列,所以《西府新文》不采其文。钟仕伦认为颜之推居中间,新旧兼采,只是根据一些旁证,并无直接资料证明。那时颜之推非常年轻,几乎不可能与徐庾王等大家相提并论。加之也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很难断定他当时的文风到底如何。不管当时他偏好哪种文风,到了北方之后,应该是坚守儒家原则。他不写以徐庾为代表的“新文”,显然是因为“新文”与其家世儒家文学观冲突。钟仕伦认为他是因为迫于北齐文风和北周文体改革的压力,笔者很难苟同。从颜之推幼年时代拒绝听萧绎讲老庄,转业儒学,到晚年写《观我生赋》以及积极为保持华夏文化努力,其儒者风范前后一致,贯穿平生,如何可能被人逼着说假话?颜庾二赋风格不同,实因文学观差异,非关才华高低。不能想象庾信能写出《观我生赋》,也不能想象颜之推能写出《哀江南赋》。但不能因此不同,而定其作品之文学价值孰高孰低。于当时的文学而言,二者都不可或缺。
至于在审美效果上,则笔者也不认为二赋差得很远,此略言几句。笔者已经叙述了颜之推作品立意之特别,我们对他的赋该持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在体验和表达个人情感一面,也许他不及庾信,但在体验和表达悲悯民族文化一面,庾信又不及他。尤其如果将此两篇作品都放到北朝时期,那个中国不仅亡国,而且华夏文化几乎无以立足的时代背景下,笔者不信人们读《观我生赋》会不如读《哀江南赋》感动。“瀍澗鞠成沙漠,神华泯為龙荒”;“就狄俘於旧壤, 陷戎俗於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鼖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 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伤,临芳樽而无赏”;“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榛,广寿陵之故步,临大行以逡巡。 向使潜於茅草之下, 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这些为华夏文化哭泣的句子,句句都是作者的锥心之痛,千古之下读之,依然让人潸然泪下。
结语
展示了颜之推《观我生赋》之立意,其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以及其与众不同的文学特征,这篇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之高,已不用赘言。作为儒者文学家,颜之推在历史需要他为华夏文化呐喊的时候,及时做到了,不但用政治的方式,文化的方式,而且还用文学的方式,可谓不辱使命。我们在赞扬爱国文学的时候,不应该忘记颜之推和他的《观我生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