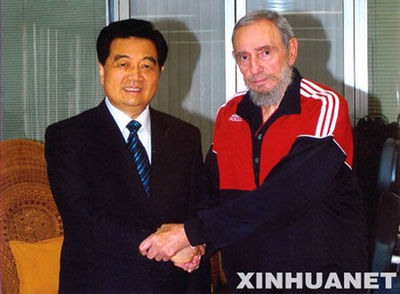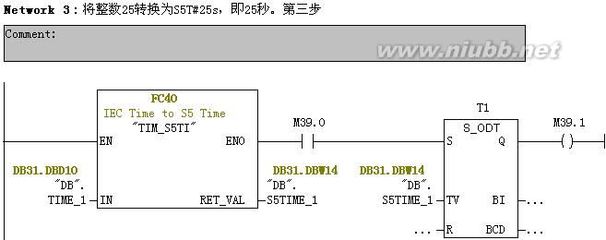(转自《数学苑》http://www.teachblog.net/poincare/)
前言:本文是《Notices of the AmericanMathematical Society》杂志2004年10月和11月份发表的Allyn Jackson关于AlexandreGrothendieck文章的翻译。
仿佛来自虚空(1)
每一门科学,当我们不是将它作为能力和统治力的工具,而是作为我们人类世代以来努力追求的对知识的冒险历程,不是别的,就是这样一种和谐,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或多或少,巨大而又丰富:在不同的时代和世纪中,对于依次出现的不同的主题,它展现给我们微妙而精细的对应,仿佛来自虚空。
——《收获与播种》,第20页
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是一位对数学对象极度敏感,对它们之间复杂而优美的结构有着深刻认识的数学家。他生平中的两个制高点——他是高等科学研究院(IHES)的创始成员之一,并在1966年荣获菲尔兹奖——就足以保证他在二十世纪数学伟人殿里的位置。但是这样的叙说远不足以反映他工作的精华,它深深植根于某种更有机更深层的东西里面。正如他在长篇回忆录《收获与播种》中所说:
“构成一个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品质的东西,正是他聆听事情内部声音能力”(原书第27页)。今天格罗滕迪克自己的声音,蕴含在他的著作中,到达我们耳中,就如来自虚空:如今76岁的高龄,他已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落里隐居十多年了。
用密歇根大学海曼-巴斯的话来说,格罗滕迪克用一种“宇宙般普适”的观点改变了整个数学的全貌。如今这种观点已经如此深入吸收到数学研究里面,以至于对新来的研究者来说,很难想象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格罗滕迪克留下最深印迹的是代数几何学,在其中他强调通过发现数学对象间的联系来理解数学对象本身。他具有一种极其强大、几乎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抽象能力,让他能够从非常普适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且他使用这种能力又是完美无缺的精确。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整个数学领域里不断加深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罗滕迪克。同时,那些为一般化而一般化,以至于去研究一些毫无意义或者没有意思的数学问题,是他从来不感兴趣的。
格罗滕迪克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早期生活充满混乱和伤害,并且他的教育背景并不是最好的。他如何从这样缺乏足够教育的开始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的领袖数学家之一,是一出精彩的戏剧——同样,在1970年,正当他最伟大的成就在数学研究领域开花结果,而且数学研究正深受他非凡个性影响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数学研究,也是富有戏剧性。
早期生活
对于我来说,我们高中数学课本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是缺乏对长度、面积和体积的严格定义。我许诺自己,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得填补这个不足。
——《收获与播种》,第3页
2003年八月以八十岁高龄过世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阿曼德-波莱尔回忆起他在1949年11月在巴黎一次布尔巴基讨论班上第一次见到格罗滕迪克的情形。在讲座的空歇时间,当时二十多岁的波莱尔正与时年45岁,法国数学界那时的一位领袖人物查尔斯-爱尔斯曼聊天。波莱尔回忆说,此时一个年轻人走到爱尔斯曼面前,不作任何介绍,当头就问:“你是拓扑群方面的专家吗?”为了显示自己的谦虚,爱尔斯曼回答说是的,他知道一点点关于拓扑群的知识。年轻人坚持说:“可我需要一个真正的专家!”这就是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时年21岁——性急,热情,确切说不是无礼,但对社交礼仪差不多一无所知。波莱尔记得格罗滕迪克当时问了一个问题:
每个局部拓扑群是否是整体拓扑群的芽?波莱尔自己恰好知道一个反例。这个问题表明格罗滕迪克那个时候就已经考虑用很普适的观点还考虑问题了。
1940年代末在巴黎度过的时期是格罗滕迪克首次和数学研究世界的真正接触。在此之前,他的生活——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预示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界一位具统治地位的人物。大多关于格罗滕迪克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的情节都是粗略或者未知的。穆斯特大学的温弗雷德-沙劳正在撰写一部格罗滕迪克的传记,因而对他的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研究。下面我对格罗滕迪克生平的简略描述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对沙劳的一次访谈或者来自于他收集的关于格罗滕迪克生平的资料。
格罗滕迪克的父亲,其名字或许叫亚历山大-沙皮诺,于1889年10月11日生于乌克兰诺夫兹博科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沙皮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过20世纪早期沙皇俄国多次暴动。在17岁的时候他被捕,尽管成功逃脱死刑的判决,但是数次越狱又被抓获,让他一共在狱中呆了大约10年时间。格罗滕迪克的父亲,有时候常常被人混淆为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亚历山大-沙皮诺,他也参加过了多次政治运动。那位沙皮诺,曾在约翰-里德的名著《震撼世界的10天》里面出现过,移民去了纽约并于1946年去世,那时候,格罗滕迪克的父亲已经过世4年了。另外一个关于格罗滕迪克父亲的显著特征是他只有一只手。根据贾斯汀-巴姆比(她在1970年代曾经与格罗滕迪克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和他育有一个儿子)的话来说,他的父亲是在一次逃避被警察抓获而尝试自杀的行动中丢失他的一只胳膊的。格罗滕迪克本人可能不知情地帮助造成这两个沙皮诺的混淆:举个例子,高等科学研究院的皮埃尔-卡迪耶尔提到格罗滕迪克坚持里德的书里面一个人物是他父亲。
仿佛来自虚空(2)
小朋友时代结束。下面牛人们将一个个登场。
1921年,沙皮诺离开俄国,从那时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国籍人。为了隐瞒他的政治过去,他获得了一份名叫亚历山大-塔纳洛夫的身份证明,从此他就用这个新的名字。他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都呆过一段时间,和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革命团体均有联系。在1920年代中期一个激进份子圈子里面,他认识了格罗滕迪克的母亲,琼娜(汉卡)-格罗滕迪克。她于1900年8月21日出生在汉堡一个中产阶级路德教徒家庭里。出于对她所受的传统教育的反叛,她被吸引来到柏林,当时那里是先锋派和社会革命运动的温床。她和沙皮诺都渴望成为作家。他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而她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特别的,在1920年到1922年间她为一家左翼报纸DerPranger写稿,当时它正在调查生活在汉堡社会底层的妓女们卖淫的真正原因。很久以后,在1940年代,她写了一本自传小说EineFrau(《一个小女人》),不过从未发表。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塔纳洛夫是一位街头摄影师,这项工作让他可以独立生活,又不用违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去被人雇佣。他和汉卡曾经都结婚过,而且都各有一个前次婚姻所生的孩子,她有个女儿而他有个儿子。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于1928年3月28日出生于柏林,其时他们家由汉卡,塔纳洛夫,汉卡的女儿、比亚历山大大四岁的麦娣组成。他被家人和后来的密友们叫做舒瑞克;他父亲的昵称叫萨沙。尽管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格罗滕迪克将他在1980年代完成的手稿A La Poursuite des Champs(《探索Stacks》)献给了他。
1933年,纳粹上台后,沙皮诺从柏林逃到了巴黎。同年12月,汉卡决定追随丈夫,于是她将儿子留在汉堡附近布兰肯尼斯的一个寄养家庭里面;麦娣则留在柏林一个收养残疾人的机构里,尽管她并不是残疾人(《收获与播种》,472-473页)。这个寄养家庭的家长是威尔海姆-海铎,他的不平凡的一生在他的传记Nur MenschSein里面得到详细描述;同书里面有格罗滕迪克1934年的一张照片,而且在书中他被简要提起。海铎曾经是路德教会牧师和军官,随后他离开教会,成为小学教师,同时是一位Heipraktiker(这个词现在可以粗略翻译为“另类医学的从业者”,江湖医生)。1930年他创立了理想主义政党人道主义党,此党后来被纳粹认定为非法。海铎自己有4个孩子,他和妻子代格玛,出于他们信仰的基督教义务,又收养了好几个孩子,他们都由于在二战前那段混乱日子不得不与自己的家庭分开。
格罗滕迪克从5岁到11岁,在海铎家里呆了5年多,并且开始上学。代格玛-威尔海姆在回忆录里面说小亚历山大是一位非常自由,特别诚实,毫无顾忌的小孩。在他生活在海铎家这几年里,格罗滕迪克只从他母亲那里收到几封信,他父亲根本就没有给他写过信。尽管汉卡仍然还有些亲戚在汉堡,从没有人来看过他。突然和父母分离,对格罗滕迪克是非常伤心的事情,这可以从《收获与播种》书中看出(473页)。沙劳认为小亚历山大可能在海铎家里过得并不愉快。从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作家长的不受拘束的家里出来,海铎家里的比较严肃的氛围可能比较让他觉得郁闷。事实上,他和海铎家附近其他一些家庭更亲近些,成年以后他仍然多年坚持给他们写信。他也给海铎家写信,并且数次回来拜访汉堡,最后一次是在1980年代中期。
1939年,战争迫在眉睫,海铎夫妇所承受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能够再抚养这些孩子了。格罗滕迪克这个情况更困难些,因为他看上去就象犹太人。尽管他父母的确切地址不为人知,但是代格玛-海铎写信给法国驻汉堡领事馆,设法给时在巴黎的沙皮诺和时在尼姆兹的汉卡带去消息。联系到他父母以后,11岁的格罗滕迪克被送上从汉堡到巴黎的火车。1939年5月他和父母团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战前的短暂时光。
目前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当格罗滕迪克在汉堡的时候,他的父母干了些什么的细节,但可以肯定他们政治上仍然很活跃。他们跑到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当佛朗哥获胜后又逃回法国。由于他们的政治活动,汉卡和她的丈夫在法国被当作危险的外国人。格罗滕迪克回到他们身边不久,沙皮诺就被送入LeVernet的国际集中营,此地是所有法国集中营中最糟糕的。很可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了。1942年8月,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到奥斯维辛,在那里他被杀害。麦娣那段时期如何度过我们并不清楚,但最终她和一位美国士兵结婚,并移居美国;她于几年前过世。
1941年汉卡和她的儿子被送入Mende附近Rieucros的战俘收容所。就战俘收容所而言,Rieucros的这个算比较好的,格罗滕迪克被允许到Mende去读高中。然而,这种生活被剥夺了自由,又很不确定。他告诉巴姆比说,他和他母亲时常被那些不知道汉卡是反对纳粹的法国人故意躲开。有一次他从收容所跑了出去,想去刺杀希特勒,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了回来。“这很可能让他丢了性命的”,巴姆比说。格罗滕迪克一生以来都很强壮,是一个很优秀的拳击手,他将此归功于这段时期,因为他常常是被伏击的对象。2年后,母子俩又分开了:汉卡被送到另一个战俘收容所,而她的儿子则最终送到小镇Chambon-sur-Lignon。安德烈-特洛克姆,一位新教徒牧师,将这个山区休假胜地Chambon镇变成了反抗纳粹占领的据点和犹太人及其他被战争危及生命的人们的避难所。在那里格罗滕迪克被送到由一个瑞士组织成立的儿童之家。他在Chambon镇专门为年轻人的教育而设立的Cevenol学院上学并得到业士学位(即通过中学毕业会考)。Chambon人的英雄行为给了逃难者安全,但是生活却是很不稳定的。在《收获与播种》里,格罗滕迪克提到当时周期性的抓捕犹太人的行动迫使他和其他同学在森林里躲藏好几天(第2页)。
在此书中,他也提到些对Mende和Chambon上学情况的回忆。很显然,尽管少年时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混乱,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很强的内在理解能力。在他的数学课上,他不需要老师的提示就能区分什么东西是深层的、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发现课本上的数学问题老是重复,而且经常和那些可以赋予它意义的东西隔离开。“这是这本书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写道。当有问题引起他注意时,他就完全忘我的投入到问题中去,以至于忘记时间(第3页)。
仿佛来自虚空(3)
从蒙彼利尔到巴黎到南锡
我的微积分老师舒拉先生向我保证说数学上最后一个问题已经在二三十年前就被一个叫勒贝格的人解决了。确切地说,他发展了一套测度和积分的理论(真是很令人惊讶的巧合!),而这就是数学的终点。
《收获与播种》,第4页
1945年5月欧战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17岁。他和母亲居住在一蒙彼利尔郊外盛产葡萄地区的一个叫Maisargues的村子里。他在蒙彼利尔大学上学,母子俩靠他的奖学金和葡萄收获季节打零工来生活;他母亲也做些清扫房屋的工作。不久以后他呆在课堂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因为他发现老师全是照本宣科。根据让-丢多涅的话来说,那时的蒙彼利尔是“法国大学里面教授数学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在这种不那么令人激昂的环境下,格罗滕迪克将他在蒙彼利尔三年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弥补他曾经觉察到的高中教科书上的缺陷,即给出令人满意的长度、面积和体积的定义。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他实际上重新发现了测度论和勒贝格积分的概念。这个小故事可以说是格罗滕迪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两个人生平中几条平行线之一:年轻的爱因斯坦根据自己的想法发展了统计物理理论,后来他才知道这已经由约舒亚·维拉德·吉布斯发现了!
1948年,在蒙彼利尔完成理学学士课程后,格罗滕迪克来到了巴黎,法国数学的主要中心。1995年,在一篇发表于一法文杂志上关于格罗滕迪克的文章中,一位名叫安德烈-马格尼尔的法国教育官员回忆起格罗滕迪克的去巴黎求学的奖学金申请。马格尼尔让他说明一下在蒙彼利尔干了些什么。"我大吃一惊,"文章引用马格尼尔的话说,"本来我以为20分钟会面就足够了,结果他不停的讲了两个小时,向我解释他如何利用'现有的工具',重新构造前人花了数十年时间构建的理论。他显示出来非凡的聪慧。"马格尼尔接着说:"格罗滕迪克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才气惊人的年青人,但是所受的苦痛和自由被剥夺的经历让他的发展很不均衡。"马格尼尔立刻推荐格罗滕迪克得到这个奖学金。
格罗滕迪克在蒙彼利尔的数学老师,舒拉先生推荐他到巴黎去找他以前的老师嘉当。不过到底是父亲,时年快八十的埃里·嘉当,还是他的儿子,四十多岁的亨利-嘉当,格罗滕迪克并不知道(《收获与播种》,第19页)。在1948年秋天到达巴黎后,他给那里的数学家看在蒙彼利尔自己做的工作。正如舒拉所说,那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不过格罗滕迪克并不觉得沮丧。事实上,这段早期孤独一人的努力可能对他成为数学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收获与播种》中,格罗滕迪克谈到这段时期时说:"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在孤独工作中学会了成为数学家的要素--这些没有一位老师能够真正教给学生的。不用别人告诉我,然而我却从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位数学家:也就是说,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做数学的人就好像人们'做'爱一样。”
他开始参加亨利-嘉当在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的传奇性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采用了一种格罗滕迪克在以后的职业生涯更严格化的模式:每一年所有的讨论围绕一个选定的主题进行,讲稿要系统的整理出来并最终出版。1948-1949年嘉当讨论班的主题是单形代数拓扑和层论--当时数学的前沿课题,还没有在法国其他地方讲授过。事实上,那时离让-勒雷(JeanLeray)最初构想层的概念并没有多久。在嘉当讨论班上,格罗滕迪克第一次见到了许多当时数学界的风云人物,包括克劳德·夏瓦雷(ClaudeChevalley),让·德尔萨(Jean Delsarte),让·丢多涅(Jean Dieudonne),罗杰·苟德曼(RogerGodement),洛朗·施瓦兹(Laurent Schwartz)和安德烈·韦依(AndreWeil)。其时嘉当的学生有让·皮埃尔·塞尔(Jean-PierreSerre)。参加嘉当讨论班以外,他还去法兰西学院听勒雷开设的一门介绍当时很新潮的局部凸空间理论的课程。
作为几何学家埃里·嘉当的儿子,自己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并且又是巴黎高师的教授,从多个方面来看亨利·嘉当都是巴黎精英数学家的中心。而且他还是战后少数几位努力创造条件与德国同行们交流的法国数学家之一,尽管他自己很清楚战争带给的惨痛:他的弟弟参加了抵抗德国占领的地下运动,结果被德国人抓获并斩首。嘉当和当时的许多一流数学家--比如爱尔斯曼,勒雷,夏瓦雷,德尔萨,丢多涅和韦依--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是"高师人",即为法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当格罗滕迪克加入嘉当讨论班的时候,他还是个外来人:这不仅仅是说他居住在战后法国而又讲德语,而且因为他与其他参加者比较起来显得特别贫乏的教育背景。然而在《收获与播种》里,格罗滕迪克说他并不觉得象是圈子里面的陌生人,并且叙述了他对在那受到的"善意的欢迎"的美好回忆(第19-20页)。他的坦率直言很快就引起大家的注意:在给嘉当100岁生日的颂词中,JeanCerf回忆说,当时在嘉当讨论班上看到"一个陌生人(即格罗滕迪克),此人从屋子后部随意向嘉当发话,就如同和他平起平坐一样"。格罗滕迪克问问题从不受拘束,然而,他在书上写道,他也发现自己很难明白新的东西,而坐在他旁边的人似乎很快就掌握了,就象"他们从摇篮里就懂一样"(第6页)。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促使他在嘉当和韦依的建议下,于1949年10月离开巴黎的高雅氛围去了节奏缓慢的南锡。另外,如丢多涅所言,格罗滕迪克那时候对拓扑线性空间比对代数几何更感兴趣,因此他去南锡恰当不过了。
仿佛来自虚空(4)
南锡的学习生涯
(我在这里受到的)欢迎弥漫开来……从1949年首次来到南锡的时候我就受到这样的欢迎,不管是在Laurent和HeleneSchwartz的家(那儿我就好像是一个家庭成员一样),还是在Dieudonne的或者Godement的家(那里也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之一)。在我初次步入数学殿堂就包容在这样挚爱的温暖中,这种温暖虽然我有时易于忘记,对我整个数学家生涯非常重要。
《收获与播种》,第42页
1940年后期,南锡是法国最强的数学中心之一;事实上,虚构人物尼古拉-布尔巴基据说是“Nancago大学”的教授,就是指在芝加哥大学的韦依和在南锡大学的他的布尔巴基同伴。此时南锡的教员包括德尔萨,Godement,Dieudonne和Schwartz。格罗滕迪克的同学包括Jacques-LouisLions和Bernard Malgrange,他们和格罗滕迪克一样均是Schwartz的学生;以及PauloRibenboim,时年20岁,差不多与格罗滕迪克同时来到南锡的巴西人。
根据现在是(加拿大)安大略省Queens大学名誉教授Ribenboim的话来说,南锡的节奏不象巴黎那么紧张,教授们也有更多时间来指导学生。Ribenboim说他感觉格罗滕迪克来到南锡的原因是因为他基础知识缺乏以致很难跟上Cartan的高强度讨论班。这不是格罗滕迪克出来承认的,“他不是那种会承认自己也会不懂的人!”Ribenboim评论说。然而,格罗滕迪克的超凡才能是显而易见的,Ribenboim记得自己当时将他作为完美化身来景仰。
格罗滕迪克可能会变得非常极端,有时候表现得不太厚道。Ribenboim回忆说:“他不是什么卑鄙的人,只是他对自己和别人都要求很苛刻.”格罗滕迪克只有很少几本书;他不是从读书中去学习新的知识,而宁愿自己去重新建构这些知识。而且他工作得很刻苦。Ribenboim还记得Schwartz告诉他:你看上去是个很友善、均衡发展的年轻人;你应该和格罗滕迪克交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玩,这样他就不会整天工作了。
其时Dieudonne和Schwartz在南锡开设了关于拓扑线性空间的讨论班。如Dieudonne在[D1]所说,那时候Banach空间及其对偶已经理解得很清楚了,不过局部凸空间的概念当时刚刚引入,而关于他们的对偶的一般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和Schwartz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决定将这些问题交给格罗滕迪克。数月之后,他们大吃一惊地得知格罗滕迪克已经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并在继续研究泛函分析的其他问题。“1953年,应当给予他博士学位的时候,有必要在他写的六篇文章中选取一篇做博士论文,可每一篇都有好的博士论文的水准,”丢多涅写道。最后选定作为论文的是“拓扑张量积和核空间”,这篇文章显示出他的一般性思考的初次征兆,而这将刻划格罗滕迪克的整个数学生涯。核空间的概念,在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就是首先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的。Schwartz在巴黎一次讨论班上宣传了格罗滕迪克的结果,
其讲稿“格罗滕迪克的张量空间”发表于1954年[Schwartz]。此外,格罗滕迪克的论文作为专著1955年在美国数学会的Memoir系列出版;此书[GThesis]在1990年第七次重印。
格罗滕迪克在泛函分析方面的工作“相当出色”,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Edwards E.Effors评论说。“他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二战后迅猛发展的代数和范畴工具可以用来研究如此高度解析的数学分支泛函分析的人了。”从某些方面来说,格罗滕迪克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Effors注意到至少花了15年时间,格罗滕迪克的工作才结合到主流的Banach空间理论中去,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大家对采用他的更代数的观点不积极。Effors还说道,近年来由于Banach空间理论的“量子化”,而格罗滕迪克的范畴论的方法特别适用于这种情况,他的工作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
尽管格罗滕迪克的数学工作已经得到很有前途的开始,他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安定下来。在南锡他和母亲住在一起,根据Ribenboim的回忆,她由于肺结核偶尔会卧床不起。她是在收容所染上这种疾病的。就在这时候她开始写自传《小女人》的。格罗滕迪克和管理他和他母亲寄住的公寓的一位年老妇人的关系让他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名叫塞吉的儿子:塞吉主要由母亲抚养。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后,格罗滕迪克找到永久职位的希望很小:他是无国籍人,而那时在法国非公民很难找到永久工作。想成为法国公民就得去参军,而格罗滕迪克拒绝这样做。从1950年起他通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有个职位,不过这个职位更象奖学金,而不是永久性的。有段时间他甚至考虑去学做木匠来赚钱谋生(《收获与播种》,第1246页)。
LaurentSchwartz于1952年访问了巴西,给那里的人说起他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在法国找工作遇到的麻烦。结果格罗滕迪克收到圣保罗大学提供给他的访问教授职位的提议,他在1953年和1954年保持了这个职位。根据当时为圣保罗大学学生、现在是Rutgers大学名誉教授的JoseBarros-Neto的话来说,格罗滕迪克(和大学)做了特别安排,这样他可以回巴黎参加那里秋天举行的讨论班。由于巴西数学界的第二语言是法语,教学和与同事交流对格罗滕迪克来讲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通过去圣保罗,格罗滕迪克延续了巴西和法国的科学交流的传统:Schwartz之外,韦依、丢多涅和德尔萨都在1940和1950年代访问过巴西。韦依1945年一月到圣保罗,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秋天、他转赴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法国和巴西的数学交流一直延续到现在。里约热内卢的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MPA)就有一个促成许多法国数学家到IMPA去的法-巴合作协议。
在《收获与播种》一书中,格罗滕迪克将1954年形容为“令人疲倦的一年”(163页)。整整一年时间,他不成功地试图在拓扑线性空间上的逼近问题上获得一些进展,而这个问题要到整整20年后才被一种和格罗滕迪克尝试的办法完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感觉做数学是如此繁重!”他写道。这次挫折给了他一个教训:不管何时,要有几个数学“铁器在火中”,这样如果一个问题被发现很难解决,就可以在别的问题上下功夫。
现在为圣保罗大学教授的ChaimHonig,当格罗滕迪克在那儿的时候是数学系的助教,他们成了好朋友。Honig说格罗滕迪克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孤独生活,靠着牛奶和香蕉过日子,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数学中。Honig有次问格罗滕迪克他为什么选择了数学。格罗滕迪克回答说他有两个爱好,数学和音乐,他选择了数学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能更容易谋生些。他的数学天赋是如此显而易见,Honig说,“我当时相当惊讶他竟然在数学和音乐间犹豫不决。”
格罗滕迪克计划和当时在里约热内卢的LeopoldoNachbin一起合写一本拓扑线性空间的书,不过这本书从来没有实质化过。然而,格罗滕迪克在圣保罗教授了拓扑线性空间这门课程,并撰写了讲义,这个讲义后来由大学出版了。Barros-Neto是班上的学生,他写了讲义上的一个介绍性章节,讲述一些基本的必需知识。Barros-Neto回忆说当格罗滕迪克在巴西的时候说起过要转换研究领域。他“很雄心勃勃,”Barros-Neto说道,“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行动——他应该做些很根本、重要而又基础的东西。”
仿佛来自虚空(5)
新星升起
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每次塞尔会强烈感觉到某个陈述下隐含着的丰富意义,而这个陈述在字面意义上讲,无疑让我既不感到兴奋,也不觉得无味——而且他可以“传输”这种对如此内蕴丰富、实在而又神秘的实质的感知——这种感知在同一时候就是理解这个实质的渴望,以至看透它的本质。
《收割与播种》,第556页
格勒诺贝尔大学的BernardMalgrange回忆起当格罗滕迪克写完论文后,他宣称自己不再对拓扑线性空间感兴趣了。“他告诉我,‘这里面不再有东西可做了,这个学科已经死了,’”Malgrange回忆道。当时学生按要求需要准备一份“第二论文”,此文不必包含原创性的工作,其用意在于让学生展示对和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相隔很远的一门数学领域的理解深度。格罗滕迪克的第二论文是关于层论的,这个工作或许埋下了他对代数几何的兴趣的种子,而这将是他做出最伟大成就的地方。在巴黎完成格罗滕迪克的论文答辩后,Malgrange记得他自己、格罗滕迪克和亨利-嘉当挤在一辆出租车上去Laurent施瓦兹家里吃午饭。他们坐出租是因为Malgrange在滑雪的时候摔断了腿。“在车上,嘉当告诉格罗滕迪克他叙述层论时犯的一些错误,”Malgrange回忆说。
离开巴西后,格罗滕迪克1955年在堪萨斯大学度过,可能是受到N.Aronzajn的邀请[Corr]。在那里格罗滕迪克开始投入到同调代数研究中去。正是在堪萨斯他写了“关于同调代数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此文在专家圈子里面被非正式地称为“Tohoku文章”,由于此文发表在TheTohoku MathematicalJournal(《东北数学期刊》)上。此文是同调代数的经典,发展了嘉当和Eilenberg关于模的工作。也是在堪萨斯的时候,格罗滕迪克写了“带结构层的纤维空间的一般理论’一文,此文作为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的一个报告发表。这个报告发展了他关于非交换上同调的初步想法,此领域在后来他会在代数几何的架构下再次触及。
就是在这时候,格罗滕迪克开始和法兰西学院的让·皮埃尔·塞尔通信。他起初和塞尔在巴黎相识,而后来在南锡时又见过面。他们信件的精选在2001年出版了法文原版,在2003年出版了法英对照版[Corr]。这是一段长期而又硕果累累的交流的开始。这些信件显示了两个非常不同的数学家的深厚而又充满活力的数学联系。格罗滕迪克表现出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而它又常常被塞尔的深刻理解和渊博知识带回到地面。有时候在信中格罗滕迪克会表现出很令人惊讶的无知:比如说,有一次他询问塞尔黎曼zeta函数是否有无穷多零点([Corr],第204页)。“他的经典代数几何知识实质上等于零,”塞尔回忆说,“我自己的经典代数几何知识比他稍微好点,但好得不多,但是我试着去帮助他。可是…有这么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格罗滕迪克不是那种了解最新文献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依靠塞尔来了解目前数学界正在干些什么。在《收获与播种》里,格罗滕迪克写道,他学习到的大部分几何知识,除去他自学的外,全学自于塞尔(第555-556页)。不过塞尔不仅仅是教给格罗滕迪克知识;他能够将要点融会贯通,然后用一种格罗滕迪克发现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叙述出来。格罗滕迪克将塞尔叫着“引爆器”,一个提供火花,将导火索点燃,促使观点大爆炸的人。
确实,格罗滕迪克将他工作的许多中心主题都归因于塞尔。比如说,就是塞尔在1955年将韦依猜想用上同调的语言介绍给格罗滕迪克——这种语言在韦依最初提出猜想的时候是没有明显给出的,而它却正是可以吸引格罗滕迪克的地方(《收获与播种》,840页)。通过对韦依猜想做“凯莱”类比的想法,塞尔也促使了格罗滕迪克的所谓“标准猜想”的提出,此猜想更加一般化,而韦依猜想只是其中一个推论(《收获与播种》,第210页)。
在堪萨斯呆了一年后,格罗滕迪克在1956年回到法国的时候,在CNRS谋得了一个位置,大部分时间里他呆在巴黎。他和塞尔继续通信,并且经常通电话讨论问题。就在此时格罗滕迪克开始更深入地研究拓扑和代数几何。他脑子里“充溢着想法,”阿曼德-波莱尔回忆说,“我很确定某些一流的工作必将出自于他。不过最后(从他那里)出来的比我想象的甚至还要高出很多。这就是他的Riemann-Roch定理,一个相当美妙的定理。它真是数学上的一个杰作。”
经典形式的Riemann-Roch定理在19世纪中叶得到证明。它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紧致黎曼曲面上,由那些极点在给定的有限多个点上,且具有最多给定次数的阶的亚纯函数构成的空间的维数是多少?问题的答案就是Riemann-Roch公式,它将维数用曲面的不变量来表达——从而提供了曲面的解析性质和拓扑性质的丰富联系。弗里德里希-赫兹布鲁克(FriedrichHirzebruch)在1953年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进展,其时他将Riemann-Roch定理推广到不仅适用于紧致曲面,而且适用于复数域上的射影非奇异簇的情况。整个数学界都在欢呼这项伟业,它可能是这个问题的盖棺之语了。
“此时格罗滕迪克走了出来,说道:‘不,黎曼-洛赫定理不是一个关于簇的定理,而是一个关于簇间态射的定理’,”普林斯顿大学的尼克莱斯-卡兹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新观点…整个定理的陈述完全改变了。”范畴论的基本哲学,也就是大家应该更加注意的是对象间的箭头(态射),而不是对象自身,才刚刚开始在数学上取得一点影响。“格罗滕迪克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种哲学应用到数学上很困难的一个论题上去,”波莱尔说,“这真的很符合范畴和函子的精神,不过人们从没有想过在如此困难的论题上使用它……
如果人们已经知道这个陈述,并且明白它在说什么,可能别的某个人可以证明这个陈述。不过单单这个陈述本身就已经领先别的任何人10年时间。”
这个定理,其后也被GerardWashnitzer[Washnitzer]在1959年证明,不仅适用于复代数簇——基域特征零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任何本征光滑代数簇而不必在乎基域是什么。赫兹布鲁克-黎曼-洛赫定理即作为特殊情况推出。1963年黎曼-洛赫定理一个影响深远的推广出现了,它就是Michael Atiyah和IsadoreSinger证明的Atiyah-Singer指标定理。在证明的过程中,格罗滕迪克引入了现在叫作格罗滕迪克群的概念,这些群本质上提供了一类新型拓扑不变量。格罗滕迪克自己将它们叫做K-群,他们提供了由Atiyah和Hirzebruch所发展的拓扑K理论的起点。拓扑K理论接着又提供了代数K理论的源动力,这两个领域从此均是研究很活跃的领域。
Arbeitstagung,字面意思即是“工作会议”,是由赫兹布鲁克在波恩大学所发起的,其作为数学前沿研究的论坛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了。正是在1957年7月首次Arbeitstagung上格罗滕迪克讲述了他在黎曼-洛赫问题上的工作。不过令人好奇的是,这个结果从没有在他名字下发表;它出现在波莱尔和塞尔的一篇文章[BS]上(这个证明作为一个报告,后来也出现在SGA6中)。正当他在1957年秋访问IAS(高等研究院)的时候,塞尔收到格罗滕迪克的一封信,里面包含了格罗滕迪克证明的概要([Corr]中日期为1957年11月1日的信)。他和波莱尔组织了一个讨论班来试着理解这个定理。因为格罗滕迪克正在忙很多别的事情,他建议他的同事们将讨论班记录下来发表。不过波莱尔推测可能有别的原因让格罗滕迪克对将证明写下来不感兴趣。“格罗滕迪克主要的哲学思想是数学应该被简化为一系列很小而又很自然的步骤,”波莱尔说,“只要你还不能这么做,就说明你还没有理解里面真正的含义…他的黎曼-洛赫证明使用了一个小窍门,uneatuce。因此他不喜欢这个证明,所以也就不想发表它。正好他有别的很多事情要做,他对将这个窍门写下来没有兴趣。”
这并不是格罗滕迪克最后一次革命化一个学科研究问题的观点。“这样的事情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发生,他会去考虑有些别人已经花了很久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100年的时间研究过的问题……
最后他完全转变了人们当初认定的这个学科告诉我们的东西。”卡兹评论道。格罗滕迪克不仅会去解决很困难的问题,他还会去继续研究引起这些问题的问题。
仿佛来自虚空(6)
新世界大门开启

(我最后终于)意识到这种“我们,伟大而高贵的精神”思维方式,在一种特别极端和恶意的形式下,从我母亲的孩提时代开始,就让她情绪易于激动,并支配着她和别人的关系,让她总是居高临下,带着常常是倨傲甚至于轻蔑的怜悯来看待别人。
《收获与播种》,第30页
根据Honig的说法,格罗滕迪克的母亲在他呆在巴西的时候,至少有部分时间也在那里,尽管Honig说自己从没有见过她。我们不清楚她是否跟随儿子去了堪萨斯。当1956年格罗滕迪克回到法国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住在一起了。在1957年11月于巴黎写给塞尔的信中,格罗滕迪克询问塞尔他是否可以租下塞尔正要搬出的一间巴黎公寓。“我想给我母亲租住这个公寓,她在Bois-Colombes过得不怎么好,而且觉得特别孤独,”格罗滕迪克这样解释[Corr]。事实上,他母亲在这年底就去世了。
格罗滕迪克的朋友们和同事们都说当他谈及父母双亲的时候总是充满景仰,几乎到了吹捧的地步。在《收获与缝补》一书中,格罗滕迪克也表达了对他们的深厚的孺慕之情。多年里他在办公室里挂了张很醒目的他父亲的肖像,此画是LeVernet集中营里的难友描绘的。据PierreCartier的描述,这幅肖像画描绘了一个剃着光头、双目“炯炯有神”的男人[Cartier1];很多年里格罗滕迪克自己也剃光头。根据Ribenboin的话,汉卡·格罗滕迪克对她的杰出儿子感到非常骄傲,反过来他也有一种对母亲特别深厚的依赖。
她过世后,格罗滕迪克经历了一段时间来寻找自我,期间他停止了所有的数学活动,还想过去成为一位作家。数月后,他决定重返数学,去完成和一些他已经开始发展的想法相关联的工作。这一年是1958年,根据格罗滕迪克的话,这一年“可能是我数学生涯最多产的一年。”(《收获与播种》,第24页)这个时候他开始和一位叫Mireille的妇女同居,他将在数年后与她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乔安娜、马修和亚历山大。Mireille和格罗滕迪克的母亲曾经过往甚密,并且据熟悉他俩的人说,她比他大了不少。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约翰-特德(John Tate)和他当时的妻子凯伦-特德(KarenTate)1957-1958学年在巴黎度过,在那儿他们首次见到格罗滕迪克。格罗滕迪克根本就没有表现过那种他归因于母亲的倨傲。“他很友好,同时相当天真和孩子气,”JohnTate回忆道,“很多数学家都相当孩子气,有时不通世务,不过格罗滕迪克犹有甚之。他看上去就那么无辜——不工于心计,不伪装自己,也不惺惺作态。他想问题的时候相当清晰,解释问题的时候非常有耐心,没有自觉比别人高明的意思。他没有被任何文明、权力或者高人一等的作风所污染。”KarinTate回忆说格罗滕迪克乐于享受快乐,他很有魅力,并喜欢开怀大笑。但他也可以变得很极端,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容不得半点灰色地带。另外他很诚实:“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她说,“他不假装任何事情。他总是很直接。”她和她的弟弟,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阿廷(MichaelArtin)都觉察到格罗滕迪克的个性和他们的父亲埃米尔-阿廷(Emil Artin)很相似。
格罗滕迪克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想主义想法”,KarinTate回忆说。比如说,他不允许在他屋子里有地毯,因为他坚信地毯只是装饰用的奢侈品罢了。她还记得他穿着轮胎做的凉鞋。“他认为这妙极了,”她说,“这些都是他所尊敬的事务的象征——人需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在他的理想主义原则下,有时候他可能变得特别不合世宜。在格罗滕迪克和Mireille1958年首次访问哈佛之前,他给了Mireille一本他喜欢的小说让她来提高她相当贫乏的英语水平。这本小说就是MobyDick。
新几何的诞生
按照三十年后的后见之明,现在我可以说就是在1958年,伴随着两件主要工具,概型(scheme,它代表旧概念“代数簇”的一个变形)和拓扑斯(toposes,它代表空间概念的变体,尽管更加复杂)的苏醒,新几何的观点真正诞生了。
《收获与播种》,第23页
1958年8月,格罗滕迪克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个大会报告[Edin]。这个报告用一种非凡的先见之明,简要描述了许多他将在未来12年里工作的主题。很清楚这个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证明AndreWeil的著名猜想,其揭示了代数簇构成的离散世界和拓扑形成的连续世界的丰富联系。
在这个时候,代数几何的发展非常迅猛,很多未知问题并不需要很多背景知识。起初的时候这个学科主要是研究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