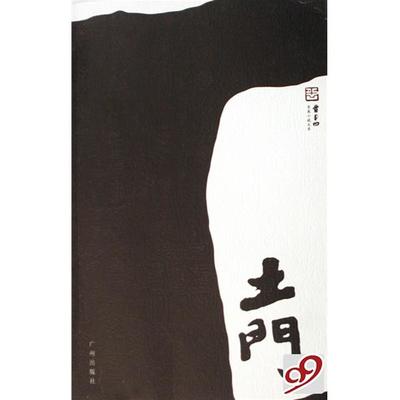《围城内外:西方经典爱情小说的进化心理学透视》序言(节选)
(《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学》丛书之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真诚的读者,你现在就要开始阅读我这本《禁果的诱惑:西方经典爱情小说的进化心理学解析》了。为了有助于你更好地阅读本书,我得先交待一下几个关键性概念,这就是:“婚外恋”、“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和“进化心理学解析”。然后,我再概括一下本书的要旨:经典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与当代进化心理学的成就之间拥有完美的对应性和一致性。而本书写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试图揭示这二者之间有哪些对应性和一致性,其奥妙又在哪里。
婚外恋与“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
正如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名言——“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样,我在这里续补一句:既然有婚姻,必然就有婚外恋——这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条“真理”。
“婚外恋”,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外遇”(俗语还有“偷情”、“私通”、“通奸”、“越轨”等),是男女两性关系、特别是两性爱情关系的1种重要而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本书中,婚外恋有其专有的、特定的所指:对男性来说,是指拥有婚姻关系的男性与另一任意女性所发生的性爱关系——不管这个女性是有丈夫,有性伴侣(或同性伴侣),还是单身,在这里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这位男性是处于婚姻关系之中的,这是1个既成的事实;而他与不是婚配对象的任一女性发生性关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能叫婚外恋。很显然,这一界定对女性同样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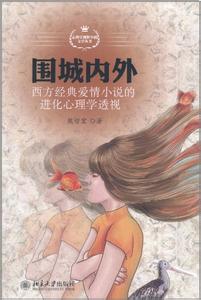
婚外恋,既是1种心理状态,又是1种外显行为。而在“行为”的意义上,国外的进化心理学家把它叫做“短期择偶”(short-termmating),这主要是从两性关系持续的时间长短来看的。因为它不像婚姻关系那样能维持很长的时间——至少是相对较长的时间。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闪电般”短暂的婚姻,据说美国的大歌星布兰妮曾有过五个小时的婚史,但充其量不过是搞笑或恶搞。婚外恋一般可长可短,但“短”也有1个时限,那就是它不短于“一夜情”或偶尔偷腥。从心理机制上说,婚外恋与一夜情或偶尔风流是不同的。
明确了婚外恋的概念,“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或简称“婚外恋小说”)就好理解了。笼统地说,凡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婚外恋为题材的小说,都可以冠之以这一名称。但本书有独到的限定——至少在文学合理性的意义上,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或标准的才属于婚外恋小说范畴:(1)小说的中心(或核心)主题是婚外恋;(2)小说中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婚姻关系中,其故事情节也始终围绕主人公的偷情行为来展开;(3)小说反映了主人公对“禁果”——为社会的道德、法律、习俗、体制、习惯和文化传承所不容——的特有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恋爱中独有的心理冲突(即不同于一般的爱情心理冲突);(4)主人公的这种爱情多半——而不是全部——带有悲剧性的色彩或结局。
在西方文学史中,能满足以上标准的小说不计其数。初略地点一下就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金碗》(The GoldenBowl)、冯塔纳(TheodorFontane)的《寂寞芳心》(Effi Briest)、左拉的《家常菜》(Potbouille)、哈代的《还乡》、亨利·米勒的《性爱之旅》(SEXUS)、沃勒的《廊桥遗梦》、阿娜伊丝宁的《亨利和琼》、约翰·霍克斯的《血橙》、保罗·鲍尔斯的《情陷撒哈拉》,等等。
我把西方最经典的婚外恋小说归属于如下5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霍桑的《红字》和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我不排除这种选择带有个人偏好的意味,但它们都最能满足我关于婚外恋小说的界定,至少在西方文学史上极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进化心理学与“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
婚外恋心理,是科学的爱情心理学中的1大难题。除了它的普遍性、隐蔽性和不可避免性等科学上的限度之外,还有1个重要的文化差异,甚至是“意识形态”——即为1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所认可和维护的价值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婚外恋一直被简单地斥责为“第三者”,把它归属于道德的范畴。幸好,“进化心理学”的诞生,为我们使婚外恋的研究成为科学、并使我们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
婚外恋的心理机制:“性选择”和“亲代投资”理论。
进化心理学对婚外恋的解释,得益于其2个核心理论,即达尔文的“性选择”和特里维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性选择”(sexualselection)理论主要关注动物因求偶行为而产生的1种心理机制(又叫“适应器”,或“心理模块”)。性选择主要有2种运作方式。第1种叫“同性竞争”。这是指同一性别的成员之间的竞争,主要竞争目标在于与异性的交配机会。例如,两只雄鹿用鹿角来打架,新的“猴王”为了让母猴发情(获得交配机会)而杀死前任猴王的孩子,就是同性竞争的典型例子。第二种方式是“异性选择”,也叫“择偶偏好选择”:如果某种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他(她)们所想要的,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就更有可能获得配偶;而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则得不到配偶。达尔文举的1个例子是,人类的女性远祖是依据男性脸部毛发的样子有没有魅力,来挑选异性伴侣的。结果是,男性的身体特征如胡须和肌肉——能显示“阳刚之气”——便被选择出来。同样,通常女性比男性更爱打扮,她们不惜用华丽的服饰、飘逸的长发、性感的口红、高耸的前胸、细长扑闪的睫毛等来彰显个性,也正是男性长期择偶偏好的结果。因为男性更喜欢选择年轻、漂亮、极具性魅力的女性作为配偶。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为我们解释人类择偶的心理机制的进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1972年,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特里维斯(RobertTrivers)在达尔文的基础上,进1步提出了他著名的“亲代投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男性对随意的性关系——或“多样化的性伴侣”——进化出了比女性更大的欲望(lust)。之所以进化出了这样的“欲望”,主要是因为男性对子女的投资比女性要小。
人类作为有性繁殖的物种,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求偶或择偶——找到1个配偶(像通常说的,男人要“讨个老婆”,女人要“嫁人”),因为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资源和时间。在此过程中,雌雄两性各自所做出的贡献,严格说来是不对等的。首先,精子和卵子的生产和消耗就有很大差别。男性可以生产无以计数的精子;相对而言,卵子却要珍贵得多(女性一生中生产的卵子数量比较固定,约400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