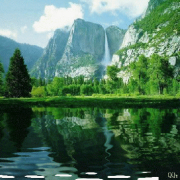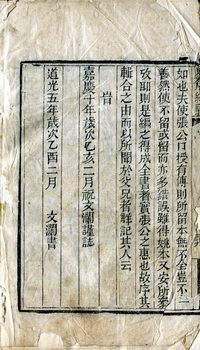二、“神无方”而可知
“道”是“阴阳”的原因,也是“神”的原因。知“阴阳”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也可以知“神”。《易传》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无方”就是没有方所,即在空间上不确定。“神”是对生成与变化发展的概括,而生成变化发展就表现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之中,这种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确定的,不停驻于某一时段,也不存在于某一方位。天地万物的变化无穷而不定,但具有其内在的根据和必然,即不离于“道”,“神”由此而可以把握无穷之变化。“神”对于生成变化发展的概括是穷尽的,而且具有明晰性,范围分明,内涵此过程而不超出此范围。 “神”不仅内涵生成变化发展的过程,也内涵因“阴阳”二性质的相感与相峙而引起的潜在因素向现实的转化。潜在因素的现实化过程表现出“神”的另一品性——“诚”。“诚”是对于现实以及现实的转化过程的如实反映。“神”与现实具有一致性,宇宙怎样生成,怎样发展变化,“神”便怎样反映之,没有任何偏差。这与《中庸》所讲的“诚”具有一致性。《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道”的运行是真实无妄的,和“阴阳”二性质的相感相峙一样,使宇宙生生不已而达到恒久。“天道”著于四方则表现出博大与厚重的品性,此品性的外化作用高大而光明,从而可以覆万物,载万物,成万物。“天道”对于万物的覆、载、成的“不贰”,就是“诚”。《中庸》此段所讲的“诚”,同时就是“神”之“诚”。 “神”虽然“无方”,但却因“诚”而具有现实性。这里,“神”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用于概括的范畴,和“道”一样,它更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和天地万物的存在一样现实,而是抽象的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这种存在虽是超越的,但它是具体化了的抽象,所以具有现实的意义。“诚”就是抽象而超越之“神”的具体化。在“无方”与“诚”之中蕴含着“神”的宽厚博大,发散于外就有像日月一样释放的光明,所以“神”而“明”。“明”既是“神”的品性,又是“神”的功效。“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神”以“明”“妙”万物,而且形于言,在对于万物的主动中显现出其品性与功效。“神”的功效就在于“阴阳”二性质的相感与相峙,“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彖》)。阴阳二性之“所感”,包括了天地万物之“情”。宇宙的所有过程的发生有其内在的规律,观“所感”,就可以把握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律,也就可以把握“神”的功效。“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上》)“感”是二性质的动态化,静态则表现为“寂”。 “寂”与“感”不分为两段,“寂”就在“感”中,“感”也在“寂”中。“寂”,则有碍而不通,表现出天地万物之形。“感”,因二性质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就可以达到“通”。“通”是因“变”而成,“感”而“通”就可以无穷止地发展,从而达到“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因此,观“神”就可以使“天地万物之情”自然显现出来。
三、由“察微研几”到“穷理尽性”
《易传》对于宇宙意义给予探察的真正目的,不仅仅在于去认识宇宙,更在于为人寻找存在的依据。《易传》将宇宙对象化,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人在仰观俯察中一步一步将对象中“有利于自己的可能性作为目的来指导行动、来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从而使对象进入价值的领域。所以,“神”同时具有价值意义。“神”不仅是价值的承担者,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体现者。这在根本上与儒家的人道主义相吻合。儒家从孔孟开始就讲人的自我地位的确认。他们所讲的确认,是以道德理性来实现。人用道德理性来认识宇宙认识自己,在认识中不断对本然的宇宙与本然的“我”打上人的烙印,使其不断具备人的印迹,以有用于“人”而价值化,同时显现人的本质力量(道德的完成和实现)。在此过程中,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人的精神力量(即或道德力量),比如孔颜之乐。 《易传》认为“神”的价值意义是怎样体现的呢?首先,人通过“察微研几”对“神”之功效——“感”进行认识。“感”所引起的变化本身是细微的,在感性的基础上难以把握。《易传》并不否认感性的认识。认为人应该对于细微的变化进行体察,在体察当中进行理性的反思,以把握“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几”就是微。“几是有无之间,你说它有,它未表现出来;你说它无,它又已经发动了,所以在有无之间。”理性对于“几”的反思并不表现在逻辑推理之上,而是靠直觉的能力。直觉能力的形成与发生作用,需要长期体察的积累,积累到一定时候,豁然通明,从而感知到“几”。这就是《易传》所讲的“研”。体悟到“几”(或“感”)只是“神”的价值意义的前提。价值的形成是双向的,既要实现自然的人化,还要实现人的自然化。“作为价值的主体,人总是首先要经历一个从自然到人化(社会化)的过程,唯有超越了自然,人才能获得内在的价值(使自身成为目的)。”同时,人的意志与行为达到自觉地与自然相符合。所以,“神”的价值化,应在人当中得以体现。人在“察微研几 ”中以“神”为范型而效法之,遵循“神”的内在趋向而不违背。《易传》认为,圣人在仰观俯察中取象制器,作八卦而“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就是在效法“神”的品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下》)人在对于“神”的效法中,期望获得更多的自由,从而改造本然之自然,使本然之自然中的潜在具有现实化的可能性,并促使可能性走向现实。“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下》),这种“神”的价值化的体现是以道德(即“神”之“诚”)为先在的。“要皆极深研几,直凑事物之里,洞开生化之源者也。亦皆提醒人之德性之真生命而直证宇宙之真生命者也。”“是故穷神即是知化,知化即是穷神。”“‘穷神知化’者即是德性生命之证悟,亦是发之于德性生命之超越的形而上之洞见。” 人的行为自觉地与“神”相符合,同时意味着“神”的价值意义的最终完成。自觉地与“神”相符合,不仅仅表现在人对于“神”的效法和把悟上,更在于“穷理尽性”。也就是以理性的直观通透“神”之理,从效法“神”之理开始逐步实现理性的自律,进而使自律走向自然而然,以致达到自觉,并在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对于精神本体即“性”的建构。将“神”作为“尽性”的途径,也同时成为了建构精神本体的直接前提。“性”非强力所能致,而是“穷理”的“功夫所至”。人的精神本体得以建构,那么人就实现了其自然化。此时,人便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可以“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文言》),最终使“神”的价值意义得以完成和实现。 综上所述,《易传》中的“神”是从自然意义上讲的,又是具有超越性的,而且具有价值意义,因而与宗教所讲的“神”截然不同。《易传》对“神”的阐述,既是对儒家价值体系的继承,又有对儒家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当然,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说《易传》中的“神”不包涵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易经》之学即是由蓍草之布算而见到生命之真几”,其带有神秘色彩的“蓍算”最终指向是人,是对于生命及其价值的体悟。总之,《易传》之“神”是在人学意义上建立的范畴,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易传》的大致哲学倾向。
王树人:“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
“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王树人(老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由《周易》所开启的“易道”之思,在巫术神秘的外衣下,凝结着中华早熟、深邃、博大、雄浑的文化底蕴。《周易》其所以能包容这样的文化底蕴,乃根源于它的“取象”和“象以尽意”的思维特征。这种发源于上古而成熟于《周易》的“象思维”,一旦具有合适的理论形态,如同形成《周易》六十四卦体系这种理论形态,就会对于“原发创生”的思想文化发展,发挥巨大而长远的影响。虽然《周易》的巫术外衣,使之常常为迷信者所利用,但是中国历代的大思想家都能透过巫术的外衣,借助《周易》原创之思的启迪,推动中华思想文化向前发展。当代的“易道”研究,不仅受到人文学者的关注,而且还受到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形成中国一个文化的热点。同时,对《周易》的“易道”研究,在西方自受到莱布尼兹重视以来,也引起相当的关注。但是,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周易》所蕴含的原创之思这一重要内涵,缺乏研究。本章的研究,拟尝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早熟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几乎可称为周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如此,就它所具有的原创性内涵而言,《周易》还是启迪中国后来思想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源头。对此,清代《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这样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一)在这一则对于《周易》具有代表性的评价中,可以看到,编撰《四库全书》时代,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实学”的特点。在“无所不包”所具体例举的学科中,大多是“实学”,而形而上之道,则仅以“逮方外之炉火”一句带过。其中触及到而没有深究的问题,则在于指出所有学科门类“皆可援《易》以为说”。何为“援《易》”?如何“援《易》?”这就涉及“易道”的本真本然,或者说涉及如何理会“易道广大”。 一、“易道”之“象” 与西方形而上学之道从“实体”出发相比较,“易道”则是从非实体的“象”出发。非实体的“象’夕构成“易道”体系的始源性范畴。理解这一点,是关键,非常重要。如《系辞传》所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又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就是说,“易道”无论多么广大深邃,都有得以生成的始源。这个始源,就是“象”。或者说,“易道”始于“象”,源于“象”。没有“象”,就没有“易道”。就是说,象在《周易》中具有决定一切的重要性。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易道”之“象”?在《周易》由卦爻辞筑象所显示的“象”中,已经具有非常丰富的层面。例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草木、飞鸟、走兽等情况;社会的农耕、狩猎、商贸、战争等事态;不同性别、等级、年龄的男女,其婚、丧、嫁、娶、生、老、病等人生百态;在生理上人的身体诸有机组织;人在现实和梦中喜、怒、哀、乐等情感表现;通过祭祀等活动人对精神的不同追求,等等,差不多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富于诗意的描述。可以说,所有这些具象、意象、联想之象,都与“易道”之“象”相联系,也都不同程度地显示“易道”之“象”。但是,却都还不是“易道”之“象”。如果承认“生生之谓易”这条对“易道”的基本解释,那么这些由卦爻辞筑象所展现的自然、社会、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等万象,不过是“生生”中的第二“生”即“被生”之生象,而“易道”之生,则属于第一生的“原生”之生象。这种“易道”之“象”,作为源头的非实体之“象”,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原发创生性”或“原发生成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实体”作为“源头的构成J比”,形成本原性的区别。就是说,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在本原上就是不同的。西方的“实体论”把种种作为始基的“实体”,当作宇宙及其所包含的具体事物之最终基源。如德漠克里特的“原子”、毕达戈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莱布尼兹的“单子”,等等。这些“实体”都是不变的。就构成的宇宙之运动而言,也只能最终归结为外在的“神力”推动。即使斯宾诺莎的“实体”自己运动,但说到最后,“实体”本身也是不变的。所谓“源头的构成性”,就是由这种不变的“实体”所决定。概念思维诉诸静态规定和分析的方法,也源于这种实体论。相反,所谓“易道”之“象”,其“原发创生性”,恰恰表现在它本身是非实体的,并且总是处在变化的动态中,因而它能原发的“生生不已”,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思维之为“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作为“原生”之“象”这种“易道”之“象”?没有别的入手处,只有从《周易》六十四卦的卦交符号系统入手。因为,“易道”之象,都是借助这个符号系统展示的。在这个系统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阴阳爻。所有六十四卦,都是由阴阳两爻不同重叠和变化所组成的。其中,六爻组成卦象,不同组成的六爻,形成不同的卦象。而每一爻又因在变化中所处的时空位置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爻象。实际上,六十四卦的卦爻之象,都不是静止固定之象,而是阴阳爻“流动与转化”之象。但是,阴阳爻又源于何处?这个问题涉及“易道”的根本即“太极”。就是说,阴阳爻源于“太极”。如《周易大传》所指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大传》这个说法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概念思维的规定。因此,这里需要的,是领会其所描述的意蕴。可以说,其中最基本的意蕴就是前述的“生生”运动及其千变万化。就是说,六十四卦爻之象,其所以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能展现出无穷的变化,能统摄自然、社会、人生万象,就在于有“原生”的“太极”之象,即“原生”的“易道”之“象”,或者说,由于有这个“原象”作“原发创生”的推动。 在这里,“生生”、“原生”、“原发创生”三种描述性范畴,是相互有机关联的。“生生”中前一个“生”,为“太极生两仪”之“生”,有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之“生”,是谓“原生”。后面一个“生”,则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生”,亦如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生”,是谓“被生”或“属生”。“原发创生”,则是前后两种“生”有机关联的描述。那么又当如何领会“生”的本真本然?从根本上说,“生”乃是一种创造。由此,接着需要发问的问题就是:何为创造?如果对此作形上学的回答,那么创造似乎可以说是:“无中生有,有中见无。”有如一位真正的画家所创作的“画作”,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一个”。这幅画作,是“无中生有”,不是“鸡生蛋”,也不是“蛋生鸡”。但是,一旦它作为“有”而存在,这个“有”又能从中见“无刀。就是说,这个“有”的意蕴,并不限于已“有”,而是为新“有”的出现,留有“生生”的“无”。例如,观赏者在欣赏这幅画作时,正因为它“有”中之“无”,使观赏者能欣赏出画作者所没有赋予的东西。也就是说,观赏者因其“有”中之“无”,而能继续“创生”。如果承认莱布尼兹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是一个真理,即承认“非同一性”的真理,那么世界上任何“生”出来的东西,就都不可能不是“创生”的“这一个”。
二、“象数”与“义理”的分野 在易学史中,产生了象数派与义理派及其论争。一般而言,象数派繁荣和兴盛于汉代。义理派则兴盛在所谓王弼“扫象”之后的唐宋时代。这种论争一直持续到近代,乃至现代。就进入中国现代而持续争论的两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争论的焦点乃在于作为象数的卦爻与作为卦爻辞的系辞哪个更根本更重要。例如,作为象数派易学代表人物尚秉和先生,他在评述《系辞传》的“立象以尽意”时指出:“盖天下的万事之意,无不包含于《易》象之中,故能尽意。此言象之本也。”他还在评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时指出:“夫曰观象系辞,则今之《易》辞,固皆古人瞪目注视卦象而为者也。《易》之卦爻辞,既由象而生,后之人释卦爻辞,而欲离象,其不能识卦爻辞为何物,不待智者而决矣。朱子云:‘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虚理易差。’”(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左传、国语易释之绪言》)应当说,尚先生认为象数作为《易》之根本,起决定作用,是符合“易道”之本真本然的。因为,“易道”之得,首先在“观象”,而且是由“象”如何来决定“系辞”如何的。那么,是不是说义理派的观点就没有道理或不重要?也不是。且看义理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所言:“一部《周易》的关键全在卦辞和爻辞上,没有它们就是有了圣王画卦和重卦也产生不出多大意义,没有它们就是产生了素王也做不成《易传》。所以,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而古今来聚讼而决的也莫过于卦爻辞。”(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确实是,虽然是“观象”并依据“象”如何来“系辞”的,但如果当时“观象”后的“系辞”,只是口头语言而未留下文字记载,那么就会如顾颉刚先生所预料,卦爻就成为无法解开的死符号。就此而言,顾先生强调卦爻辞在揭示卦爻象数之迷的重要性和决定作用,也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在语言文字产生前后,人类已经和不断地发明着各种符号。但是,所有这些符号都不能与语言文字符号相比。就是说,对这些符号的揭示和说明还必须依赖语言文字。亦如《周易》的卦爻符号,其内涵必须有卦爻辞这种语言文字来揭示和说明。然而,今天看来,这种争论似乎还没有深入到“易道”的本真本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争论的双方都各执一端,都没有把握“生生”、“原生”、“原发创生”这个“易道”之本真本然的角度,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卦爻符号与卦爻辞符号,从而也就不能看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显然,从“易道”本真本然的角度看,所谓“观象系辞”,看似两回事,但都属于“原发创生”的有机统一过程。前述所引“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实际上所表明的就是,无论“观象”还是“系辞”,都是“生生”中的“象的流动与转化”。“观象”在于“观”出“卦爻”之“象”,“系辞”也不是判断推理,而是以语言文字“筑象”来显示作为“易道”的卦爻之意。
三、“太极”之“象” 可见,“易道广大”之“大”,其所以能统摄自然、社会、人生万象,就在于“易道”之“象”是作为“太极”的“原发创生”之“象”。对于“太极”,宋代周敦颐作了进一步深刻的诠释:“无极而太极”。这种“无极而太极”之“象”,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这种“太极”之“象”,“无极”之“象”,“大象无形”之“象”,都是“无物之象”。这样,就在“太极”或“无极”作为“原发创生”这个“易道”根本问题上,提出了“无”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太极”和“无极”的本真本然,就在于“无”。可以说,“太极”和“无极”作为“易道”之根本,正因其“无”而能“原发创生”,也正因其“无”而能使“易道广大”。这种“无”,不是数学上化整为零的无,不是常识中存在物消灭后的无,而是超常的具有无限生机的“有生于无”之“无”,因而是无所不生之“无”,“至大无外”之“无”,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包之“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到魏晋时期曾经发生“崇无”与“贵有”之争。这种争论,把道家老子和庄子提出的“有”与“无”的问题,进一步明朗化和深刻化了。但争论双方各执一端的立场,却把在道家那里原本统一的“有”与“无”加以割裂了。“无”蕴含“有”,反之,“有”也蕴含“无”,“有”与“无”具有同一性。这个问题,是概念思维,特别是形式逻辑所不能理解的。即使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虽然指出和承认这种同一性,但由于缺乏整体直观性,以及仍然处在对象化思维模式之中,所以也不能真正领悟这里“生生”的“原发创生”意蕴。 在所谓王弼“扫象”之后,易学的义理派在现代以前,都是从儒家立场出发批评象数派观点的。义理派主要是在将卦爻辞儒家化的诠释中发展儒学,所以他们称赞王弼“扫象”。但是,他们对于王弼“崇无”的道家倾向又加以否定。这一点,在《四库全书》的编撰者那里也有表现。例如在评述象数派与义理派之争时他们是这样说的:“《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此中不难看到,编撰者所表现的,就是儒家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入于祥”的象数迷信和陈抟、邵雍图解的虚玄持批判态度,此外并不完全否定象数。并且认为,“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就是说,汉儒仍保持着对《易》的古风遗韵。问题在于,对王弼的态度。所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前半句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于“入于祥”迷信的象数,“尽黜”得对。但是,把象数都“尽黜”,则不对。而对后半句,“说以老庄”,从儒家立场出发,则是完全否定的。然而,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领会王弼“黜象”和“说以老庄”的本真本然。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黜象”,在王弼那里,确乎是针对象数研究“入于祥”的问题而发,并不是完全黜象数。因为,在王弼易学著作《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中,都还包含对象数给以肯定和积极评价。提出所谓“象以尽意”和“尽意莫若象”等等。然而这种积极评价,正是与“说以老庄”联系在一起。老庄的“道”实质上,就是“大象无形”之“象”即笔者所说的“原象”。而这种“原象”的本真本然,就是“无”。应当说,老庄的“道”或“大象无形”之“象”,与《周易》的“太极”、“无极”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以老庄”,不但没有离开“易道”的本真本然,而且是一种深化。这种深化,就表现在对“易道”根本即“无”这个问题,被更加明确地提出来了。 关于由“无”所开显出的“原发创生”,提出两重意义。其一,这种“原发创生”是一种大视野,因其打破了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即概念思维方式,从而,能进人整体动态直观的“象思维”之大视野。其二,这种“原发创生”还是一种精神虚灵开悟的崇高境界。这后面一点,更是对象化的概念思维所不问也不知道的。在这里,也许最富挑战性的问题还在于:何以为“无”以及“无”何以能开显出“原发创生”的视野和境界?在对涉及这个问题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是老子最先也最明确地提出:“有生于无。”此后,《周易大传》的作者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到魏晋时期,“崇无论”者王弼,明确地把“无”作为本体。王弼这种解释“易道”以“无”为本体的思想,影响深远,一直到唐宋,许多重要易学著作,都接受和传承王弼这一思想。但是,所有这些以“无”为本体的论说,对于何以为“无”的问题,以及“无”何以能开显出“原发创生”一切这个问题,都未作出说明。或者视之为当然,或者认为不可说,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 “无”之“道”真的不可说吗?虽然老子认为不可“道”说,但是老子不还是说了五千言吗?因此,对于“无”,在今天看来,似乎应当区分在什么意义上不可说,在什么意义上又可说。首先,“无”之“道”不能对象化,或者说不能主客二元。因此,在概念思维的意义上,不可说。但是,在整体动态直观的“象思维”意义上,却可以说。这时所说的语言或写出的文字,不是概念思维意义上的语言文字,不是对象化的规定,而是以语言文字筑象,如同“文字禅”。因此,对这种诗意描述的语言文字,就不能像概念思维意义上的语言文字那样去抠字眼,去作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而只能去体悟“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了。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与这种“无”之“道”在体悟中沟通。人的生与死构成人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无时不与宇宙整体在体悟中沟通。在寒暑冷暖的感受和反应中,在酒醉如梦如痴的言谈中,在观花赏月的审美感受和愉悦中,在情爱甜蜜感受的忘乎所以中,在一切物我两忘的痴迷创造活动中,即凡是超越理性常规常识的感悟性活动,可以说,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与“无”之“道”相通。而诗人和艺术家,其所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恰恰是他们能作出超越理性常规常识的感悟,并能在与他人这种感悟沟通中完成他们的诗作和艺术作品的创作。
四、“无极”之“无” 写到这里,所作的讨论,可以说,都还在何以为“无”以及“无”何以能开显出“原发创生”的视野和境界这两个问题之外。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只要说明了何以为“无”,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前面,事实上已经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指引,即指出“无”中蕴含“有”和“有”中蕴含“无”。不仅如此,所谓“无”中蕴含“有”之“有”,还是“大象无形”之“大有”。而这“大有”之“大”,又大到“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是“无”呢?应当如何领悟这个“无”呢?似乎可以这样来领会,就是说,虽然这个“无”含有“大有”,但还没有“创生”出来。作为“太极”,还没有“生两仪”,更没有其后之“生”。作为“道”,还没有“道生一”,也没有其后之“生”。所以,“太极”和“道”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无”,而非具体事物消灭后的无,也不是数字消减为零的无。勿宁说,这种“无”,如同宇宙的“黑洞”,具有被压缩和凝结的巨大质量和能量,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了。正是这种显示为“黑洞”的“无”,一旦象“太极”,“是生两仪”,或象“道”,“道生一”,即发生“大爆炸”,那么压缩和凝结其中的巨大质量和能量及其时空,就会展现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宇宙。可见,“太极”和“道”之“无”,就如同这“黑洞”之“无”在“大爆炸”前那种“无”的状态一样。由此可知,“太极”和“道”之“无”,其所以能在精神上开显出“大视野”和“高境界”,就在于这种“无”蕴含有压缩和凝结的巨大的精神质量和能量,或者说,“无”也可以类比为精神的“黑洞”。对于人来说,如若进人这种“无”的视野和境界,乃是一种长期无形的修养和涵养,是巨大精神质量和能量的压缩与凝结的结果。显然,开悟的显现,只能是在这种修养和涵养之后。 由此可知,“易道广大”之“大”,乃在于“易道”以“太极”为本体构成了宇宙的生成论体系,同时,也以“太极”为本体构成了精神世界的生成论体系。“太极”或“无极”之“无”,是“大象无形”的“无”,蕴含着压缩和凝结的巨大无比的质量和能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宇宙的星系和精神世界的星系,都由“太极”或“无极”之“无”孕育和创生,是谓“原发创生”。这种“无中生有”的“原发创生”论,已经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解释宇宙生成的“大爆炸”理论时得到认同。至于在精神世界,其“苟日新”而“日日新”创造,则无时不在印证这种“原发创生”论的深刻合理性。前引所谓各门学科都“援易以为说”,但真正有创造性的“为说”,都不是套用《周易》外在形式或模式,而是深入领会其“原发创生”理思。
蕭進銘:三才思維與太陽系生態系統觀初探── 以《易傳》、《禮記》及《黃帝內經》為討論核心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 (《素問· 氣 交變大論篇》)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聖人作則, 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禮記·禮運》)
【內容提要】 本文之主要目的,係在對中國古代三才思維的源流、內容、認識論的基礎以及其現代意義,做一全面性的探討。筆者以為,這一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抑或更早的整體思維模式,在中國的軸心時代期間,經過重新的詮釋及改造,而被完整地繼受下來。其主要的精神,係把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視為是密切相關且無法被割離的統一整體來加以認識及思索。在《易傳》、《內經》及《禮記》等書當中,對此三者間之具體的關係,皆有著十分詳實的論述及剖析。對於這樣的一些內容,若以現代的觀念、語彙來加以詮釋,實可被視為是以整個太陽系做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看待的生態學式思維。此一思維,對於今日在思考人與自然關係以及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時,將極具參考價值。
【關鍵詞】 三才思維、氣、象、太陽系生態系統
壹、序言
中國古代的文化、哲學之具有有機整體及連續統一等特質,海內外的學者已有不少的論述及闡發,比如張光直、牟復禮(F.W.Mote)及杜維明等氏之如下言論,便是其中之極具代表性的說法:
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可以說是最為令人注目的特徵,是從意識型態上說來,它是在一個整體性的宇宙形成論的框架裡面創造出來的。用牟 復禮的話來說,真正中國的宇宙起源論,是一種有機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論。就是說,整個宇宙的所有組成部分,都屬於同一個有機的整體,而 且它們全都以參與者的身份,在一個自發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杜維明進一步指出,這個有機物性的程序,呈示三個基本的主題: 連續性、整體性和動力性。存在的所有形式,從一個石子到天,都是一個連續體的組成部分。……既然在這連續體之外一無所有,存在的鏈子便從不破斷。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對物事之間,永遠可以找到連鎖關係。中國古代的這種世界觀──有人稱為『聯繫性的宇宙觀』──顯然不是中國獨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會中廣泛出現的人類世界觀的基層。
這種宇宙觀在中國古代存在的特殊重要性,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明,在它的基礎之上與它的界限之內建立起來這件事實。中國古代文明是一個連續性的文明。1對於如是的一種觀點,我們基本上是抱持著贊同的態度。特別是張光直氏所指出的,類似中國這樣一種具有連續性特質的文明形態,在原始社會中,乃是相當普遍的,而西方將文明與自然截然二分的傾向,反而是一特例的觀點2,對於今日在反省人與自然關係一事上,更是別具啟發性。無論是從《老子》、《莊子》、《易經》、《易傳》、《禮記》以及《黃帝內經》等典籍,還是就中國幾千年來現實政治、社會運作的情況來看,古代中國人,確實從未脫離自然、宇宙或天地陰陽變化現象,來思考及安排人事,由是而使得中國古代文明具有一種連續及整體的特質。不過,筆者以為,光是概括或定性式地指出中國古代的文明具有著連續及整體等特質,尚不足以使我們完整地把握中國古代文明的確切內涵以及特色所在。因為這一連續及整體的文明觀,除了具有類似道──陰陽──五行這樣一種宇宙論,以做為其理論基礎之外,而且,也發展出了將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同時參究並論的三才整體思維模式,來具體落實《易傳·乾卦·文言》當中所謂的,「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偉大理想。因此,只有當我們進一步去了解天、地、人三才思維的真正內涵,而且去探討古代中國人怎樣具體地看待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間的密切關係,以及怎樣在天地這個無可逃避的大舞台、大背景下,來安排及考量人事,才能使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有一全面而深入的認識。筆者以為,這個由中國古代的「聖人」們所發展出來的系統思維模式,以及其對於天文、地理及人事三者間之密切關係的認識,對現代人在思考人類與自然關係以及人類文明未來的走向等事上,實深具啟發意義。因此,在本文當中,筆者嘗試對此思維之確切的內涵、其認識論的基礎以及此思維對現代世界的啟示……等等主題,做一通盤性的剖析及探討。
貳、三才思維的淵源以及其體系的完備與確定
一、三才思維溯源
三才思維的一個基本預設,便是以天文、地理及人事三者,具有著互融互攝、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類的生、心理活動以及一切行事,皆無時無刻不經受著來自於天地間的影響。是以,人類在思考及安排一切行事之時,不僅無法脫離這來自於天地的作用及影響,而且還要先了解天地相對運動的規律及變化情況,然後再依此規律及變化情況,來適切地安排人事。換言之,天地之間的相對運動,對於人類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來說,具有著一種根本性及決定性的支配作用;人類及一切生物的種種活動及作為,只有了解並依循天地相對運動的規律及法則,才有可能在這個星球上達到長治久安抑或永續經營發展的目的。類似這樣的一種思維,最遲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已達到體系完整、全面,且滲透到當時各個文化領域,成為最具支配性及關鍵性的主流思維模式。然論其源流,卻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巫術文化。
當代著名的宗教學者M.耶律亞德,在探討上古的存有論時,曾發現一些遍存於原始社會以及歐亞古代文化當中的共同認知。比如,古人以為,「不管是外界的事物,或是人的行為,都沒有獨立自足的內在價值。事物或行為所以有意義,乃因於它們以某些樣式參與超越它們的某種實在,才有可能得到,它們也由此才變為真實的」。「環繞我們,為人手所開發的世界,它取法一個超越塵世以外的原型。人類依據某一原型而建設,不僅城市或寺廟有其天上的模型,連他所居住的全部區域,供給飲水的河川,提供食物的田野等等,也莫不如此。」「古代世界裡沒有世俗的活動:任何意義明確的行為──狩獵、漁獲、農耕或競技、鬥爭、性行為──都是在參贊神聖」3。如是的一些論點,和中國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思維,確有不少共通處。事實上,當耶律亞德在探討上古的存有論之時,也不時援引中國古代包括《禮記》在內的典籍文獻。而無論是從《周禮》一書中天、地、春、夏、秋、冬等官制的設計及規畫,還是從《禮記·月令》的論述以及秦始皇陵之內部空間的構築4,皆可有力地印證,耶律亞德如上的觀點,確實完全可以適用在中國古代思維模式的理解上。由此,亦可概略地見出三才思維模式之古遠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性。當然,若就中國本土的文獻資料來論,應當可以更有力地支持如上的一種說法。 前不久剛去世的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在論述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時,曾如此說到?
中國古代文明中的一個重大觀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層次;其中 ,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層次之間的關係,不是嚴密隔絕、彼此不相往來的。中國古代許多儀式、宗教思想和行為的很重要任務,就是在這種世界的不同層次之間進行溝通。進行溝通的人物就是古代的巫覡。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shamanistic)的文明,這 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個特徵。5
張光直先生之所以得出如上重要的結論,和他對於巫覡在上古文化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巫覡之職能、所使用的法器、工具的深入研究有關。在<商代的巫與巫術>一文當中,他即一針見血地指出,「商、周時代的巫,便是數學家,也就是當時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能知天知地,是智者也是聖者」6。而巫師所經常使用的法器及工具,比如矩、琮、樹木、動物……等等,也都具有著交通天地、神人的功能7。是以,在人文事物尚未勃興,文字及理性思維尚未繁榮發展的時代(特別是在西周之前)當中,巫、覡這一類的人物,其身分、地位,確實是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這在許多的原始部落當中,仍可看到近似的情況8。雖然巫覡的地位在周代之後已一落千丈,其影響力亦大不如前,但若要探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抑或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的起源,實不能不追溯到巫、覡這一號人物身上。這無論是從《國語·楚語》中,楚昭王與觀射父那一段著名的對話,還是從諸子百家皆推崇聖人,並把聖人視為其學術思想的創始人,皆不難得到說明。而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的一般,巫所扮演的角色,便是溝天地、神人,其所擁有的能力,乃是知天知地的智慧。是以,當我們在追尋中國古代三才思維的起源時,實不能溯及到上古的巫者身上。做為三才思維之理論淵藪的《易經》、《易傳》及《黃帝內經》等書,將其知識的締造,歸諸於「聖人」這一類人物,便可有力地支持這樣的說法。
雖然由於文獻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完整地重建新石器時代巫、覡的世界觀、認識方式以及思維模式,與殷、周文化之間的確切傳承脈絡,然從現存典籍的一些記載,亦可見出,原始的天地人三才思維,經巫、覡首先揭示之後,便已完全為後世所採納及接受,並且得到了一些新的發展。《尚書·堯典》中的這一段文字,便是極好的證明?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天官書》中有言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此外《尚書·堯典》孔安國《傳》亦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由以上這兩則論述,皆可清楚見出,羲、和二人之學術思想及思維模式,和顓頊時代的重、黎,確實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而從《漢書·藝文志》當中所說的,「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數術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亦可得知,羲、和二人,在身分上,亦和重、黎一般,同屬巫、覡一類人物9。就內容來論,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一語,正提綱挈領地概括出<堯典>中這一整段文字的根本思維模式。此一思維模式,清楚地顯示著,依循天地運行的規律,來適切地安排及進行人事的重要性。在古人看來,只有這樣,才是長治久安、繁榮興茂的不二道路。凡熟悉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及文化諸領域之人,皆不難看出,如上的一種思維,數千年來,事實上並未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動。每一新王朝成立之時,皆把頒布正朔、制定新曆法,以使政經、社會情事,有所遵行的依據及法度,便是最好的說明。而負責觀測天文現象的官員、機構,一直在各個王朝當中,扮演一關鍵性的角色,亦是有力的佐證10。相對於西方文化來說,中國古代文化及思維模式之如是的連續性及一致性,實不能不說是一極為獨特及值得深思、探索的現象。比如,為何類似這樣的一種思維模式,會如此地穩固、長命及不可打破?遵循如是的一種思維模式而運作,是否是中國古代文化之得以延續如此久遠的主要原因?如果說,類似中國古代天地人三才合參並論的整體思維模式,在人類早期世界當中,具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那麼,為何在中國一直延續著它,而西方卻沒有呢?
二、三才思維體系的完備及確立

美國的社會學家Peter Berger,在探討西方社會世俗化的起源及過程時,曾比Max Weber更進一步,將思想的源頭追溯至古代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上。在 Peter Berger 的認識當中,埃及及美索不達米亞這兩大古文明之間,雖存在著不少差異,但卻同時具有一個Berger稱之為「宇宙論」的共通特點。「這個特點,意味著把人的世界(即我們們今天稱為文化和社會的一切)理解為是鑲嵌在包含整個世界的宇宙秩序之中的。這種秩序,不僅未在經驗實在中人的領域與非人的(即自然的)領域之間,作出現代這種截然的畫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假定了在經驗的東西與超經驗的東西之間,在人的世界與神的世界之間,存在著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假定,人間的事件與滲透宇宙的神聖力量之間,有一種不間斷的聯繫,它一次又一次地在宗教儀式中得以實現」11。然而,如是的一種共同的宇宙論觀點,在以色列新興的宗教當中,被一個超絕於世界之外的上帝信仰所取代。由於這個上帝「站在宇宙之外,宇宙是他的創造物,但卻與他相對立,未被他所滲透」12,因此,原始的人與宇宙之間相互融攝、密合無間的宇宙觀,便一轉而為帶有斷裂性及二元性的特質。換言之,在Peter Berger看來,古猶太教所建立的獨特上帝信仰,正是日後促使西方文化走向理性化及世俗化的根本源頭。猶太教及基督宗教的信仰形態,對於西方文化的形塑來說,實具有一種決定性的影響。
對照於近東早期文化之如是的一種巨大轉折,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並未出現。誠如上面所論述的一般,中國三代之前的文化,無疑和埃及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一樣,具有著「宇宙論」的特質。但這樣的一種宇宙觀,不僅在人文大興、文字大量使用及巫覡地位大幅衰落的周代當中,得到了全面性和創造性的保留及繼承,而且,還一直延續到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這和西方的情況,實有著相當根本的不同。如果說,近東早期文化之所以會經歷如是的一種巨大轉折,和猶太教上帝一神信仰以及摩西、以利亞等先知型人物的出現有關;那麼中國古代文化之所以會保持如此長久的延續性,也正和兩周之際,所出現的一些聖人、賢哲,對於中國上古文化所做出的創造性轉化及詮釋有關。德哲雅斯培所提出的「軸心時代」說,即敏銳地指出,東西方在這一時期當中所出現的一些先知型或聖哲型人物,對於後世文化之內容及形態的確立,具有一種關鍵性的決定作用。以中國的情況來論,在兩周之際,中國文化確實經歷了一次極為重要、極為關鍵的轉型。原始的巫術或薩滿式文明,在文字的出現及大量使用以及工具技術層面的變革之後,開始面臨著解體、崩潰的危機。無論是巫覡地位的大幅衰落、天地鬼神信仰體系的日漸瓦解,還是禮樂制度的潰散,都在在反應出當時所出現之信仰或世界觀崩潰危機的全面性及緊迫性。於此之際,所誕生的一些聖哲般的人物,比如劉康公、子產、孔子、老子……等等,對於所謂「現象的拯救」、人生觀及世界觀的重新安立,以及原始薩滿文化的轉型及延續,的確扮演著相當核心且重要的角色。其中,又以孔子及老子二人,做為文化龍脈的最重要結穴點。從孔、老二人對於其所身處之文化傳統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工作,正可清楚地見出,中國上古的巫術型文化,如何經過重新的詮釋及改造,而被全盤地保留及承傳下來。這樣的重新詮釋及改造模式,和近東以及地中海一帶,大約同時出現的轉折,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日後中西的文化,之所以會呈現出如此不同的風貌及內容,此時代所各自歷經的不同轉變,正是一個不能不去了解的關鍵所在。以下,即進一步論述孔、老二人如何重新的詮釋及傳承原始的巫術文化,以及原始的天地人三才思維,在這個時期當中,所經歷的同樣轉變。
做為北方周、魯文化之核心內容的禮與樂,原本具有著宗教祭祀之功能及作用,無論是從《國語》、《禮記》等典籍文獻的論述,還是從今日學者們(如王國維氏)的研究考證以及現存原始民族的宗教儀式、道教正一派的齋醮科儀,都可得到充分的佐證及說明。《說文解字·示部》、《易經·豫卦》以及《禮記·樂記》當中所說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事从豊」,「先王以作樂崇禮,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等語,即是其中之代表性的要論。至若考論原始禮樂的創制者及執行者,《國語·楚語》當中所提及的「巫、覡、宗、祝」,顯是不二的答案。不過,正如上文所曾提到的一般,這些原本涵蘊著極為濃厚之宗教、神學色彩的儀禮音樂,在理性思維的抬頭以及文明事物的大量出現之後,便逐漸為統治者及被統治者所遺忘及疏遠。此時,若不針對其內容做一番重新整理及改造的工作,則古老的禮樂文化,便不免落入「花果飄零」,甚至枯萎斷絕的命運當中。從當時之思想、文化的發展情況來看,孔子「仁學」思想的適時提出,顯然即發揮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作用。
孔子的思想,並非無其先行者;然而,孔子本人,無疑是北方周、魯文化之最重要的總結者、詮釋者及集大成者。因著孔子的重新詮釋,我們可以看到,原本具有濃厚之宗教、神學色彩,但又因時代環境以及人心、意識的巨變,而難再為人所遵奉及信持的禮樂文化,在人類自身生命及宇宙天地當中,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礎及根據。所謂「天生德於予」(《論語·述而》),「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禮之奉行,在求心安」13……等思想,都在在反應出,古老的禮樂,到了孔子手中,已被賦予了嶄新的存在基礎,賦予了新的意義及生命。正是因著這樣的重新詮釋,才使得原已陷入信仰危機的禮樂文化,不僅再度活絡過來,而且還深深地影響中國此後兩千多年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生活。
類似於孔子對於北方周魯文化的傳承及再造工作,我們在老子身上,亦同樣可以看到;而且,兩者皆同樣具有反求諸己,在自身生命當中,尋求現象之本源,以重新活絡其所傳承文化的共通特質。當然,在此共通點之外,亦同樣存在不少的差異;且由於這樣的差異,而導致影響層面的不同。老子所傳承的文化,如眾所熟知的一般,乃是巫覡、祭祀之風十分鼎盛的荊楚文化。但從《老子》一書當中,可以發現,原本具有著至上神地位的「帝」,其存在的位階及屬性,已被老子明確的判定隸屬在「道」之下14;此外,原本具有巫覡及宗教色彩的「靈」、「神」等字眼15,也被抽象化及內在化,單純地視之為生命自有的現象及能力。如此觀點的提出,不僅將會對舊有的薩滿文化及宗教信仰體系,產生一種拆解及顛覆的作用;而且,也同時賦予了舊有文化以確定與穩固的存在根據及基礎,使舊有文化的內涵,不但不會因為新時代的到來,而遭到淘汰或否定的命運,甚且還獲得了嶄新的生命及力量,使後來者得以依循其所提示之途徑,反觀內求,探索宇宙及生命的奧秘。後世道教的內丹派修行者以及大部分的醫家、術數家所進行的探索活動,皆是遵從老子本人所指示的路徑而前進的。老子本人對後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特別表現在這一向度上。
從以上的分析及探討中可以發現,無論老子或孔子,皆未對其所傳承的文化,進行一種徹底決裂式的改造;反之,而是重新探求其存在的基礎,使之得以再度獲得源源不絕的活水及創造力。屬於原始人類社會所普遍共有的聯繫性、整體性宇宙觀,之所以會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直不斷地延續下去,和孔、老二人在其時代當中,所從事之轉化工作的特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孔、老二人之傳承及再造文化的方式,在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天地人三才思維模式,不僅同樣存在,而且,其內容、形態之穩固確立,在時間點上,亦近乎同步。以下所要繼續論述的,即是三才思維。
從前面的探討當中,可以見到,三才式的整體思維,其最早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薩滿或巫覡身上;隨後,發展至堯舜時代,已粗具規模。最後,來到春秋、戰國時期,則不但已演變得十分詳實而完備,而且,還深深地影響了包括禮樂、政治、社會、經濟、醫學、術數……等等領域在內的思維。甚至把此思維,視為是中國古代文明建構的最基本原理、原則,亦不為過。這樣的說法,從以下所引出之《易傳》、《黃帝內經》以及《禮記》當中之文字,便不難得到說明:
▲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易傳·繫辭傳上》)
▲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傳·繫辭傳下》)
▲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傳·繫辭傳下》)
▲ 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 紀。……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 而為鬼神。
▲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禮記·樂記》)
▲ 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為萬物之父母。……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素問·金匱真言論篇》)
▲ 黃帝問曰:「用針之法,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 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素問·八正 神明論篇》)
▲ 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
▲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老子列傳》一文結尾時,曾經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太史公此說,明顯地反映出戰國以降,儒、道二家之間所存在的分歧及爭議。而在《老子》、《莊子》及《荀子》等書當中,我們也確實可以看到儒、道二家對某些主題之思想、見地上的不同。然而,在這些不同之外,我們卻也驚訝地發現,基本思想與老莊極為接近的《黃帝內經》16,和儒家的《禮記》,在思維模式及基本理論結構上,竟完全一致。兩者皆同樣以《易傳》當中所謂的「三才之道」,做為理論的基本框架。只不過,一個強調依循天地氣運的規律及道理,來從事養生、醫療等活動;而另一個則主張,依循天地運行的規律及道理,來安排政治、社會活動以及規範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17。兩者所著重的面向雖有所差異,但就思維模式來看,並無絲毫的不同。這特別是從兩者對於具體行為的進一步規範情況來看,更是如此。比如,《內經》當中以為,當春天到來之時,天地萬物一片欣欣向榮,處於其中的人類,其內在的生理、情緒以及氣血運行情況,亦和天地萬物無所差別。是以,為求生、心理的和諧平順,人類應當順此節奏、規律,來進行作息及養生活動。若不如此便有傷生甚或病變的可能。《內經》上說?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氣交,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
完全同樣的思維,我們亦可以在《禮記·月令》一篇當中見到。其文曰?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冬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飆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從以上這兩段文字,我們除了可以看到,三才式的思維,乃為儒、道二家所共有的之外,而且,也看到了,原本在《尚書·堯典》當中所提到之「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較為樸素的三才思維,發展至春秋、戰國時代,已呈現出體系粲然明備、條目清晰具體的完善境地。這樣的一種思維體系,不僅未因時代環境的巨變、民心民智的開啟,而遭到淘汰、否棄的命運;反而由於被賦予了新的理論基礎,而變得更為繁茂及更為札實。這和儒家的禮樂思想以及原始的巫術文化,在中國的軸心時代所經歷的轉變,是完全一致的。而從後來之《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及《太極圖說》等書,以及現實的政治、社會運作情況來看,在《易經》、《易傳》、《禮記》及《黃帝內經》當中所呈現之三才思維,已根本地決定著日後中國人組織或構建其文明的方式,決定著億萬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作息習慣,以及看待人與自然關係的角度。欲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以及古代中國人的人天觀,三才思維實是一個不能不加以注意的關鍵所在。
參、三才思維的核心要旨及現代詮釋
一、三才思維的宇宙論基礎
天地人三才思維之得以建構起來,背後實有其獨特的宇宙論及認識論的基礎;不了解這樣的基礎,便無法了解三才思維的由來、依據及完整的內涵。有關認識論方面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當中,做專門的探討及處理,此處所要探討的,乃是宇宙論的問題。
無論是《易傳》、《禮記》,還是《黃帝內經》的作者,都十分清楚地意識到,在三才思維的背後,實預設著一個完整而獨特的宇宙觀,而且,從宇宙論的層次來看,此三者的認識,亦完全一致。由此,亦更加可以肯定,此三書當中所共同主張的三才思維,應當存在著一個共同的來源。首先,來看看《內經》當中的說法 ?
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闊,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臣斯十世,此之謂也。」(《素問·天元紀大論篇》)
夫變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素問·五運行大論篇》)
這兩段文字,基本上皆反映著一個同樣的宇宙觀。此宇宙觀以為,宇宙間之萬物萬象,皆源生自一個共同的根源──太虛;由於此根源之運動變化,才有陰陽、天地及萬物、萬象的形成及生化。而且,天與陽為主動,地與陰屬被動;天和地、陽和陰二者,正猶如根本與枝葉的關係一般。對於置身其中的人類來說,此乃人類無可能逃脫及迴避的基本背景、條件;人類實無時無刻,不經受著來自天地、宇宙的巨大作用及影響。是以,無論是為了完整理解人類自身的生命,還是為了適切地安排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皆不能不考慮這些來自於天地之間以及宇宙根源力量的決定性影響。主張在天地這一個廣闊背景下來思考及安排人事的三才思維,其之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礎,正是這樣的一種宇宙論觀點。
完全同樣的宇宙觀,亦可見之於《禮記》一書。比如<禮運>及<樂記>二篇當中所說的 ?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鬼神。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單單從《論語》或《孟子》這樣的儒家典籍,以及後世中國人對於禮樂的概念,我們很容易將儒家的禮樂,設想為規範人類政治、社會、家庭及個人生活的完整儀軌。比如,孔子所說的「非禮物視,非禮物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語,便很容易讓人形成這樣的一種印象。不過,從《周禮》、《禮記》以及《左傳》當中的許多論述,都可發現,無論是禮或樂,事實上,都不單純是一套人文世界的行為規範或藝術創作而已;在任何一個具體禮樂儀式的背後,都有其宇宙論或形而上的根源18。前引Eliade所說的,「古代世界裡沒有世俗的活動:任何意義明確的行為──狩獵、漁獲、農耕或競技、鬥爭、性行為──都是在參贊神聖」一語,事實上,正可恰如其分地用來理解原始儒家所賦予禮樂儀制的深刻意含。當然,從這裡也可見出,對於先秦時代的中國儒者來說,自然與人文,從來就不會被理解為判然分離的兩橛;所有人類世界的建制,皆應取法或符應自然的規律及道理,如此方有和諧順當、永續經營發展的可能。這一個古代禮樂所緊緊依循及取法的宇宙觀,與《內經》當中所說的,實無絲毫的不同;而當我們將眼光移轉至《易傳》上頭,更可見到,不管是《內經》或《禮記》,在論述宇宙論時所使用到的許多語彙,和《易傳》(特別是其中的《繫辭傳》),更是一字無差。由此皆可再次印證此三書思維之一致性,以及三才思維確有一個統一的宇宙論基礎。三才思維當中所牽涉到的一些獨特名相及範疇,比如太極、陰陽、五行、五運、六氣、象數、精、神、中和……等等字眼,皆和此宇宙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三才思維實此宇宙論進一步推演的結果;而從三才思維體系當中,亦可更為具體地把握此宇宙論之完整內涵。
二、天人相應及天地萬物一體觀
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在論述「連續性文明」的特質時,曾引用過這樣的一段話:
墨西哥人(即阿茲忒克人)把他們的都城和它的環境之間的關係, 看作一個整合性的宇宙論的結構──亦即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在其中,自然現象被當是從本質上說是神聖的、有生命的,並且與人類的活動發生密切關係的。這種觀點與歐洲人的看法相對照:後者把城市看作文明的人工產物,亦即宗教與法律制度在那裡很尖銳地將人類的身份與未經馴化的自然的身體,區分開來的地方。西班牙的修道士與兵士們,自動地將作為人類的他們自己,在一個上帝創造的秩序之中,比生命的其他形式為高的一個層次。但是印第安人則以一種參與的意識,來對待自然現象,宇宙被看成是各種生命力之間的關係的反映,而生命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相互交叉的宇宙體系的一部分。19
張光直先生以為,如上的一段論述,正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描述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從以上對於天地人三才思維以及此思維背後所依據之宇宙觀的探討,無疑可以相當有力地支持張氏這樣的一種說法。所謂「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在三才思維的認識當中,人類與天地萬物,本皆源自於一個共同的根源;彼此之間,在此根源性力量的牽引下,構成一個環環相扣、相互通感且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天地間的相對運動,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人類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事物;而人類自身的所做所為,亦會影響到週遭的一切,有時甚至還可能影響到天地自身的運行規律。是以,從這樣的思維來看,人類根本不可能脫離天地宇宙的因素來思考人事抑或認識人類自身;脫離天地這一個根本性及決定性的因素來思考人類事務,必然會因認識的偏頗及不週全,而導致不好的結果或下場。《內經》及《禮記》二書中,如是一般的思維,實不勝枚舉。
在《黃帝內經》當中,除了較抽象地談論到人與天地萬物間的統一整體關係之外,亦相當具體地論述了兩者間的相互對應情況。比如,如下所見的一些文字: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 正方,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素問·診要經終論篇》)
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軟弱輕 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素問·玉機真藏論篇》)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明 ,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素問·八正神明論篇》)
從這樣一些十分具體的論述中,應當可以使我們更加完整、清楚地把握三才思維中所認識的人與自然間的微妙關係20。《內經》的作者之所以一再強調,人與天地萬物,實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割離的整體,人類實不能脫離天地的作用來思考人事及了解自身生命的狀況,背後正有如是的一種具體認識在支持著。而因著這樣的一些認識,亦可見出,三才思維的建立及具體運,用並非單純地基於思辨、想像甚或比附;反之,而是植基在一種獨特的直觀體察認識方式。這樣一種微妙細膩的直觀體察認識方式,可以使人直接感應到宇宙及人體中之極微細、極微妙的變化。無論是《內經》、《易傳》或《老子》、《莊子》、《管子》等書,皆一致主張,經由這樣的方式認識宇宙、生命及人天關係。討論三才思維,而不論及此種認識方式,正猶如討論某種科學理論,而不去詢問其背後的實驗或論證根據一般。
三、氣論及象論
前言,在三才思維的觀照下,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皆源生自同一根源,且彼此互滲互攝,構成一個完整而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在《內經》一書當中,這一個相互貫串且時時相互作用著的統一整體,正是透「氣」這個紐帶,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上文所論述的宇宙論,事實上,亦可冠之以「氣一元論」的宇宙觀。依據此宇宙觀,舉凡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生物及無生物,人體內的經絡臟腑及組織結構,無不由氣所摶聚而成,亦無不通貫、滲透著氣。是以,宇宙間一切生滅變化現象,皆可透過「氣」之一字,來得到說明及解釋。比如,如下之兩段文字,便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 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素問·六微旨大論篇》)
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素問·六微旨大論篇》)
這兩段文字,清楚地顯示著,整個天地間之相互作用及變化情況,其本質上即是一種氣的變化;一個人若能掌握此氣之升降變化情況,即能了解天地運動詳情。天地如此,與天地運動時時相互呼應著的人體,又何嘗不然!《素問·四時刺逆從論篇》及《難經·第八難》當中即說:
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乎五臟。
諸十二經脈者,皆繫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
是以,無論是天地,還是人類自身,皆是由氣所摶聚而成;而天地與人體之間的交相作用,其本質即是氣的生成變化運動。相對於具有固定形象之質器之物來說,氣之存在屬性及位階,實要更為根本,更具本質性。古代的醫者,正是認識到此點,所以處處展現出重神氣而不重形質的傾向,並且完全以神氣來把握及說明人體生、心理現象以及天人之間的交互作用21。同樣地,三才思維所認識的天地人三者關係,亦完全可以氣來把握及說明。
氣之存在位階,除了較形器之物來得根本外,而且可因演化階段及特性的不同,而進一步區分為陰陽,或二陰二陽、三陰三陽……等氣。此外,天本身由於有其自身的運動變化過程,地理本身,亦有其自身的運動變化過程,因此,天和地,亦各自有其自身的陰陽變化。由是,整個天地之間交互作用的實際情況,便可透過天與地之陰陽氣運的相互作用情況來理解及推演22。依據《內經》作者的候察體會,天地之間的交互作用正好呈現出六十年一週期這樣的規律;已在中國沿用了數千年之久的干支紀年(日)法,正反映著六十年當中天地氣運變化的實際清況。醫家在掌握了每一年的運氣情況之後,方能據之以預測、診斷及治療疾病。三才思維之詳情,也只有在了解《內經》中所謂「五運六氣」的內容,方算是全面而完整。
除了氣之外,我們在《易傳》、《內經》及《禮記》當中,亦可看到一個重要性不下於氣的概念──「象」。有關「氣」之思想,學界己有不少的討論;然而,對於「象」之關注程度,相對來說,卻少了許多。事實上,氣與象二者,實是一體之兩面;兩者緊密相連而不可分離。欲了解氣,實不能離開象,象因氣之運動變化而產生23,是以,我們正可透過對象之把握,來了解氣之實際變化情況。離開了象,便無從了解氣;反之,亦是如此。「氣象」一詞之出現,正反映著氣與象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無論是在《內經》或其他典籍當中,都可充分印證這樣的說法。比如《素問》之<脈要精微論篇>及<五運行大論篇>所說的: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 ,不如鹽;青欲如蒼璧,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素問·脈要精微論篇》
岐伯曰:「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 牛女戊分。……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素問·五運行大論篇》)
前面一段文字所講述者,乃人之氣象;而後一段文字所論者,為天之氣象。先前在討論三才思維背後所預設的宇宙論時,我們曾引用了「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這樣的一段話,後面的這段文字,正可被視為句中所謂「觀象於天」的進一步說明。是以,氣與象二者,實不能被割離開來認識。而且,如果氣相對於形器來說,其存在的位階或屬性,要比後者來得更為根本;那麼,氣象相對於物象或形象來說,亦是如此。進一步來說,如果對於氣之覺察感通,有賴於超越後天感官之上的微妙覺知能力;那麼,對於氣象的觀測及把握,亦是如此。《易繫辭傳上》當中所謂的,「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正含蘊有這樣的意義;此外,《老子》書中所說的「象」,亦顯然具有超越經驗層次的意含24。
總而言之,在三才思維體系當中,無論是氣或因氣而有之氣象,其存在的屬性或位階,都要比感官可見之具體事物,來得更為根本及真實。凡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之間的交相作用情況,就本質上來說,皆可被歸結為氣與象的變化。職是,一個人若能體察天地之間氣與象變化運轉之機制,則即能由此而了知整個天地運動變化詳情。中國古代文化當中所充斥之「望氣」、「候氣」或「觀象」的說法25,正與如上的一種宇宙論或存有論觀點相互呼應著。是以,三才式的思維,亦可被理解為氣與象的思維;離開了氣與象,三才思維即無存在之可能;唯有掌握了氣與象的實質內涵,才能真正了解三才思維之真諦所在。
四、三才思維與太陽系生態系統觀
對於所謂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大英百科全書》(簡明版)<生態系統>條目下,有著如下一般的定義:
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組成的功能整體。由各自獨立,但相互作用的各部分所形成的統一整體稱為系統。由人類角度來理解,生態系統包括人類和人類的生命維持系統。後者,再包括空氣、水分、礦物質、土壤、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它們共同發揮作用並形成一個整體。在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下,產生不斷的能流,系統中形成營養結構,並造成物種的分化和生物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26
從此定義來看,小至一個池塘、溪流,大至一個島嶼、海洋以及整個地球,皆可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完整的生態系統。在一個生態系統當中,屬於其中的各個組成物,皆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給養,由是而構成一個環環相扣且密不可分的整體。有關生態學及生態系統的深入研究,除了使人類對於生物與環境的關係,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及體會之外,它也提供了另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及「思維典範」。此一新的思維模式,視事物與事物之間,皆彼此互有關聯;對於任何一個事物的認識與思索,皆不脫離其與整體環境或其他事物的關係來進行。如果先前的科學思維模式,有一種「分割存有」及「原子式思維」的傾向;那麼生態學式的思維,便一轉而具有「整體」、「有機」以及注重關係網絡的特質。「分割存有」及「原子式思維」的缺陷及不足,和其所帶來的惡果,已十分明顯地展現在人類對於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上;而生態學式的思維,不僅有彌補或矯正先前科學思維之不足的重大作用,而且,還可能更接近於宇宙或存有之根本實相。是以,生態學式思維的出現,在人類思想史上,實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
從上文對於三才思維的分析及討論來看,這個貫串著中國古代幾千年文化的核心思維模式,其形態,顯然可以被視為是生態學式的。蓋此一思維,從來就是一種整體式或機體式的思維,而且,從未把任何一個事物,從其存在環境當中獨立出來進行認識及思考。在《內經》當中,對於人類的生理、心理、病理與天地環境間之密切關係的認識,便是最好的說明。細考此思維模式,我們固然可以見到,在視宇宙間之萬事萬物皆源生自同一根源的宇宙論視野下,所有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皆互有關聯,且不可能被單獨地抽離出來認識。不過,再進一步加以檢視,亦可發現,對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星球來說,影響最重大的,還是屬於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是以,三才思維當中的一個重要核心內涵,便是超離地球,把太陽系視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加以看待及思索;而且,對於日地、月地以及日月五星與人體生、心理的關係,有著十分獨特的認識。類似這樣的一種生態系統觀及認識內容,即使在今天,仍極具啟發意義及價值。以下,即特別針對這些,做更深入的探討。
首先,在日地及天地關係的認識上,無論是《易傳》,還是《內經》的作者,皆十分清楚地肯定,相對於太陽或整個天體來說,地球本身,其實是處在一個被動而非主動的地位。凡地球自身所出現的規律性季節變化及膨脹收縮運動,都是在天體力量的牽引下或特別是太陽光的照射之下而產生的;如果缺乏這外來力量的牽引、作用,則地球本身所展現的無限生機及繁榮景象,將頓時停息下來。上文所曾引用到的,「夫變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一語,便清楚地傳達著這樣的認識。其中所謂的「七曜」,即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素問》的作者特別指出此七星,顯然是認為,在整個天體當中,此七個星球的運動,對於地球來說,實具有最關鍵性的影響作用。除了《內經》之外,我們從《易傳》的《乾卦·彖傳》及《坤卦》的<彖傳>及<文言>當中,亦可見到同樣的觀點: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無論是「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一語,還是「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之說,皆明白地反映出,地球所處之被動而非主動的地位。地球上所展現的種種生化現象,皆得力於乾元的引動,抑或太陽(即上引文所謂的「大明」)的照射。其中所提到的「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說,和《左傳》、《莊子》以及《內經》等先秦典籍,所一再出現的「六氣」之說,完全一致;它們皆共同指涉著太陽幅射在一年當中所出現之六個強烈不同的變化階段。
如果天與地或日與地的關係,係一種主動與被動的關係,那麼,當天體或太陽本身的活動出現變化時,地球也會連帶地出現一些相應的反應。從這裡我們除了可以進一步地確認,欲真正認清包括人類活動在內的一切地球上的現象,實不能不了解來自於天體或特別是太陽這個關鍵性因素的說法之外,而且,還可進一步地得出,只要我們能預先掌握天體或太陽變化的情況,那麼,我們自然也能事先預知地球上有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相應變化了。《素問·五運行大論篇》之所以會有「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之論斷,正是因為有如上的認識做為前提。天文學在中國各個朝代當中,之所以會受到無與倫比的高度重視,也正是有這樣的思維在背後支持著。
除了日地及天地關係之外,《內經》當中,亦對於月球及金木水火土星與地球的關係,做了一些論述。比如:
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致,毛髮堅,腠理郤,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靈樞·歲露論》)
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 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歲火太過,上應熒惑星。歲土太過,……上應鎮星。……歲金太過,……上應太白星。……歲水太過,上應晨星。……夫子之言歲候,其不及太過,而上應五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
前一段文字以為,無論是地球上海洋的潮汐運動,還是人體內氣血的盛衰情形,皆受到月球引力的影響。當滿月之時,海水西盛,人體氣血亦達到最旺盛的階段;而當月相由圓滿走向虧缺時,海水亦由西往東退去,人體內的氣血,則由實轉虛。至於下一段文字,則肯定地球上木火土金水五運之遷轉變化,和天上的歲星(即木星)、熒惑星(火星)、鎮星(土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的運動,有一種對應的關係。除此之外,《內經》的作者還觀察到,五星的運動有徐疾順逆的不同,而星球所發出之光芒亦有大小明暗的差別。當五星的運動及明暗程度有所變化之時,地球上四季的運轉情況,亦會出現一些相應的變化27。這是《內經》的作者,根據長期的觀察,所得出的一些結論。
以上有關《內經》日地、月地以及五星與地球關係的論述,有不少地方,和現代天文學、大氣科學的認識,十分接近;當然,不能為現代科學所接受的,亦不在少數。然而,當我們試圖以現代科學的認識,要來檢證《內經》的思想時,亦必須清楚地認識,《內經》及《易傳》的作者,其觀察或理解地球與日月五星關係的方式,和現代科學所使用的方法,可說是南轅北轍。如果我們對於古代觀察天地的方式以及其中所牽涉到之認識論的問題,尚未有確切的把握及反省前,實不宜立即妄下論斷。此外,如果我們都能接受太陽及月球的運動,對於地球來說,確實有著相當關鍵性的影響,那麼,當我們在思考及認識地球上所出現的種種變化情況時,很顯然是無法將眼光只局限在地球這個生態系統本身。換句話說,從《易傳》或《內經》的觀點來看,一個能比較全面而完整地了解地球上之生化情況的思維模式,至少是必須以整個太陽系做為基本的思考單位的思維模式。若不如此,則對於地球本身的認識,也必然是片面而不完整的。三才思維對於今日世界在思考環境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係時,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地方,正是在這裡。
肆、三才思維的認識論基礎
當西方近現代文化的內容,襲捲了整個世界,支配了人們看待宇宙、生命的方式之後,東方人在看待自家文化的內容時,便很難徹底地擺脫西方式的思維及觀點的影響。嚴重點的,會全面而徹底地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較輕微的,則是以西方式的觀點,來理解傳統文化當中的許多內容。比如,對於本文當中所討論到的宇宙論及三才式思維,不少人皆將之等同於西方式的思辨哲學,認為其所據以建立的方式,便是想像、推理及思辨;不然,便是從現代科學的立場,認為其是屬於前科學時代的產物,其是否具有真實性,實不值得一駁。對於如上的兩種觀點,當我們深入去了解三才思維的內容時,便可發現,其之偏頗及錯誤,都是十分明顯的。因為,無論是在認識方式(比如,「虛靜」、「用神」、「仰觀俯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等等),還是在認識內容上(如五運六氣、陰陽、太極、精、氣、神、象……等等),三才思維與西方主流的哲學及科學,實截然有別。如果我們未能深入去了解其所據以建立的方式以及其所認識內容的獨特性,則便不宜對其內容,遽下斷語。有關三才思維的具體內容,上文已有不少的討論;以下,即針對三才思維的認識論基礎,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從下面的討論,將可清楚地發現,三才思維的認識方法及認識內容,兩者實息息相關、無法分離。
一、真人、聖人、至人及三才思維體系之建立
現代科學的建立者,係被稱為「科學家」的一類人;而在《易傳》、《內經》及《禮記》當中,則把其知識或禮樂的發明及創制,歸之於真人、至人、聖人及君子。當我們嘗試去了解科學知識的性質時,實有必要去了解科學家是怎樣的一類人;同樣地,當我們要去了解三才思維的實質內涵及知識的特質時,亦有必要去了解所謂的「真人」、「至人」、「聖人」,到底是怎樣的一類人?他們又是以如何的方式,來進行對於宇宙、生命的認識?在《易傳》及《內經》二書當中,對於所謂的「真人」、「至人」、「聖人」,以及其精神狀態、人格特質、認識方式,皆有相當具體的描述。以下所錄者,即是當中的部分說法:
與道合同,惟真人也。(《素問·六微旨大論篇》)
上古有真人者,提契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 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 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 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亦歸於真人。(《素問·上古天真論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傳·繫辭傳上》)
從以上幾段文字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在《易傳》及《內經》作者的眼中,所謂的「真人」、「至人」或「聖人」,由於其煉養有方、操持得法,因此而能超越通常感官知覺的認知能力以及後天有限形軀的限制,不僅大大地延長自身的壽命,而且,還能覺察感應到一般人所無法領受的深層微妙現象及信息。無論是中醫各類知識的建立,還是《易傳》當中所特別強調之象、數、幾等獨特現象及規律的把握,都和聖人、真人本身所擁有的超乎常人的認識能力有關。此項能力,顯然只有在止息及轉化後天的感官知覺及生命作用方能被開顯出來。如是的說法,對於現代人來說,雖然十分的陌生及難以思議;然而,在原始民族28、上古的巫覡、薩滿29以及先秦時代的許多典籍及學派當中,卻是屢見不鮮。比如,《老》、《莊》及《管子》書中所說的「虛靜」(《老子》,第16章)、「無為無不為」(《老子》,第48章)、「無有入無間」(《老子》,第43章)、「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莊子·養生主》)、「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莊子·人間世》)、「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管子·內業》)……等等,皆與《易傳》、《內經》所主張的認識途徑,完全一致30。是以,當我們嘗試去了解三才思維的內涵時,實有必要先了解其背後所依據的獨特認識途徑及精神、意識狀態。
二、三才思維認識方式的特質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三才思維所據以建立的認識方式,事實上乃是一種具有智性直觀特質的特殊覺知能力。無論是《易傳》所謂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還是《內經》中的「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素問·寶命全形論篇》)、「持脈有道,虛靜為寶」(《素問·脈要精微論篇》),都是在講述這樣的一種獨特認識能力。此種能力,可以不為時空所限制,並且能穿透事物之表面現象,而直接把握到屬於事物之本質層次的內容。這樣一種能力的開顯,乃是在止息並轉化後天感官的知覺作用以及認識方式之後,方有可能。換個角度來說,無論是《易傳》及《內經》,皆同樣肯定,人類生命當中存在著一種超乎眼、耳、鼻、舌、身、意之外的特殊直觀能力以及超乎器質性肉身之外的存在層次。當一個人經由虛靜或無思、無為的工夫,轉化自身生命的存在狀態以及運用通常感官知覺的方式,便有可能使生命進入一種超常的境界當中,開啟另一種覺知事物的方式,並且覺察到一般人的感官知覺所無法領受的現象及信息。有關此種能力的開顯方式以及生命狀態的轉化過程,在《易傳》及《內經》二書中,雖講得非常簡略,但在老莊以及大興於唐末五代之后的內丹煉養學說,卻闡述得相當詳盡。基於此數者認識論主張的一致性,我們無疑可以透過老莊及內丹典籍,來還原有關此種認識途徑的詳情31。
伍、三才思維模式對現代世界的啟示
一、三才思維與永續發展之道
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由於人口的過度膨脹、毫無節制及缺乏長遠規畫的使用自然資源,以及思維方式的狹隘、片面……等等因素,而造成對於地球環的嚴重破壞。有識之士遂開始呼籲及提倡一種新的整體式思維及環境倫理觀,並尋求一條可以與地球上的環境共存共榮及永續經營的道路。有關此點,筆者以為,中國傳統的天地人三才整體思維模式,事實上有著非常豐富的思想資源以及上下幾千年的具體實踐經驗,可以提供給現代世界做參考。
從上文對於三才思維的探討,我們不難發現,此思維的最高理想,本在追求使人類生命以及其所建構的社會,皆得以達到長治久安、永續發展的境地。所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一語,正可直接而扼要地點出這樣的目的。此外,從這句話也可看出,在《內經》作者們的想法中,欲達到這樣的目的,則首要的前提,乃是確切地把握地球自身的變化運動情況,以及日月五星等天球對於地球的作用力及影響詳情。蓋對於人類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來說,來自天地的作用力及影響力,不僅是人類所無法迴避及違逆的,而且還具有著十分關鍵性及支配性的決定作用。是以,實不能不設法認知及把握,且確實依循天地運行的規律,來生息及繁衍。如若不然,則便難免遭受禍害災厄,甚至早早夭折滅亡的悲慘命運。這是《內經》一書中所一再出現的嚴重告誡。基於這樣的一種基本認識,《內經》的作者還進一步提出他們所體認及觀察到的天地相對運動規律,以及對於人體生理、心理的具體影響情況。此外,也歸納出許多日常生活起居作息的基本原則。類似這樣的一些內容及原則,對於我們今日在思考人與自然關係以及思考如何在此星球上長遠而永續地經營發展下去,皆應當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整體思維與萬物一體觀的建立及培養
三才思維做為一種整體式的思維模式,其之得以建立,實和《易傳》、《內經》及《禮記》等書中所謂的「聖人」、「真人」的獨特修行體驗及精神、意識狀態有關。此種精神狀態,超越了器質性身體的限制以及感官經驗的層次,打破了物我間的分際及對立,而與宇宙萬物互滲互攝、融合成一無可割離的統一整體。由此狀態的進入,而能敏銳細緻且通暢無礙地直接感應到宇宙萬物之運動規律及變化詳情。此種狀態,既已如實地感受到宇宙萬物實為一不可分離的統一整體,則其思其想、其領悟事態的方式,自然也會表現出一種整體思維的模式。此外,對於與其無可分別的萬事萬物,也必然會生起一種憐憫愛惜之心。今日環境問題的真正起因,顯然不只是在於人口的過度膨脹,以及物質科技的錯誤運用這樣一些表面或外在的因素而已,生命或宇宙之物質層次,被視為一獨立甚且是唯一的實體,身體與心靈之無法得到真正的統一,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疏離及對立,方是問題的真正關鍵所在。外在世界所呈現的種種問題,說到底,只不過是生命內在問題的外部化罷了。若生命本身得不到真正的完整統一,則反映在外部行為的,也必然是一個與世界或與他人相衝突、對立的結果。是以,徹底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萬物一體意識」的領會及培養。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中國、印度的宗教哲學,還是原始文化,皆有十分豐富而寶貴的資源。筆者以為,東方哲學以及許多原始文化的內容,能對環境問題的解決,做出重大貢獻的地方,亦是在此。
陸、結論
本文之主要目的,係在對中國古代三才思維的源流、內容、認識論的基礎以及其現代意義,做一全面性的探討。筆者以為,這一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抑或更早的整體思維模式,在中國的軸心時代期間,經過重新的詮釋及改造,而被完整地繼受下來。其主要的精神,係把天文、地理以及人事三者,視為是密切相關且無法被割離的統一整體來加以認識及思索。在《易傳》、《內經》及《禮記》等書當中,對此三者間之具體的關係,皆有著十分詳實的論述及剖析。對於這樣的一些內容,若以現代的觀念、語彙來加以詮釋,實可被視為是以整個太陽系做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看待的生態學式思維。此一思維,對於今日在思考人與自然關係以及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時,將極具參考價值。
除了上面所陳述的各項要點之外,本文亦對三才思維的認識論基礎,做了一些初步性的探討。此外,還以為,三才思維所涵蘊的「天地萬物一體觀」,正是現代世界所十分欠缺,也是徹底解決今日環境問題所必須建立的基本意識。無論是三才思維,還是中國傳統的哲學,在此意識的培養及建立上,皆有著十分豐富而寶貴的資源。三才思維及中國傳統哲學能對於環境問題的思考及解決,產生重大貢獻的地方,此是另一要項。由於本文所涉及的範圍過於廣泛,此外,亦有時間及篇幅上的限制,是以對於各項主題的探討,便難免有疏闊不足的地方。更加細緻而完整的討論,實有待於未來。
--------------------------------------------------------------------------------
1 張光直著,《中國青銅時代》,頁487-488,北京,三聯書店,1999。 2 詳參張光直先生所著《考古學專題六講》(台北,稻鄉,民77)一書<第 一講>以及上註書第494頁以下的討論。 3 以上三段引文,分別出自M. Eliade所著的《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楊儒賓譯,聯經,2000)一書的第2、7、22頁。 4 根據《史記·秦始皇帝本紀》的記載,秦始皇為其自己所構建的陵墓,「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此外,秦兵馬俑三號坑所出土的秦皇座車,亦是模仿天圓地方的形態而製造。 5 張光直著,《考古學專題六講》,頁4。 6 張光直著,《中國青銅時代》,頁256。 7 有關此點的詳細討論,可參看張光直先生所著之《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的<商代的巫與巫術>及<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二文。
8 在秋浦氏所主編的《薩滿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一書當中,對於薩滿在原始民族中的地位,即有如下的一段論述:「薩滿是集許多民族原始宗教的大成的。他被為是這種原始宗教教義最具權威性的解釋者,是被認為能保估人們平安生活免除災難的祖先神靈的代表,是專門進行宗教活動的巫師,是一切傳統習慣的堅決維護者。薩滿作為人神之間的『使者』,在人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55頁)如是的說法,和《國語·楚語》中所提到之巫覡的地位,完全一樣。 9 有關此點的詳細討論,可參看江曉原所著之《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一書第三章第二節。 10 詳參江曉原《天學真原》一書第三章的討論。 11 Peter Berger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頁135-13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有關此點,張光直先生的觀點,和Peter Berger似有不同。前者以為,斷裂式文明的出現,係在兩河流域(《考古學專題六講》,頁23-24);但後者則以為源自於以色列民族的宗教信仰。 12同上書,頁138。 13《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一事,孔子的回答,即有此意。 14《老子》第四章言,「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15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靈,巫以玉事神。” 此外,在《楚辭》當中,亦有將巫稱爲靈的說法。由此二者,皆可見出,“靈”之一字,和巫覡以及巫覡進行通神之時所進入的精神狀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老子在解釋“靈”這個字時,不僅完全排除了巫覡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排除了其中的宗教、神學成分,而且還以爲,一個人如果能(透過虛靜的工夫)使自己的精神達到完全專一的狀態,便自能産生微妙靈通的玄智,在這之中,並不需要借助巫覡這樣的媒介。從這裏亦可看出,老子本人是透過如何的一種方式,來重新解釋、改造及保存上古的巫術文化。這和孔子以“仁”來重新詮釋及保存周魯的禮樂文化,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16 關於此點,筆者之碩士論文《內經認識論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1994)第四章第一節,有較為詳細之討論。 17兩者各自所強調的面向雖有所不同,但糾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涵蓋生命的一切活動。由此即可見出,三才式的思維,實滲透到傳統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當中。 18 饒宗頤先生在<《春秋左傳》中之「禮經」及重要禮論>(收於陳其泰等編的《二十世紀中國禮研究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一書中)一文中,即曾指出,「根據燕京大學《引得》,《左傳》全書中禮字總共見四百五十三次,又言『禮制』者十條。出現的頻率可和印度《梨俱吠陀》(Rigveda)中Rta一字出現超過三百次,互相比擬。《吠陀》的Rta,意義是指天地的秩序,這種秩序是代表禮儀上、道德上的宇宙性的經常之道。它和『禮』表示天經地義的『禮經』,有點相似。一談到禮,很容易把它說成禮儀、禮節,把它翻成ritual,但春秋以來的儒家(如叔向、晏嬰)以至初期的法家(如子產)都給予宇宙義。這一點是需要重新認識和抉發的。」(472頁)饒氏此說,和《禮記》中對於『禮』之看法,無疑相當吻合。 19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495頁。 20有關人體氣血的運行與天體運動的對應情況 ,在中醫之「子午流注」及「五腧穴」學說當中,有著更精微、更細緻的認識。 21比如,「外內相得,無以形先」(《素問·寶命全形論》),「粗守形,上守神」(《靈樞·九針十二原篇》)(對於這段話,馬玄台的註解是,下工泥於形跡,徒守刺法;上工則守人之神。凡人之血氣虛實,可補可瀉,一以其神為主,不僅用此針法而已矣。)等語,皆清楚地顯示著這樣的一種傾向。傳統的中醫之所以不重視人體解剖,其根本的原因,亦是在此。中醫如是理解人的方式,在整個中國文化當中,不僅不是絕無僅有的孤例,而且是遍見於各個領域當中。比如顧愷之、宗炳、沈括等人所說的,「四體妍蚩,本無關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說新語·巧藝篇》),「神之所暢,孰有先焉!」(傅抱石編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里仁】,第38頁)「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夢溪筆談》),正充分表現出和中醫一樣的人觀。 22《素問·天元紀大論篇》言,「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 23《素問·五常政大論篇》:「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 24《老子》第21章言,「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由此,在《老子》一書中,「象」之一物,顯然是屬於形而上層次。《易繫辭傳》中的聖人所見之「賾」與「象」,和老子本人所見者,很可能是同樣的事物。 25 比如,《史記》<秦始皇帝本紀>所說的「候星氣者至三百人」,即充分顯示,類似「望氣」、「候氣」或「觀象」等方術,在古代乃是相賞普遍的。此外,<項羽本紀>中,范增所說的,「吾令人望其(指劉邦)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亦是一例。 26《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簡明版)第13冊,167頁,台北,丹青圖書公司。 27 詳參《素問·氣交變大論篇》 28 在列維─斯特勞斯所著的《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一書第一章,對於原始民族之敏銳的知覺能力,引述到不少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比如下面的這兩個例子:「這裏的土著具有敏銳的官能,他們精確地注意到了陸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種的種屬特性,以及象風、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變化、水流和氣流等自然現象的最細微的變異。」「他們注意到細微的區別,…他們給該地區的每一種針葉樹都取一個名字,儘管各種樹木之間的區別微不可辨。普通的白人則不能區分它們。人們也許真有可能把一篇植物學論文翻譯成特瓦語。」 29《國語·楚語》中對於巫覡之人格特質、認識能力及精神狀態的描述(如,「精爽不攜貳,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便是最好的例子。 30有關此點,請參閱拙著《內經認識論研究》第三、四章的討論。 31詳參拙著,《形上之道的探求──老莊及內丹認識論綜合研究》(中國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