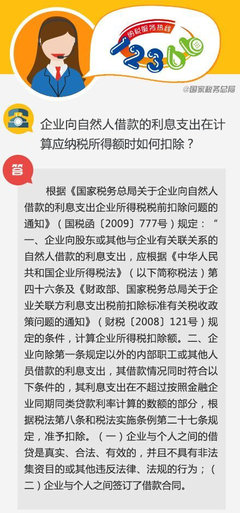被囚禁在“要么是世界疯了”与“要么是自己疯了”两道铁门闸,我深知其味。
撰稿·边芹 旅法专栏作家
假如现实是用笔画的一个圈,那么人的眼睛时常只能注意多变线圈上的几个点。只看见一个点时,现实就是这个点;看到两个点时,现实连成一条线;再慷慨一些收进三个点,现实就构成了一块三角地。但要拼出原来那个圈,眼睛要容纳无数个点。明白这个道理,人可以自己在浑水里打捞自己,既然永远摸不到现实真正的边界,苦或乐都可能是历史瞬间的变形、人心片刻的收放。 于是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尽可能多收几个点,看能不能超越悲剧的三角地。我是个杂读者,无系统,在文字世界无法无天,时常给我脱去囚衣的幻觉。这几日饱餐地从巴黎各区图书馆搜罗的书如下,看透过人类的陈酿能捉到几个点: 李治华翻译的法文版《红楼梦》。我喜欢在语境转换中寻找人间已不存在的世外桃源,两个语言哪怕在翻译高手的牵拉下,也会在挤兑中生出新空间,这就是我称之为“世外桃源”的他世界,是挤压在两个文化之间的彩色泡沫,是两个战场间的无人地带。
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全集第一卷,我主要是读收入此卷的《一个蛮人在亚洲》。米肖在书中就中国人写道:“油津津的脸上令人惊异地带着谦逊朴实的表情,与之相比欧洲人看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显得面容夸张,十足野猪的脸。”写到日本人,米肖还有一段:“总之这个民族缺乏睿智、朴实和深度,严肃得过分,虽然也喜欢玩具和新鲜事物,但很难快活起来,总是野心勃勃,表面一套,生来就是要让我们遭殃的……”不过读这类比较也不要得意,书成于30年代,那年头日本是西方的竞争对手,中国则是贫弱的观赏对象。对敢于和他们叫板的民族,西方人会瞬间变成绝情的狼犬;对一百年都赶不上来的,心便做戏般的软。 弗迪南·塞林纳全集第四卷,我为收入其中的《与Y教授的谈话》而借。50年代从丹麦监狱被放出来的他已处在被虐狂状态,精神皮肤没有一处不是伤,一触即破。他不幸看到皇帝的裸体,但所有人都说他疯了。被囚禁在“要么是世界疯了”与“要么是自己疯了”两道铁门间,我深知其味。 下面这一本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不到,只收在肉眼不能接触的总库里,一般都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事先知道书名的人才能申请从总库调阅,但知悉者甚少,因为传媒对这类书禁言。言论“自由”宣言下的暗门设在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此书被划到“政治不正确”一边,大概是对中国近代的不幸过于同情了,书名《世界最大的悲剧——从慈禧到毛的中国》,1968年加利马出版,作者吕西安·博达尔。第八章有一段,我读了泪洒衣襟:“混乱。混乱的蔓延。这是在遥远的四川作区区法国副领事的父亲,不断涌到嘴边的几个词……让他回不过神来的,是忽然之间,一个文明在几天之内,便似乎神秘地、不可解释地消失于野蛮之中。”那是1911年。博达尔眼里:西方策划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崩溃,而这才是人类历史最悲惨的一幕。 这些大部头间夹带着一本轻便袋装书,是借来放在手提包里乘地铁时读的:叔本华的《世界的苦痛》。但我读了几日,便决心还掉,待阳光普照的日子再借,书本身暗无天日,看这句:“今天很糟,以后每一天会更糟,直到最坏的降临。”人在文字里也没有希望。 还有奖臼桥涯嬲咚鞫誓崆俚模槐?980年出版的《西方的错误》;另一本20年后写的《两个世纪在一起(1795-1995)——犹太人与俄罗斯人》,我只借到上卷:十月革命前。这书属于被隐形封杀之列,我搜遍巴黎才找到一本,下卷还未借到。与他那本《古拉格》在各图书馆之泛滥,形成触目对照。他因前一本被捧上天,又因后一本差一点死讯都被封锁。索氏笔下犹太人从不自己动手创造财富而总是吸附在移居地人民身上诈财,害起他人从来名正言顺。但“神话”是动不得的。索顽童咽气前才明白揭东方能拿大奖,揭西方永世不得翻身。由此想到几天前在圣米歇尔艺术影院,看到《解放报》一篇评彭韬《血蝉》的文章大字报般贴在影院门上招揽看客,艺术在这里变成政治爆破,《血蝉》被制成射向中国、砸向奥运的炮弹。至少有一个现实是,你讲艺术良心,人家只讲政治用途。
 爱华网
爱华网